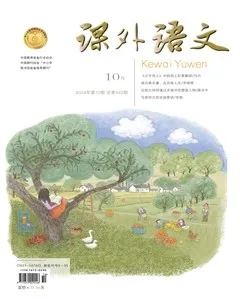認真聽,才能答得剛剛好
南朝宋著名文學家劉義慶所撰筆記小說集《世說新語》,是六朝志人小說的代表。其中《詠雪》被選入人教版《語文》七年級上冊。通常的賞析和教學中,都是簡單地說謝道韞的比喻要比謝朗的好,而其中的緣由是什么,蘊含的道理又是什么,卻少有人深入探索。本文將從聽的禮儀要求的角度來探討兩個比喻的優劣和文章要教給孩子們的做人的道理。
對于《詠雪》一文,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員范子燁有評語說:文章塑造了鮮明的聰慧才女謝道韞的形象,作者著意刻畫的魏晉新女性的藝術形象,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
老師們講課,也基本上是根據“未若柳絮因風起”來講謝道韞的才華之高。這些都對,但是卻不夠深入。筆者認為,文章除了高度評價謝道韞的才華之外,更多的是講做人的基本禮儀——認真聽!
要讀出《詠雪》的這一層意思,就必須認真品味“驟”字的含義,如果簡單地把“驟”理解為“大”,就無法讀出文章的品德教育意義。當然,也要調動生活常識,找一找如撒鹽一般的雪景,而不能把所有的“大雪”都理解成“鵝毛大雪”。
《詠雪》一文非常短小,為了論說方便,把全文抄錄如下: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文章非常簡單,說謝安在一個寒冷的大雪天,把子侄輩的人聚集在一起,跟他們一起談論詩文。不一會兒,雪下得很快了,謝安非常高興地說:“這紛紛揚揚的白雪像什么?”他一個哥哥的兒子(即謝朗,小名胡兒)說:“把鹽撒在空中差不多可以相比。”他另一個哥哥的女兒(謝道韞)說:“不如比作柳絮憑借風而飛起。”謝太傅聽了高興得大笑起來。她(謝道韞)就是謝太傅大哥的女兒,也是左將軍王凝之的妻子。
謝太傅在這里提出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紛紛揚揚的白雪像什么?”兩個孩子各自說了一個答案,兩個答案是很不一樣的。謝朗把雪比作了從空中撒下的鹽,側重于表現其綿密、急速的特點;而謝道韞則把雪比作了柳絮,側重于表現其輕盈、飄動、形態較大的特點。到底誰的好?就謝太傅的問題“白雪紛紛何所似”而言,當然是謝道韞的好。“紛紛”一詞在本詩中應該解釋為“多而雜亂”(據《漢語大辭典》),與撒鹽時鹽巴急速落下的狀態有很大的差別,但是與柳絮紛飛卻很相近。所以說謝道韞的比喻好,更形象,很有詩意,也更有一種奮進的感覺在里面。所以,劉義慶才會在最后交代她的身份,以示對她的贊賞——畢竟在中國古代歷史長河里,能留下名姓的女子實在是太少太少了。
另一個孩子謝朗的答案確實不好,不過,這種不好并不在于比喻本身,而在于他的回答是“答非所問”。為什么這么說?如果謝太傅的問題是“雪像什么”,答案會有很多種,就如魯迅所寫——“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紛飛之后,卻永遠如粉,如沙”,更有詩句“燕山雪花大如席”,等等。但是謝太傅的問題卻是“白雪紛紛何所似”,關鍵在“紛紛”這個詞上面,是“紛紛揚揚的白雪”,不是其他樣子的雪,所以說它像柳絮,比說它像撒鹽更貼切一些。
而筆者認為謝朗是“答非所問”的理由就在于這個故事里還有一種雪,這個雪和謝太傅問題里所限定的“紛紛白雪”是完全不同的,它就是“雪驟”。什么是“雪驟”?就是說雪下得很快,也就是說“驟”在這里不能簡答地解釋為“大”。
“驟”在不同的字典里的解釋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四角號碼新詞典》(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九次修訂重排本,1982年12月第九版,第579頁)里有三個義項,其一是“馬奔馳”,其二是“急速、突然”,其三是“屢次”。在《新華字典》(商務印書館出版,2004年1月第10版,雙色本,第633頁)里有兩個義項,其一是“快跑”,其二是“急,疾速,突然”。在《說文解字》(清代陳昌治刻本)里的解釋是“馬疾步也”。在人教版《語文》教材里,也注釋為“急”。所以,筆者認為這里的“驟”字應該解釋為“疾速”或者“很快”,也就是說“雪驟”就是雪下得很快。
根據生活常識,“紛紛揚揚的雪”的形態應該是漫天飛舞,而絕非下得很快的雪。生活中有沒有下得很快的雪呢?有!
它(雪花)好像比空氣還輕,并不是從半空里落下來,而是被空氣從地面卷起來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黃昏時候的成群的蚊蚋,像春天流蜜時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飛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著人身,或擁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
——魯彥《雪》
雪來了,污穢的大地也會變成潔白;雪來了,茅廬草舍也會變成水晶宮一樣地好看。葉脫殆盡的枯枝因雪成了玉樹一般的美麗,梅花會因著它的陪襯格外地有姿態,松樹會因著它的映發格外的英氣。而且雪是最聰明的乖覺的,正乘著人們賞玩還未有盡興的時候,它偷偷地就去了;它去了給人以深厚的余味與留戀,卻不使人有若何的感傷。它的來也多是無聲無臭,給人意料以外的快樂。至于它那下來時翩翩姍姍的飛舞,更非“撒鹽空中”或“柳絮因風”所能擬其百一的。
——瀟炳實《雪》
正如魯彥《雪》中所寫,雪的下降速度有快有慢,也如瀟炳實《雪》中所言,雪的形態千變萬化。生活中確實有落得很快的雪,而且這種雪更接近于雪白的鹽巴,而非隨風飄舞的柳絮。
再回到《詠雪》的故事里面,劉義慶用一個“驟”字來形容當時的雪,說明那雪下得很快,這樣的雪我們在生活中也是經常遇到,它應該屬于粒狀雪,形態方面更接近鹽的樣子。謝朗那天并沒有認真聽課,他當時被這種下落得很快的跟鹽巴一樣的雪景吸引住了,當謝太傅提問“白雪紛紛何所似”時,他聽到的問題卻是“白雪何所似”,所以他就脫口而出“撒鹽空中差可擬”。他的這個比喻和他眼前的雪景是一致的,也是很形象的。可惜謝太傅的問題不是這個,謝朗“答非所問”。同樣是兩個小孩子,兩個普普通通的比喻,并不能完全說明才華的高低,就像“彎彎的月牙像什么”一樣,你可以說它是船,也可以說它是豆莢,都對。千姿百態的雪當然也可以有千千萬萬種比喻,無分優劣。可是,當你在聽別人說話時,卻沒有認真聽,那就不一樣了。如小學六年級課文《學弈》,它要告訴孩子們的是:認真或者不認真聽,學習的效果完全不一樣。而《詠雪》要告訴孩子們的是:認真或者不認真聽,所體現的品德是完全不一樣的。也正因為如此,劉義慶才會讓謝道韞在書中留下自己的名字,從而千古流芳,這種待遇比歷代帝王的家眷的待遇要高得多,她們很多人都只有一個“某某氏”的代號而已。
綜上所述,謝道韞的比喻的確好,很形象,很生動,有一種奮進向上的精神。謝朗的比喻不好,但這種不好與答案的關系不大,如果謝太傅的問題變成“白雪何所似”,那么他的答案也挺不錯。可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光在于如何“說”,更在于認真聽。要認真聽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認真聽了我們就可以獲得更多、更準確的知識和信息,更重要的原因是認真聽是一種禮儀,是一種美德。不光老師的課需要我們認真聽,生活中與任何人的交流都需要認真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