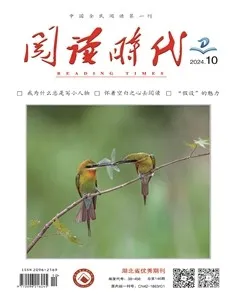書籍打開人的靈性
我們人生中特別需要一本這樣的書,它能打開你的靈性。
何為打開人的靈性?每個人的基因中都有原始人的生存密碼,原始人沒有那么繁雜的知識體系,最突出的是直覺和想象力。他們認為打雷、起風這樣的自然現象背后都有超自然的推手,他們創(chuàng)造出了很多神。
我們看《千與千尋》,驚詫于那個擁有無邊想象的世界。在現代社會,我們的大腦越來越理性,越來越知性,天然的想象力,如神話般造就生靈的想象潛質發(fā)揮不出來了,我們的生活過得太合理性了,限定了自己的想象邊界。
而書能幫我們打破這樣的邊界,特別是小說一類,你的內心會隨著文字跌宕起伏,時而緊張、時而放松。對未知的渴望以及內心的澎湃甚至會讓你一度懷疑自己是個傀儡,生命不歸自己支配,比如閱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有的人會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故事的氛圍中。
馬爾克斯年輕時喜歡寫作,但他一直覺得自己寫得不好,直到有一天看到卡夫卡的《變形記》,他馬上跳了起來了,“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從此以后他寫小說就放開了,自由了。人,特別是作家,當他在某一瞬間獲得內心的解放后,會打破以前生活中養(yǎng)成的習慣和認知。比如說語法的局限,主謂賓語如何使用的習慣,突破作品千篇一律的魔咒,讓作品本身的靈魂舞動起來。文學語言是自由的、沒有語法的,循規(guī)蹈矩寫出來的是語文,不是文學。所以馬爾克斯看到《變形記》時極為高興,后來他又驚喜地讀到了英國作家伍爾夫的意識流小說《達洛維夫人》,他的時間感、心理空間全部被打破,這兩部作品對他后來的寫作影響極大。
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也說過,菲茨杰拉德和雷蒙德·錢德勒對他影響極大,他們分別是《了不起的蓋茨比》和《漫長的告白》的作者。菲茨杰拉德的小說中充斥的悲傷性和音樂性,對村上春樹影響很大。但村上春樹大學畢業(yè)以后并未開始寫作,而是開了一間酒吧,直到二十八九歲時,他觀看一場棒球比賽,一個外國選手打出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二壘安打,就在那一瞬間,他的心靈仿佛也被擊中,突然萌發(fā)想要寫作的沖動,他認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應該是寫作。于是第二天村上春樹就開始寫作,最后寫出了《且聽風吟》等作品。
人一定要多讀書。如果村上春樹沒有閱讀積累,他看的那場棒球賽哪怕有再多精彩的本壘打,他的心里也不會有剎那的觸動。這就是好書的作用:它在你心里埋下一粒種子,埋下一種“打開”生命的可能。所以說生命中需要閱讀,需要一本能夠“打開”自己的書。
我喜歡去福州路的上海書城,每次進入書城,我感覺自己看到的不是書,而是一個一個鮮活的生命——伊索、莎士比亞、雨果,等等。在那里,你跟什么書相會,作者的聲音就會傳到你心里,當然,不是每個聲音都能打動你的心。但這就為你埋下了無限多的可能性,或許有一天“一個棒球”就突然打開了這種可能性。
閱讀會創(chuàng)造人生的另一種精彩,我們很多的潛在價值觀都是在閱讀中慢慢積累、悄然形成的。每個人都有特別的天賦,但真正能夠將它挖掘并實現的人并不多,我們很多時候就是缺少這樣一種“芝麻開門”的點醒。閱讀,閱讀合適的書,可能就是開門的那把鑰匙。

對我影響很大的一本書,是前蘇聯(lián)作家高爾基的《在人間》。《在人間》是一部長篇小說,現在很多年輕人覺得它是現實主義文學,很少有人看了,但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文革”的時候,學校不怎么能保證上課的時間,我就去新華書店學習。當時新華書店的書大部分都是紅色經典,高爾基是無產階級作家,所以他的書能夠上架。《在人間》描述了非常多的社會底層人民,主人公在底層流浪時,遇到了廚師、鍋爐工、妓女、仆人、面包師等形形色色的人,這些人多數很貧窮,言語粗魯,但這本書的可愛之處就在這里,它寫出了人性的善良,那些人的樸素,那些人的悲憐。所以直到現在,我仍然會不時拿來重溫一遍。
現在的教育,或者說主流思潮,太重視“馬太效應”,更多的關注點放在了“塔尖”,比如說頂尖的科學家、著名的作家、高考的“狀元”、奧運的冠軍、一線的明星等等。我們的視線都向上集中在金字塔尖的那部分人,但是與我們視線平行的那部分人才是社會堅實的基礎。比如我們乘坐高鐵經過的一個個隧道,隧道當然是某個高端人才設計的,可真正建設時也離不開那些普通的員工。
我們對普通人也應該懷有感情,金字塔越往底層基數越大,我們的感情越往底層反而越稀薄。有些人習慣性地將人分為三六九等,所以我們迫切地需要進行社會情感建設,迫切地需要在人和人之間建立一種有溫度的感情。如何建設?陌生的人如何能無礙溝通?人有被尊重的需求,情感要從尊重開始。所以讀書,讀一本好書,一本類似《在人間》這樣的書,能讓我們打開靈性,加深對人的理解、對世界的理解。
(源自《閱讀、游歷和愛情》,紫陌紅塵薦稿)
責編:小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