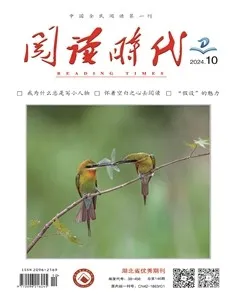我與金庸“華山論劍”
華山論劍,這個成語家喻戶曉,它是金庸發(fā)明的。
西岳華山,只要一想起這座山,我心里就天崩地裂。
我記不住數(shù)字,常常忘掉銀行卡密碼,家里的電話號碼也說不清楚。唯獨這座山。任何時候,只要有人問我華山北峰的海拔,我脫口就能報出來:1614.7米。
這刻在骨頭里的記憶,是從金庸先生承諾上華山開始的。
華山有靈
2003年時,金庸80歲,他從未上過華山。
那一年,我在陜西電視臺主持一檔談話節(jié)目《開壇》。彼時,金庸先生在寫《中國通史》,他說要用小說的方法寫歷史,讓年輕人更愛看。當(dāng)年8月,岳麓書院有一場金庸講座,我們的制片人去了現(xiàn)場,正式邀請金庸先生到陜西,上一趟華山。沒過多久他拎著一張紙回來了——金庸手書瘦金體,六個字:“金庸華山論劍”。這六個字后來變成了長達五個小時的現(xiàn)場直播節(jié)目,主會場在華山北峰之巔,我是現(xiàn)場主持人。
從金庸同意上華山,到節(jié)目播出,總共103天。總策劃白玉奇天天帶著我們開會,他狠狠抽煙,把手插進卷曲的頭發(fā)里抓一下,盯著我問:“李蕾,你說這節(jié)目怎么才能讓金庸老爺子滿意呢?”
的確是這樣,那還是媒體的黃金年代,做電視節(jié)目的人挺牛氣的,不大關(guān)心市場。我們也天然相信:只要金庸肯上電視,他說什么都有人看。
一個人憑著一支筆、一疊紙,硬生生創(chuàng)造出一個江湖,“有華人之處皆讀金庸”,在我看來,這真是白紙黑字最大的榮耀。
上中學(xué)的時候,我在數(shù)學(xué)課上偷看《射雕英雄傳》,老師過來“篤篤”地敲著桌子,我還叫他“不要煩”,因為正看到梅超風(fēng)要殺郭靖。那時候我沒想到,有一天,“金庸”兩個字會從封面上走下來,一直走到我眼前。
金庸到華山腳下是2003年10月8日。
直播的前一天,華山附近的賓館都被工作人員住滿了。我參加了全臺工作動員會,又一連串開完大活動會、技術(shù)會、策劃會、主持人會,回房間的時候已經(jīng)是凌晨2點了。按時間表,我要凌晨3點半起來化妝,7點前上到北峰,我站在走廊里晃水杯,心里想著我到底睡不睡呢?
凌晨一場陰雨,泥石流崩塌,上山的路斷了一截,大車過不去。當(dāng)時的總指揮梁和平連夜調(diào)動武警、公安、消防和城管,搬個板凳坐在現(xiàn)場監(jiān)工修路。清晨5點,陰雨停歇,道路恢復(fù),7點多太陽出來了,山巔云海升騰。
華山有靈。
一期一會
上午9點直播開始。我在北峰上戴著耳機,通過小小的監(jiān)視器看畫面,一群小朋友的少林拳開場,金庸獲贈華山論劍武林大會盟主印。他穿著一件手工考究的青布棉襖,開口說的第一句是:天氣這么冷,小朋友穿得這么少,我很感動。
上山路上,我們設(shè)計了“金庸闖三關(guān)”環(huán)節(jié),分別是“美人關(guān)”“美酒關(guān)”和“棋局關(guān)”。
“美人關(guān)”是挑選了不同版本的黃蓉扮演者,讓金庸來點評,金庸多給了周迅一個詞:靈動。他說很喜歡周迅版的俏蓉兒。我們之前想要邀請周迅和李亞鵬來現(xiàn)場,張紀(jì)中導(dǎo)演說:“這兩人正鬧分手呢,還沒公布,來不了,你們必須保密。我給你們帶個新人來。”他說的“新人”就是“神仙姐姐”劉亦菲,那時《天龍八部》還沒播,劉亦菲只有16歲,參加節(jié)目要監(jiān)護人陪同,是媽媽帶著她一起到了華山,為了討論媽媽漂亮還是女兒漂亮,我們的兩個攝像還吵了一架。
設(shè)想中的周迅和李亞鵬沒來,“美酒關(guān)”的守關(guān)人就定了演員巍子。金庸不是令狐沖,不喝酒,這一關(guān)準(zhǔn)備了太白酒。說好端起略沾沾唇就過關(guān),沒想到金庸端起來聞聞,說:“我知道陜西的西鳳酒很有名的。”直播啊,這個大廣告打得也是不容反駁。節(jié)目播完西鳳酒就找上門來,貼了廣告,還專門出了一款白酒,叫“華山論劍”,這是后話。
華山上有個極險要處,叫“下棋亭”,相傳宋太祖趙匡胤和陳摶老祖在這里下棋,差點輸了江山。我們請來“棋圣”聶衛(wèi)平在這里等金庸,一見面,金庸就拱手,說“不敢不敢,怎能與‘棋圣’比試”。
從下棋亭再至北峰之巔,索道之上有一段狹長的臺階路,金庸走不動,是用滑竿把老先生抬上去的,直播沒播。若干年后有朋友到華山旅游,打電話告訴我:“我們坐滑竿,人家說他是抬過金庸的。”
華山北峰面積不大,長著幾棵模樣清奇的松樹。立起一塊大石頭:金庸華山論劍。金庸就坐在這塊石頭前,分別與魏明倫、張紀(jì)中、楊爭光、孔慶東論劍華山。當(dāng)年時間緊張,做了塊假石頭,看起來是石頭,其實是石膏泡沫。機器設(shè)備、電線軌道、流動廁所、椅子道具,各種零零碎碎,還有我們喝的水和這塊假石頭,都是當(dāng)?shù)乩习傩毡成仙降模恢蕾M了多少人力。
在華山山頂,我問金庸:“您看自己的書有三次大哭。第一次,《倚天屠龍記》,寫到張無忌和小昭離別,您哭了。第二次,《天龍八部》,寫到蕭峰一掌打死阿朱,您哭了。第三次,《神雕俠侶》,楊過和小龍女相約16年后斷腸崖下相見,楊過等到太陽落山,小龍女沒來……您也哭了。現(xiàn)在再看這些片段,您還會難過嗎?”
“難過的。”他說:“你這么說的時候,我就已經(jīng)難過了。”
那一瞬間,大團大團云海從懸崖一側(cè)呼啦啦升起來,雪白如畫,光可照人,所有人都塞住了,不說話,我?guī)缀跤醒蹨I要掉下來。孔慶東忽然打個岔:“別老說這些讓人難過的,我們說點別的,說點別的。”
后來,我才知道那一刻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跡。最難的事情,不是哭出來,不是哭不出來,是不能哭出來。這幾乎成為我性格的一部分,有人指責(zé)我決絕——如果你認識當(dāng)年的我,也許就會原諒現(xiàn)在的我。
大約是2005年,金庸帶著太太來西安游玩,我也被叫去陪他們吃飯,還一起觀看了老腔和皮影。我悄悄跟金庸說:“好想被您寫進書里哦。如果我在您的書里,會是誰呢?”他絮絮叨叨地回答:“生得好看的女孩子不要聰明,聰明了就任性一點才好,不要太懂事才有人疼愛,不要去我的書里。”
我當(dāng)時不懂他的話,這么些年,也從未對人說過。
“華山論劍”之后,金庸送我一本書,是一本《俠客行》。扉頁上寫著:李蕾女史,華山之巔,談情論俠,平生快事!
這一場江湖大夢,一期一會,此生不再見。
(源自《新民周刊》,紫陌紅塵薦稿)
責(zé)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