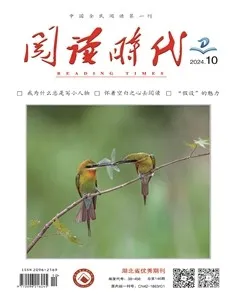離騷的“騷”是什么
楚辭所有篇章里出場率最高的,不必說肯定永遠(yuǎn)是《離騷》。從漢代至今兩千多年,無數(shù)學(xué)者提出了自己對(duì)“騷”的見解。
司馬遷是最早解釋離騷一詞的學(xué)者,《史記·屈原列傳》稱:“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認(rèn)為“騷”就是“憂傷、憂愁”之意,但沒有說為什么,也沒提“離”是什么意思。東漢史學(xué)家班固則進(jìn)一步解釋:“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認(rèn)為離是“遭逢”的意思,離騷就是遭逢憂傷。東漢文學(xué)家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解釋為“離,別也。騷,愁也”,如此,“離騷”就成了“別愁”。近代楚辭專家游國恩則認(rèn)為,離騷是“楚國曲名《勞商》的異寫”,則離騷大概屬于曲牌一類,沒有什么明確含義。
這眾多的假說里,“曲牌”說被訓(xùn)詁學(xué)否定,“別愁”說與原詩文意不合。“遭憂”說是其中比較說得通的一個(gè),而且司馬遷的時(shí)代離屈原不過百余年,因此也多被今人引用。
“離”字解釋為遭逢還好說,畢竟“離”可以通“罹”。直到今天,現(xiàn)代漢語還會(huì)用“罹難”一詞表示“遭遇死難”。可“騷”在古文中從來只有“騷擾、騷動(dòng)”的含義,只有楚辭這一處表“憂愁”,實(shí)在有孤證不立之嫌。而且從司馬遷“離騷者,猶離憂也”的“猶”字看,他也不確定這么說就對(duì),只敢用“猶如、就像”這類詞模糊解釋一下。
直到20世紀(jì)60年代,湖北江陵望山一號(hào)戰(zhàn)國墓,出土了一批楚簡,其中有占卜墓主人是否生病的內(nèi)容,用詞為“大‘又蟲’”。這里的“又蟲”是一個(gè)字,寫作上又下蟲,現(xiàn)代學(xué)者將其隸定為“蚤”字。
到了1993年,湖北荊門又發(fā)現(xiàn)一座珍貴楚墓,其中出土了著名的“郭店楚簡”,內(nèi)容甚至包括迄今為止最早版本的《道德經(jīng)》,一舉否定了“疑古派”認(rèn)為《道德經(jīng)》系漢代人偽造的假說——而郭店楚簡中除了道家典籍,更多的是儒家典籍,有一篇整理者定名為《尊德義》的,其中第28簡也出現(xiàn)了“又蟲”字:德之流,速乎置“又蟲”而傳命。
只看上下文,很難確定這個(gè)“又蟲”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在傳世典籍中正好有可以對(duì)照的文句,《孟子·公孫丑上》:“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由于有文獻(xiàn)對(duì)讀,基本能確定“又蟲”這個(gè)字,讀音應(yīng)該與“郵”相通。學(xué)者們因此認(rèn)為,該字是以“又”為聲符的形聲字,和作為會(huì)意字的“蚤”顯然不同——蚤字上面的“叉”,其實(shí)是一個(gè)手,表示以手抓蟲。其名詞形式就是蚤,動(dòng)詞形式便是“搔”。
再回過頭去看江陵望山楚簡的字,顯然也應(yīng)該讀為“郵”才對(duì),而郵字在古文中又經(jīng)常通作“尤”。可巧,“離尤”恰好是楚辭中多次出現(xiàn)的詞組,且就在《離騷》篇中也有,便是那句著名的“進(jìn)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fù)修吾初服”——這里的“尤”是過錯(cuò)、怨恨的意思,這個(gè)含義還保留在今天的成語里,比如怨天尤人,尤就是怨恨,歸咎之意。字義演化的鏈條或是:過錯(cuò)(名詞)—把過錯(cuò)歸因于,歸咎(動(dòng)詞)—怨恨或責(zé)怪(動(dòng)詞)—怨恨或責(zé)怪(名詞)。
由此學(xué)者們得出結(jié)論:在戰(zhàn)國楚文字里,有一個(gè)以“又”為聲旁,可表示“郵”或“尤”的字。但這應(yīng)該是楚國獨(dú)有的寫法,秦國不存在這個(gè)字,長得最像的是“蚤”字。秦國滅楚后大肆焚書,戰(zhàn)國楚辭作品一度中斷流傳,直到西漢初年,才又通過各種搜集發(fā)掘重見于世。漢初人整理楚辭,一定會(huì)將楚文字轉(zhuǎn)寫為當(dāng)時(shí)通行的秦漢隸書。可以想見,在這個(gè)過程中,假如《離騷》的“騷”字原本是寫作“又蟲”,漢人根據(jù)自己的用字習(xí)慣,很容易將其誤認(rèn)為“蚤”字。而“離蚤”又完全讀不通,于是又加了一個(gè)偏旁,就被抄成了《離騷》——因此“離騷”的本義,應(yīng)該與“離尤”相同,即“遭到責(zé)怪”。
(源自《南方周末》)
責(zé)編: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