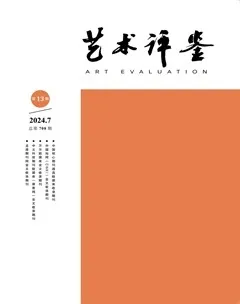南宋《瀟湘八景圖》禪意研究
【摘 要】《瀟湘八景圖》長久以來一直受到歷代藝術家的關注。它以湖南瀟湘地區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為題材,不僅在藝術上具有較高的價值,還蘊含著深遠的禪意。首先,本文對南宋《瀟湘八景圖》的起源和發展背景進行概述;其次,從簡素、自然等方面來論述《瀟湘八景圖》中禪意的含義,揭示了景色與禪境之間的關聯性;最后,試圖啟發人們挖掘、傳承傳統文化的精髓。
【關鍵詞】瀟湘八景圖 禪意 簡素 靜寂 幽玄
中圖分類號:J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24)13-0049-06
南宋《瀟湘八景圖》系列山水畫是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珍貴遺產之一,其憑借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深邃的禪意,深受廣大藝術愛好者和研究者的青睞。研究這些作品中的禪意,不僅可以進一步了解南宋時期的藝術發展和禪修文化,還有助于深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禪宗藝術的認識和理解。本文旨在深入研究南宋《瀟湘八景圖》所包含的禪意,闡述其獨特的藝術特點、意境以及哲學內涵,從而更好地理解其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價值。
《瀟湘八景圖》主要描繪了古代湖南地區的八個著名景點,分別位于湘潭昭山、衡山清涼寺、衡陽回雁峰、湘陰縣城江、長沙橘子洲、洞庭湖、桃花源白鱗洲、永州城東郊。
南宋時期,北方大部分地區被金朝占領,宋朝只能撤退到南方,建立了以臨安(今杭州)為首都的南宋政權。這一時期的經濟相對繁榮,文化藝術也蓬勃發展。以繪畫為代表的文化藝術開始融入禪宗文化的思想和精神內涵,追求內心寂靜與超脫,表達超越世俗的境界,中國藝術迎來山水畫的巔峰。《瀟湘八景圖》以描繪瀟湘風景為主題,將山水與禪意相結合,體現了禪宗對自然、人生和心靈的獨特見解。畫家們以自然山水、靜謐村落等場景為背景,通過構圖手法和繪畫技巧,傳達禪修境界和思想。因此,南宋時期的政治背景、文化繁榮和藝術發展為南宋《瀟湘八景圖》的創作和禪意藝術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背景。
“‘禪’或‘禪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譯,原意是沉思、靜慮。”禪意是禪宗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被視為一種特殊的境界或體驗。禪宗是佛教的一個分支,強調通過打破思維定勢和超越言語概念,直接體驗無我本性的境地。禪意是一種超越形式概念的境界,它強調直接體驗和直覺洞見,超越常規思維的二元對立和邏輯推理。禪意的核心在于呈現當下,全身心地沉浸于當前的經驗之中,而非被過去或未來所困擾。它關注個體與宇宙之間的連接,體現了內觀與覺察的狀態。禪意的實踐主要通過禪修(坐禪)來達到,通過專注于呼吸、身心感受或觀察思維等方式,逐漸減少思維活動,進入內心的深度靜默和覺知狀態。
“日本禪學學者鈴木大拙把禪藝術歸結為有七個特征:不均齊、簡素、枯高、自然、幽玄、脫俗、靜寂,可以說是對禪畫研究的集大成理論。”本文將圍繞簡素、自然等方面來論述南宋《瀟湘八景圖》中的禪意體現。
一、簡素的體現
“逸者必‘簡’,而簡也必是某種程度的逸。”何為簡素?在筆者看來,簡素的意思就是將簡素一詞拆解為“簡”和“素”兩個字,“簡”就是簡單、簡化、少的意思;“素”則代表樸素、本色、未經修飾的意思。中國畫中,強調“簡”是中國古代藝術精神的主要特征,也是古代藝術家們一直追求的理想境界。在中國古代繪畫中,“簡”是一以貫之的藝術理念。“‘筆簡形具,得之自然’是‘逸’格的重要標志之一。”
第一,在筆墨的表達方面,其中最為代表性的是南宋畫家牧溪。牧溪在他的瀟湘八景中不追求山水的繁密復雜去體現山水的巍峨雄壯氣勢,而是追求在極簡寂靜中觀察山水萬象,將所看到的山水都盡可能地簡略化表現,在八景中的《煙寺晚鐘》一景中,煙云的籠罩之下,將所看到的塔殘影化,讓觀者體會其中的“禪意”,有意讓觀者去體會煙寺晚鐘里的“晚鐘”所帶來的陣陣鐘鳴;在《平沙落雁》中,表現了茫茫煙海中雁影的閃動,這種筆墨的殘簡巧妙地給觀者帶來一種靜寂的感覺,也是符合“禪”在畫中化繁為簡的一種體現。南宋畫家玉澗所創作的三幅作品分別是《遠浦歸帆》《洞庭秋月》與《山市晴嵐》。在這三幅畫中,玉澗采用一種“簡筆”和“殘墨”式的藝術表現形式,僅用幾筆勾勒出山石和樹木的形態,用筆簡練而充滿瀟灑。歐陽修曾提出“墨精筆簡但求意足”的觀點,強調“筆簡”是為了更好地表現超越“形似”的“意足”,從而增加畫面的張力,提高藝術表現力,使畫作呈現出獨具藝術家審美趣味的特質。相較于北宋時期繁密的畫風,這種簡練的筆墨運用代表一種創新。
第二,在物象的選取方面,南宋畫家牧溪、王洪、玉澗都選擇極少的物象。玉澗的《遠浦歸帆》《洞庭秋月》和《山市晴嵐》基本上是幾棵樹、幾塊山石、大片的云霧、水面所構成,而牧溪的《洞庭秋月》《平沙落雁》中更加只有寥寥的山、水、樹等類似極簡的物象。能夠體現出下文所要闡述的寂靜、幽玄,如果有繁雜的物象,則體現不出畫面的縱深和空靈之感,南宋山水畫家馬遠、夏圭就深知其中道理,故有“馬半角,夏半邊”這樣后來人的畫風總結,同時,物象的簡素也是“禪”在理念中對“簡”“空”的直接體現。沒有用過多冗余的物象與華麗的表現形式去描繪,無不體現了南宋畫家對于《瀟湘八景圖》中禪意的簡素理解。
二、自然的體現
南宋《瀟湘八景圖》對于自然的體現展現出禪宗對自然的崇敬和敬畏之情,以及追求與自然和諧的理念。
首先,畫家對自然的描繪。《瀟湘八景圖》以自然山水為背景,通過描繪山川、湖泊、漁船等元素,傳達出禪宗修行中追求與自然和諧的理念。畫中物象的姿態恬靜自然,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呈現出一種內外合一、心與自然相通的禪意。《瀟湘八景圖》中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相互交融,形成一種和諧統一的景象。畫中的山水、湖泊等元素都與人文活動密切相關,它們不是孤立的自然景觀,而是與人類生活緊密相連的。這種和諧統一的景象體現了禪宗思想中的“自然即佛性”和“人即佛性”觀念,表達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應該和諧相處的理念。
其次,瀟湘八景的描繪體現了大自然的不斷變化和流動。瀟湘八景的繪畫和相關詩作在時間表達上和諧呼應。八景題材本身就具有明顯的時間屬性,如“暮”“夜”“晚”“夕”等字眼,以及“落”“歸”“月”等詞語,間接地將景致引入日落時分。特別是“山市晴嵐”,其中的“晴”不僅指天氣,也隱喻白晝的時間觀念,因此這個景別是八景中唯一描繪白天景象的。總體而言,瀟湘八景的畫卷與詩篇在時間維度上形成了有機協調。在描述《瀟湘八景圖》中牧溪和王洪兩位畫家的表現手法時,可以發現兩者存在明顯的差異。牧溪偏好運用暮靄、光靄等手法展現出一種虛幻而意境深遠的效果,其畫面中云霧和煙氣彌漫繚繞。相比之下,王洪的畫面則更為清晰明快,給人以晴朗爽朗的感受。從玉澗的題畫詩來看,在《洞庭秋月》中他描繪了“四面平湖月滿山”的夜晚景致,在《山市晴嵐》和《遠浦歸帆》中也分別出現了“隱隱殘虹帶晚霞”和“帆落秋江隱暮嵐”的字句,這些都暗示著作者對瀟湘夜色的特別青睞。
再次,筆墨的自然。在牧溪的《遠浦歸帆》和《漁村夕照》中,對比前面所提到的《煙寺晚鐘》《平沙落雁》這兩幅畫所表現的手法是完全不同的,《煙寺晚鐘》和《平沙落雁》更像是用工筆的暈染表現出來的,而《遠浦歸帆》和《漁村夕照》則更加寫意一點,在畫面中可以看到兩幅畫中甚至找不到毛筆所運用的筆觸痕跡,更像是筆腹中飽含水分在畫面上拖過去的樣子,用筆十分自然,瀟灑隨意。絲毫看不出有刻意表達形體之意,讓水流自然躍動在畫面之上,這樣的表現顯然更加靈動趣味,同時水墨的萬千形態也與千姿百態的山川、氣象、水流相輔相成,運用筆墨的自然凸顯自然界的“自然”。再看玉澗的瀟湘八景作品,玉澗在用筆上更加放松灑脫,其會用自然的筆觸表現自然的造型,通常是用淡墨意筆第一遍作畫,接著用濃墨潑在未干的淡墨上,使得濃墨能夠在淡墨中隨意流動擴散,暈染效果也更加自然,產生一個個意想不到的物象,同時濃墨的點綴使得畫面更加富有層次,也間接使畫面具有節奏。在現代山水畫作品中,有潑墨、潑彩、水壺灑水、撒鹽等各種技法,運用這些技法的不確定性去表現自然,實際上也有一定的禪宗因緣暗含其中。
最后,自然元素與人物的結合。《瀟湘八景圖》中人物的活動與自然元素相互交融。牧溪《漁村夕照》中的漁船、《煙寺晚鐘》中的寺廟、《洞庭秋月》中的漁人,還有玉澗在《洞庭秋月》中的房屋,畫中人物可以是山間的隱士、田間的農夫、湖邊的漁夫等,他們與自然環境的結合展現了禪宗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在他們的畫面中,不難發現有大量漁船獨飄于湖面之上,也暗示了畫家對于自然的向往,追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古人對漁船這一物象是有特殊文人情結的,描寫漁船誤入桃花林,也是古人對自然美好環境隱居的一種向往。王洪的名作《漁村夕照》以自然恬靜的景致為主要描述對象。畫面中,傍晚的農村煙霧環繞、霧氣彌漫,一名君子坐于山間,背對道路旁的灌木叢,面向火爐或窯爐。周圍的群山峻峭而茂密,高聳入云,呈現出極為復雜繁復的景象。在煙靄繚繞的江面上,一名船夫正駕駛著小船緩緩航行,船頭有人靜靜坐立。岸邊的林木掩映下,隱約可見漁船停靠,捕獲的魚類正在出售或與附近酒家交換酒水,構建出一幅理想自然生活的美好場景。作者對鄉村生活的向往通過這一靜謐唯美的情境得以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三、靜寂的體現
《瀟湘八景圖》以靜謐與平和的場景為主題,通過描繪大面積平靜的水面等靜止情景,傳遞出禪宗修行追求內心的寧靜和平和的含義。這種寧靜的氛圍引導觀者放下雜念,沉浸于內心深處的靜謐狀態。
第一,畫面中大量留白。留白就體現在畫面中大量的煙霧、水面、云氣等物象上。在兩宋的山水畫中,不難發現水面占整個畫面比重是相當高的,南宋《瀟湘八景圖》更是以大面積的留白為特征。進入南宋時期,當代許多文人對國家的未來憂慮。《瀟湘八景圖》描述了廣闊的水域和稀疏的山石樹木,傳達出一種悲涼凄慘的情感。這種憂傷的情緒在畫家心中積累日久,最終凝結成獨特的殘山剩水的繪畫風格。在宋代,許多文人畫家喜歡隱居山林,以水為景建造居所,以泉水為樂,以此追求從水中獲得的平靜與閑適。在構圖方面,大面積的留白使得山石更加突出,也算是一種映襯作用,用樹木的隨風飄動襯托出水面的寧靜,同時也能夠展現出煙波浩渺,空靈的瀟湘。禪僧玉澗的作品《山市晴嵐》就將水面與煙霧描繪得渾然一體,既表現了瀟湘的靜遠寂寥,而且使得畫面出現一種“空靈縹緲”的境界,宗白華先生說:“美感的養成在于能空,對物象造成距離,使自己不沾不滯,物象得以孤立絕緣,自成境界。”他將“空”與“舍”看成藝術表達的最高境界,認為“由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實,然后宇宙生命的一切理一切事無不把他的最深意義燦然呈現于前。”這也是禪僧對于禪學文化素養的一種外化體現。
第二,畫面中的物象體現了靜寂。在牧溪的《平沙落雁》中,一排排落雁消失于天際盡頭;前灘上孤寂的四只大雁,用這種以動襯靜的方式,用落雁與地上野雁這樣的生命之“動”體現整個瀟湘氛圍之“靜”。同時玉澗《洞庭秋月》與牧溪的洞庭秋月中都有人類散落的房子,給人以幽居,隱居之感,頗有一種“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的孤寂之感。在此基礎之上,無論是牧溪、玉澗,還是王洪的畫面中都大量描繪了漁船這一物象,在上文提到,古代文人都有漁人情結,暗喻自己對美好自然、隱居田園生活的美好向往,但同時,古人也喜歡將漁人與孤寂聯系在一起,早有唐代詩人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將釣魚的人和孤獨的船行駛于寒冷的江面之上,也有宋代陸游蘇軾的“一竿風月,一蓑煙雨”,“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孤寂、獨隱、脫俗的感受。畫家描繪的漁船頗有古代詩詞之感,不光在空間的表現上帶給觀者靜謐之感,更在漁船之上帶給觀者心靈上的孤冷、清寂之感。
四、幽玄的體現
幽玄一詞來自日本美學的三大理念,即“侘寂”“幽玄”“物哀”,幽玄為幽深玄妙、幽昧、昏暗,有幽深玄妙之意,通常附有玄虛的禪學哲理。
第一,從畫面中的構圖來看,南宋《瀟湘八景圖》大部分的形式為長卷平遠式的構圖,其中又有一些深遠的意蘊在里面。“平遠”一詞來自郭溪的《林泉高致》中的理念,意為自近山而觀遠山后,平遠相較于其他兩種,平遠更加適合表現縹緲含蓄的意境,觀南宋《瀟湘八景圖》,都是以前景與中景水面及遠景后山組成,以南宋畫家牧溪的《漁村夕照》舉例,大量的湖面與遠山的霧靄交融在一起,前后縱深感十分強烈,再加上霧靄的留白,給觀者無窮無盡的想象空間,既有空間上的幽深,又有體悟上的玄妙;再看玉澗作品《遠浦歸帆》,寥寥幾筆就給人一種空間上的想象,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人間仙境,既有人類生活的痕跡,又有一種脫離世間的場景與其巧妙地留白創造出幽遠玄妙的意境,使得觀者產生無窮的遐思。綜上所述,雖然南宋《瀟湘八景圖》并非以幽玄為主題,但其中的景色和意境仍能與幽玄的內涵相聯系,通過自然景觀的描繪和境界展現,傳達出一種寧靜深邃的審美情趣和超越凡俗的境界感。
第二,《瀟湘八景圖》還融入文學元素。通過圖中的詩句,以及與詩詞的互文和呼應,使得作品更具有文化內涵和情感表達。這種詩意的表現方式營造了作品的幽玄氛圍,使得觀者在欣賞的同時,也能體會到其中蘊含的深意。從畫面境界的表達中可以發現,上文提到的玉澗所作的《瀟湘八景圖》中,諸幅作品均呈現出晚景幽怨的意境。例如,《瀟湘八景圖》中“四面平湖月滿山,一阿螺髻鏡中觀”一詩,將明月比作阿螺,水面作為鏡子,凸顯出“鏡中明月”的玄妙情懷。《平沙落雁》則描繪了雁群如點點墨跡,即將融入遠處蘆葦叢的暗淡景象。《瀟湘夜雨》以“漲水痕”暗示“黃昏雨”,營造出夜色下“無處尋覓”“難以招魂”的幽怨氛圍。《山市晴嵐》和《遠浦歸帆》亦有“殘虹帶晚霞”“帆落秋江隱暮嵐”的晚景描寫。由此可見,玉澗的《瀟湘八景》多以優雅沉郁的晚景為創作主題。
五、脫俗的體現
明代畫家董其昌曾在其畫論著作《南北宗論》北宗以“漸修”為核心的思想,而南宗以“頓悟”為核心的思想,所以將畫分為南宗和北宗兩大派別,董其昌本人也是更加青睞南宗的文人畫,因為南宗的文人畫格調要比北宗的院體畫格調要高。文人畫與禪畫都追求的是一種精神境界,雖然文人畫與禪畫有非常大的區別。在此不一一贅述,在追求的境界領域,兩種派系是大同的,例如元代南宗文人畫家倪瓚的作品《漁莊秋霽圖》和南宋《瀟湘八景圖》的構圖,意蘊都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五代南宗畫家董源的《瀟湘圖》也對南宋《瀟湘八景圖》的建構具有一定的影響。
在筆墨方面,文人畫以繼承為主,書畫同源,大多文人畫家的書法功夫都是非常厲害的,但是禪畫更加追求一種自我創新,清代四僧之一的石濤就有自己的一套用筆技法,再反觀玉澗的作品,在當時也是一種極其具有創新性的筆墨。牧溪的畫面運用潑墨減筆畫法,勾勒出恣意瀟灑的景致,沒有雄渾迅疾的氣勢,用筆緩慢而從容,如同輕撫云霧,墨色淡淡而淺。追求在簡潔、寧靜的表現中展示千變萬化,將所有的場景物象簡略化,讓云山相融,寺廟、漁船、屋舍、樹梢虛實交映,仿佛真實與虛幻的結合,就像瀟湘山水禪境一般浩渺而遙遠,宛如夢境般。《瀟湘八景圖》以自由放縱的筆法展現著恣意瀟灑的風采,墨色的濃淡對比鮮明,構圖簡潔而廣闊。其背景大量運用留白,以凸顯水面的廣袤和云霧的彌漫。遠處的山巒在云霧中相互交融,微光閃爍,細細品味之中仿佛時間停止。畫中的漁人和農夫也融入玉澗的氣息,與山水融為一體,整幅畫卷散發著瀟灑靈動、清曠邈遠的氛圍。
就圖式而言,以宋代王洪的《瀟湘八景圖》為例,瀟湘山水畫以南方江河地區的景色作為其基本素材。在這些畫作中,畫面常常不離煙霧彌漫、廣闊的江域或平靜的湖面,以及平緩蒼郁的山石等元素。此外,橫構圖手卷的形式被廣泛采用,因為它最能夠表現南方平遠山水的特點。盡管在南宋時期豎構圖也開始出現,但“平遠”的空間結構始終貫穿于瀟湘山水畫中。在技法方面,常用的手法包括渲染法,通過暈染水與天空,畫面的虛實運用巧妙,而山石的勾線往往采用省略的方法,以模糊的筆觸來表現邊緣。大塊的留白也常被采用,以營造寬闊而寧靜的氛圍,引發觀者遐想。墨法上,與北方山水畫濃烈深刻的特征不同,瀟湘山水畫的墨色常常清淡而簡約,更加注重營造意境。
在境界方面,禪畫也更加脫俗,文人畫已經相較于傳統寫實山水更加脫俗,因為自王維起,引詩入畫的觀念開始興起,文人畫更加追求將詩詞里面所描繪的境界與山水畫相結合,通常將自己的個人情操與自己的抱負理想借景抒情,但禪宗主張“真相無相”有點類似于“大象無形”“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感覺,同時禪宗又有著緣境觀空的理念。如果說文人畫是心與象的結合,那么禪畫就是更注重用心去作畫。現在看到玉澗與牧溪所描繪的瀟湘八景中大量的留白運用,各式各樣的點景所創造出來的境界對后來的元代山水畫家倪瓚都有十分重要的啟發,這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視覺上的禪宗空觀的藝術呈現,更是心靈上的對禪意的思考與洗滌。
南宋《瀟湘八景圖》將禪宗文化精髓與自然山水和禪修心境相融合,展現了獨特的禪意藝術魅力。該作品所描繪的自然元素,如:山水、云霧、煙波等,不僅是對自然景觀本身的描述,更蘊含著豐富的禪意符號與隱喻意義。藝術家運用細膩的繪畫技法和隱喻手法,傳達了禪修心境的啟發與引導。同時,研究也發現,這些作品中深深體現了禪修精神。創作過程中,藝術家深受禪修心境的影響,通過繪畫技巧和細節描繪,將禪意融入其中。這種禪修精神的呈現,不僅體現在藝術家對自然景色的把握上,更體現在作品中觸動觀者內心的力量。
六、結語
總體而言,對于南宋《瀟湘八景圖》禪意的研究,不僅有助于人們全面把握這些作品所傳達的禪修精神和美學觀念,更能深化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禪宗藝術深厚底蘊的認識。這些作品以獨特的藝術風格和禪意表達方式,彰顯了其中所蘊含的禪境之美。通過深入研究,使人們對禪意在藝術創作中的應用和影響有了更加透徹的理解。未來的研究或可進一步探討禪意的深層內涵,結合更多藝術作品進行比較分析,以進一步拓展其在藝術領域的研究和應用前景。
參考文獻:
[1]顧致農.禪思系丹青——以貫休為代表的禪畫[J].新美術(中國美術學院學報),2006(03):78-79.
[2]梁松娥.從中國向韓國的瀟湘八景圖研究——論韓國瀟湘八景的圖式[D].北京:中央美術學院,2013年.
[3]邱晨.法常繪畫藝術研究[D].蕪湖:安徽工程大學,2022年.
[4]鄧紹秋.借景寓意 緣境觀空——辨析文人畫與禪畫之異同[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05):85-89.
[5]施锜.南宋“瀟湘八景圖”的時間與光影之美[J].中國美學,2021(01):145-163.
[6]張聰聰.宋代山水畫中“水”的表現特征研究[D].蕪湖:安徽工程大學,2021年.
[7]李靜.南宋禪宗繪畫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17年.
[8]郭甜甜.淺談宋代瀟湘山水畫引發愁思緣由[J].戲劇之家,2022(29):188-190.
[9]馮顯斐.倪瓚山水畫中的“簡逸”格調對山水創作實踐的啟示[D].昆明:云南大學,2013年.
[10]張萍萍.論南宋禪宗水墨長卷的藝術風格與發展脈絡[D].濟南:山東大學,2021年.
[11]王雙.瀟湘山水圖式研究[D].南京:南京藝術學院,2022年.
[12]劉迪.圖式與意象[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學,2020年.
[13]呂道建.五代、兩宋瀟湘主題山水畫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