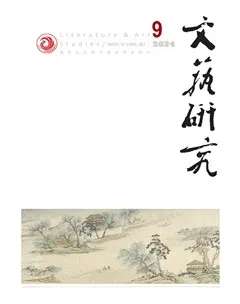現代性視域中的鄉愁:德國早期浪漫主義的“思鄉情結”
德國早期浪漫主義作為西方審美現代性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思潮,其“思鄉情結”(nostalgia) 是值得關注的議題。有別于啟蒙運動對無限進步觀念的確信,浪漫主義者追求遠逝的“故鄉”以獲得心靈的定向,此處的故鄉并非地理意義上的具體場所,而是聯結著浪漫主義者生存體驗的想象的歸宿,其思鄉情結超越有限時空而成為一種永恒的渴望。厘清德國早期浪漫主義的思鄉情結,有助于理解現代性所造成的無根性的主體生存境遇,進而反思現代性困境,并回應后現代主義危機。
一、思鄉情結的動因
思鄉情結是德國早期浪漫主義的重要表征,其產生有著深刻的歷史語境,承載著“與人類實際處境相關的各種意義”。啟蒙運動以理性為基礎,展開對世界的去神圣化,強調宗教、自然、歷史等并非崇高的神圣創造。霍布斯認為宗教源于人性,人因對自然現象的無知而產生恐懼心理,借由想象的無形之力把握自然世界,依附此種力量并賦予其榮耀。休謨指出,合理性的自然不是源于超越性的上帝,而是可以被觀察和認識的機械之物,神性自然向機械自然的轉向表明,理性從論證信仰的工具變成信仰本身。伏爾泰揚棄神圣歷史的框架,將自然科學的理性世界觀作為人類歷史發展的唯一標準,借鑒歷史經驗中人性的永恒而普遍的原則,建構今勝于古的世界歷史。啟蒙運動有賴于知識之光對神圣世界的祛魅,源于神圣世界的敬畏感使人相信萬物皆有靈性,并且萬物因“圣顯”(hierophany) 獲得自身存在的意義。此種圣顯既不受因果律制約也無固定之所,它區隔神圣世界與世俗世界,保證萬物自身的獨特性和自由。
德國早期浪漫主義繼承敬虔主義(pietism),相信世界具有令人敬畏的神圣性。政治權力對路德宗教會的僭越使后者失去“屬靈”的特質,同時后宗教改革時代的神學家援引亞里士多德哲學來解釋“屬世”的世界,對此,17、18世紀的德國社會興起以復興原始路德宗教為己任的敬虔主義。敬虔主義運動以施本納、弗蘭克、親岑道夫等人為代表,強調作為歷史與啟示之承載者的圣經的重要性,探求圣經的文字義與屬靈義。他們認為,救贖的核心不在于教會,而在于重視“信”與“行”的重生思想,只有信仰上帝并與基督形成屬靈團契的關系,才能得享上帝的恩典、獲得成圣的可能。敬虔主義作為一場屬靈的運動,借助但又超越語言和邏輯,主要以神話、象征等方式闡釋神性實在等不可言說的思想,這也使其成為浪漫主義的精神源頭。
浪漫主義者借由對不可見世界的敬畏感來糾正過度偏重理性的啟蒙主義。奧古斯特·施勒格爾指出,“啟蒙”并非對“光明”的神性象征,而是在光明中一覽事物的必然性和明晰性,黑暗是“生活的魔力賴以存在的基礎”,但“啟蒙運動則缺乏對于黑暗的最起碼的尊敬”。龔德羅得在《遠古時代與新時代》一詩中認為,遠古時代仿佛是一條狹窄不平的小道,既通往天堂也通往地獄,而在啟蒙時代,“天堂被推翻,深淵被填平,理性覆蓋,一片坦途”,信仰的高地被踐踏乃至摧毀。諾瓦利斯則認為,法國人以“光”來命名啟蒙運動這一偉大事業,“消除神圣之物的每一道痕跡,用冷嘲熱諷打消對一切崇高的事件和人物的懷念”,但這一事業違背人的天性,因為人之天性總是神秘莫測和詩意無限的,“塵世的生命發源于本真的內省”。
啟蒙主義作為一種實在性的思想運動,導致“思想喪失了自我反思的要素”,而浪漫主義者試圖回歸內心與傳統。諾瓦利斯指出,很多學者只會推理而不喜反思,哲學作為“對最真摯的反思之愛、對智慧的絕對興趣的一種證明”,是對歷史根基性的探索,只有通過創造性和否定性的反思,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弗里德里希·施勒格爾強調,詩意的反思能夠有力地沖破現實的束縛。荷爾德林亦將語言視為創造性反思的產品,詩人通過創造語言來改變世界。海德格爾在闡釋荷爾德林的詩歌時特別指出,語言作為一種奧秘建立了世界,語言“產生人,才給出(er?gibt) 人”,即語言是人之存在本身,“語言保證了——人作為歷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語言不是一個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種擁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本有事件(Ereignis) ”。
法國大革命也造成了浪漫主義者的深層退卻,他們把詩與哲學、散文、生命等融為一體,打破新古典主義詩學傳統所要求的藝術形式的陳規:他們在反抗傳統這一基礎上是認可法國大革命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爾將法國大革命、費希特《全部知識學的基礎》和歌德《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視為啟蒙時代最偉大的潮流,從人類歷史的高度禮贊法國大革命。費希特揭示出此世真正的幸福是自由的自我活動,把源自康德《實踐理性批判》的自由哲學與法國大革命相類比。他在《糾正公眾對于法國革命的評論》一書中,從語義學的唯心主義、歷史道德觀和對國家的無政府主義批判三個方面,論證法國大革命的合法性。然而,反法同盟失敗、法國大軍踏上德國領土等事件,最終導致德國知識分子“認為這場革命具有世界主義性質的幻想的破滅”。
浪漫主義者對待法國大革命的此種轉變,其原因既是法國大革命作為一種“根基性過去”(foundational past),如雅努斯一樣具有正義和恐怖兩幅面孔,更是法國大革命使浪漫主義者產生兩個層面的屈辱感,導致他們尋求一種內省的生活。一是由德法文化差距而來的屈辱感。三十年戰爭和正統路德宗教的墮落摧毀了德國精神,德意志民族文化退化成地方性的文化,而大革命之后的法國逐漸成為歐洲文化中心。浪漫主義者既將法國作為理想國家的范本,又強調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獨特性。二是由浪漫主義者與啟蒙思想家的身份落差而來的屈辱感,前者多來自中下層社會,后者多來自上層社會。這種落差使浪漫主義者既渴慕啟蒙思想家秉持的自由、平等、博愛理念,又厭惡他們現實中的浮華作派和階層分化。浪漫主義者試圖“放棄上路來克服道路上的障礙”,以緩解個體的不安和焦慮,尋求個體、民族的自由或獨立。
此外,工業革命所推動的城市化進程使人對故鄉的歸屬感逐漸消失。赫爾德從幽暗而模糊的感性出發,探尋主體生成的歷史。他認為,作為實體的“有機力量”是精神與物質之間的“中間概念”(Mittelbegriff),具有自然的可生長性,在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發展中獲得時空的規定。從此生物地理學的角度,他強調人類的歷史并非造物主的創造,而是人形塑了自身民族的文化。赫爾德以此拒斥以自然科學為代表的理性文化,他所言的民族的地理化揭示了人對故鄉的依戀感。卡斯帕·弗里德里希畫過的奧德修斯是一個典型的思鄉者,后者的鄉愁是希求返回實在的故鄉,他“將自己美好的生命(ai?n) 融入其中”。故鄉作為自我與環境交互作用的原初場所,承載著人的生存意義上的“風土”(Fudo),人正是在此地理化的風土中認識自身,“風土便成了人之存在將自己客體化的契機,恰恰于此,人也認識了自己”。然而,城市化不僅消解了人與故鄉的親密性,“‘最親密的感受’亦即基礎情調”,而且導致了人對神圣故鄉的僭越。此處的空間指的不是人的客觀生存環境,而是人與世界交往的場所。海德格爾通過考察物的本質,揭示“只有那種本身是一個位置(Ort) 的東西”,才能以場所的方式聚集天、地、神、人四重整體,使人感知四重整體的演繹,進而展開作為物之生產的筑造活動,最終讓自身棲居其中,而人的此種棲居是對四重整體的保護,即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諸神、護送終有一死者。
啟蒙運動對神圣世界的祛魅、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社會劇變、城市化對人與故鄉關系的消解,使人徹底淪為異鄉人,并抱持永恒的鄉愁,因而浪漫主義者將故鄉作為永遠的歸宿,不斷在還鄉之路上尋找理想家園。
二、思鄉情結的意涵
浪漫主義者力圖超越有限的理性世界、重返原初的神性世界,對故鄉的渴望促使他們不斷尋找一個可以棲居的中心、一個充滿神性的實體。神圣的故鄉作為世界的中心,被隱藏在無限的宗教、神秘的中世紀文化和本真的自然中。
浪漫主義者認為基督教是人性之完善和完美的表征,試圖通過宗教回歸神圣世界。對浪漫主義者而言,世界作為有生命的存在,并非外在的、超越性的理性神的創造,而是內在的無限者的精神所顯現的結果;有限的個體是“巨大的存在之鏈”的一部分,只有與無限者相融合,才能分享后者的本性、獲得生存的定向。赫爾德指出,知性是人類最高的稟賦,以探究因果關系為己任,而神則以其無形的隱匿性成為自然最初和唯一的原因。宗教是人性的最高表達,而且自然因源于神而成為至善至美的存在,人則依著善與愛崇拜自然,宗教便成為人心最大的滿足、最強有力的善和對他人的愛。荷爾德林認為,由于人的自然本質的超越性,人與世界處于一種無限而深情的宗教關系,歸于大全的宗教信仰使人超越有限的現實生活而獲得更高的自由,“一切宗教按照其本質將皆為詩性的/創造性的”。施萊爾馬赫認為,“宗教”(基督教) 是動詞,它既非思維也非行動,而是對“無限者和永恒者”的直觀,通過此種“絕對依賴感”,有限的個體與無限者徹底取消主客二分的對象性關系,在圣域中融為一體。
作為浪漫主義思鄉情結的核心意象,“藍花”富有宗教色彩。《奧夫特爾丁》中的亨利希發問“我們究竟去哪里”,得到的答案是“永遠在還鄉”。故鄉為詩人的思想抹上了永恒的色彩,即“藍花”的神秘、夢幻和憂郁。亨利希體驗了自然、生死、戰爭、異域、歷史和詩之后,最終明白這都是對故鄉的渴望,“始終讓人回想起藍花”。海德格爾認為,返鄉作為對本源的切近,具有神秘性和無限性,“他因此就在那里經驗到他要求索的東西的本質,然后才能經歷漸豐,作為求索者返回”。如果說此種神秘性和無限性表明了作為民族性與歷史性之“基底”(Fond) 的故鄉自行鎖閉的狀態,那么還鄉的過程實則是故鄉圖景的敞開。在此意義上,故鄉與大地(Erde) 有著趨近的內涵,“大地是一切涌現者的返身隱匿之所,并且是作為這樣一種把一切涌現者返身隱匿起來的涌現。在涌現者中,大地現身而為庇護者(das Bergende) ”。對“藍花”的渴望就是將自我融入無限的嘗試,是在心中復活基督教奧義的世俗化宗教追求,亦是異教精神中自我與自然的創造性力量合一的表現。
浪漫主義者期望重返中世紀以獲得家的歸屬感。赫爾德認為,在自然民族向文化民族的發展過程中,需要吸收、轉化先前具有養分的“有機力”,啟蒙理性是由傳統滋養而成的自然之果,“如果我們更進一步,武斷地劃定文化與啟蒙之間的界線,則我們是在迷霧中墮得更深,因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與啟蒙乃是不可分”的,中世紀的文化也就成為浪漫主義反思啟蒙運動的依據。蒂克和瓦肯羅德認為,中世紀藝術是神秘的象征,它更多表現了力量而非單純的技藝,后者是可以習得的經驗,但前者是人內在的無限精神及意志的表達。因此,浪漫主義者“首次把擁有中世紀城市、森林、古堡廢墟、王宮和礦山的法蘭肯地區,神化為德國浪漫主義的圣地”。奧古斯特·施勒格爾尤其喜愛中世紀的徽記,贊美其“把最不相干的東西,如星辰和花朵,撮合到一塊”,認為這不僅是騎士文化的縮影,更是與浪漫詩的“總匯”精神高度一致。
浪漫主義者對中世紀文化的向往集中體現為對哥特風格的喜愛。哥特風格不僅滿足了浪漫主義者對內心震撼的需求,也是中世紀超越世俗、聯結神性的文化象征。歌德認為,哥特式建筑風格表征著“人類創作與一個強大安寧卻又蔑視一切的時代之間的沖突”,它是人類超越性的體現。如沃林格爾所言,在哥特式建筑中,有“一種超人的力量把我們裹挾著,進入到無盡的意愿與渴望的迷狂、沉醉中”。哥特風格永遠處于一種運動狀態,尤為重視內在力量的表現,而非外在技巧的展示,“是焦渴不安的平靜……必須無休無止地奮爭前進”,這與浪漫主義的總匯詩(Universal Poem) 要求永遠變化的思想是一致的。此外,哥特建筑廢墟的破敗、神秘、陰森之感,猶如人的幽暗而模糊的感性世界,其作為非理性世界正是理性的基礎。
浪漫主義者也試圖回到神性的自然,以逃離啟蒙主義的壓抑。啟蒙運動把中世紀的神學目的論轉換為近代經驗-數學理性的自然知識論,理性化的自然脫離了神性的宇宙中心。浪漫主義者則將自然視為神性力量的生命的象征,物質的自然現象只是象征化的部分,而內在的神性世界是意義之所出的被象征部分,象征事件出自神圣之在場與人之見證的相遇。此種相遇不是假借主客二分的認識,而是以人的超理性信仰為中介,使有限的人與神性的自然相融合。康德借助審美判斷力所具有的情感愉悅的共通感,使個體可以用“自然像藝術”的比擬來重新審視自然事物的機械作用,以審美性質的敬重感將終極目的導向人自身,并且是作為自然-社會文化目的下有道德的人。與康德美學關注自然美相似,浪漫主義者認為自然的神性是自然美的根源。最初人與自然關系密切,神性的自然所顯現的美使人對自然萬物充滿著愛,從而消除了生命的痛苦和孤獨。在諾瓦利斯看來,人與自然是作為神性統一體而存在的,草木鳥獸、山川河流都擁有情感與神性,無際的大地是“諸神的居處和人類的故鄉”。荷爾德林在面對自然時,會感到“仿佛一種親密的精神為我張開臂膀,仿佛孤獨的痛苦融入了神性的生命”,但是啟蒙理性對世界的祛魅分離了人與自然,自然失去神性、人失去故鄉,“自然收斂了臂膀,我像異鄉人站在它面前,不理解它”。
浪漫主義者的思鄉情結是對具有意涵的逝去事物的想象與建構,他們追尋宗教的無限性、中世紀文化的超越性以及自然的神圣性,其目的在于超越當下有限的現實生活。返鄉行為本身并無內在的重要性,它是浪漫主義“反抗平凡、反抗當前現實的一張王牌,利用它的意圖是否定現在”。
三、作為返鄉方式的反諷
浪漫主義者將反諷(irony) 作為超越有限、追求無限的方式,這深刻體現在浪漫主義者將故鄉主觀化、將世界浪漫化的過程中。故鄉的主觀化是將故鄉的實在性轉化為內心的渴望,通過反諷把有限的現實轉化為無限的可能性。浪漫主義者在費希特的主體性哲學基礎上發展反諷理論,反諷成為不斷否定有限、回歸自我的無限運動。費希特以“自我”為絕對的、原初的存在,而“非我”作為自我對象性活動的產物,不斷處于復歸自我的運動中,反諷在自我與非我的雙向運動中得以產生。浪漫主義反諷亦受謝林自然哲學的影響,借由否定有限的理性領域來追求非理性領域。謝林認為,絕對先在的原初生命是“最完滿意義上的自然界”,人的自我意識來自并等同于這個原初生命,它“包含著萬物的最高的明晰性”。然而,人對這個世界的本原的超越并非自由和純凈的,而是與較低的本原相結合,后者作為原初生命的產物,本質上是無意識的、黑暗的存在。浪漫主義者將內心的非理性世界視為更真實的世界,即真正的故鄉,而外部世界只是內心的投影。回歸原初本我不僅意味著回歸內心,更是將“開端”認作最為本真的狀態。在浪漫主義者眼中,故鄉與世界的原初狀態一致,具有無限性與非理性。他們以反諷否定當下的有限性存在,促使非我不斷開啟新的有限性境域。當反諷完成對具體事件、人與物的超越時,又會產生新的反諷。浪漫主義的反諷超越言語層面,展現出非實在的故鄉的無限可能性。
由于故鄉的主觀化需要實在物作為寄托,浪漫主義者借由反諷找到了一種替代品,即超越“實在”范疇的“總體”。作為超驗之詩的總匯詩以“詩性統一”將世界浪漫化,浪漫主義以此重構神圣性的精神家園。“總匯詩”概念基于百科全書理論,“‘百科全書’或‘百科全書式’是早期浪漫主義論著中常見的術語”,它表征著學科、經驗世界乃至超驗世界的一種綜合性和整體性。弗里德里希·施勒格爾認為,語言和交流是不同學科之間最普遍的聯系,文學遂成為百科全書的中心和要義,“浪漫詩是漸進的總匯詩”,而總匯詩意在使“所有的形式和所有的材料交替地得到滿足”,這不僅擴大了詩的范圍,也將萬物詩意化,以加深世界的維度。總匯詩作為本體的詩,并不消除萬物自身的特色,而是將各種力量并置,產生無限的張力效果,各種對立的力量在其中不斷交替和超越。詩通過反諷將自身提升到哲學高度,達到完美的和諧。“哲學是反諷真正的故鄉”,反諷的終極特質即哲學,而“一切哲學不外乎是總匯性的精神”,總匯性精神也就是反諷的特質,通過否定使對立的事物走向綜合。借由反諷,總匯詩將有限的自身向無限的整體提升,從而達至一種永恒的詩性狀態。總匯詩因反諷的無限否定性和未完成性而處于不斷的生成變化中,“永遠只在變化生成,永遠不會完結,這正是浪漫詩的真正本質”,總匯詩于此成為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體。
與弗里德里希·施勒格爾的“總匯詩”概念類似,諾瓦利斯的“浪漫化”概念揭示了反諷的雙向維度。諾瓦利斯認為,浪漫化包含著對世界的質的強化,此種強化是質的乘方與開方、提升與降低的綜合。世界的浪漫化意味著以反諷將世俗世界神圣化,實現對崇高、神秘、無限之物的渴望;若面對崇高、未知、神秘、無限之物,則要反向將其浪漫化,世界在浪漫化的反諷辯證法中,獲得動態的平衡與和諧。此處的浪漫化不是絕對與純粹的存在,更不能達至超驗之境。世界的浪漫化所希冀的是無限中的有限,在有限中彰顯無限的存在。這表明反諷并非形而上的玄思,而是確保“一切事件和人……被作為游戲來看待,并以這樣的形式向我們展現生活的面貌”,使有限的生活向著無限的整體提升,對當下的否定轉為對故鄉的昭示。
浪漫主義的反諷不斷抬高主體的地位,同時詩人將總匯詩作為世界的本體,成為浪漫化世界的創造者和立法者。在諾瓦利斯看來,總匯詩作為世界的本體,建構出超驗的偉大藝術,詩人成為人類的精神與肉體的守護者,“以痛苦和刺激來實行統治……提升人并使人超越自己”。詩人又是先知性的存在,運用超常的能力沖破一切束縛,將世界詩意化。進一步說,任何人通過反諷都可以將自身提升至詩與哲學的高度。如施米特所言,主體運用反諷,“能夠把自身徹底變成整個宇宙的主人、變成科學的總體和藝術的總體”。在浪漫主義者看來,只有通過反諷的方式,哲學與詩“才能把所有各門學科和藝術注入靈魂并且統一成一個整體”,以此賦予日常生活以詩意。反諷作為“自我創造和自我毀滅的經常交替”,將個體置于個性與總匯性的交替,使他不斷意識到自身的有限性與無限性、現實與理想的沖突。要言之,詩人通過反諷將個體的現實生活投入一種趨于無限且與世界相似的生活,即將不同的生活方式引入一種綜合性的生活方式,作為個體的人可以“最熱切地、完全不停頓地、幾乎是貪婪地去參與一切生活”。浪漫主義者通過反諷形塑了自我與外界的交互,使整個世界浪漫化,并實現個體與現實的統一融合。
反諷是浪漫主義者不斷在更高的主觀層面上把握故鄉的方式,使審美超越世俗性世界而達至總體性世界。在反諷構建的浪漫化世界中,作為創造者和立法者的詩人成為家園的主人,最終實現無限的自由境界。
四、返鄉中的虛無主義
近代以降,哲學家對美的理解形成了顯與隱兩條路徑。顯性路徑受近代認識論影響,將美劃定為與知性相對的感性領域,從屬且受制于知性。笛卡爾認為,審美不具有客觀性,而知性擁有主體意義上的行動力,感性服從知性的引導;萊布尼茨認為,感性事實具有確定性,感性領域被設定為知識論范疇內的對象;在鮑姆加登看來,晦暗的感性認知可以借由“習練”與理性認知被清晰化,感性思維以自身的力量便能獲得真理,美的思維與人文藝術成為感性認識的高級形式;康德以判斷力整合想象力與知性,卻也導致自由的審美判斷受到知性制約。隱性路徑則將感性作為幽暗力量的游戲,以瓦解理性主體的實踐。赫爾德認為,美是人的靈魂的幽暗力量的體現,構成了“人的前主體,甚至反主體的力量”。在這種幽暗力量的游戲中,人在面臨不確定性的同時,突破法則和目的,使主體性成為可能。浪漫主義的思鄉情結尤為強調審美的神秘力量,將其作為世界運行的基礎,這也是彌合感性與理性的分裂、實現同一性的重要嘗試。更重要的是,浪漫主義把神性目的論與道德原則作為反諷的界限,對反諷進行了雙重限制,前者使審美獲得神性層面的統攝,后者承認道德參與審美的必要性。新古典主義者批評浪漫主義者缺乏道德觀念、具有非人化的傾向,但浪漫主義者實則強調,真正的趣味只有在道德力量和自主性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產生,他們認同的道德不是社會道德規范,而是個體的本真性道德。然而,從德國早期浪漫主義的發展結果而言,反諷的否定性使故鄉逐漸主觀化,思鄉情結蘊含著走向審美虛無主義的危險。
浪漫主義者雖然將故鄉作為情感與精神的寄托,但最終未能將其轉化為安放心靈與身體的實在性的家園。故鄉的非實在性使人走向內心世界,而現實中的個體已在不同文化場域下形塑出新的個性,有限的個體只能于精神層面無限接近故鄉,卻無法真正在“親密性”的意義上還鄉,故鄉由此成為虛無主義的表征。約納斯將虛無主義視為存在主義的危機,人因擁有反思意識和懷疑精神而不同于外部自然,“他的意識只能讓他在這個世界作為一個異鄉人存在,每個真實的反思都在講述這種荒涼的異鄉性”。浪漫主義者在思鄉情結中將自身視為異鄉人,不斷追尋逝去的故鄉,甚至希望將現有的世界改造成夢想的故鄉。在浪漫主義者看來,真實世界存在于古老而遙遠的異國他鄉、過去的宗教與文學、消失的夢與幻想、遠離塵世的本真自然,此種真實成為他們對故鄉的信念。然而,這終究只是一種暫時性的逃離,對異域風格的向往常常存留于幻想,對自然的喜愛因藝術化而遠離實際的自然生活,故鄉淪為無法證明的存在。未能滿足的懷古幽思使浪漫主義者試圖在內心喚起對故鄉的感覺,將思鄉情結轉化為主體的精神世界,而非時空意義上的寄托,“逃向自我、沉溺于自我,建立一個外在厄運無法侵入的內心世界”,內心世界的真切、私密使“人們情愿全然生活于它之中。它就是故鄉”。只有當故鄉存留于主觀的內心世界時,它才真正屬于個體自身。由此,故鄉成為一個觀念中的模糊而遙遠的符號,以滿足浪漫主義者的情感與精神需要。當浪漫主義者始終無法找到故鄉時,他們不免會厭倦乃至陷入虛無之境,“我們再沒有什么可尋求——/心已厭(饜) 足——世界空虛”。
浪漫主義返鄉的意義也因反諷的無限否定而逐漸走向價值萎縮。浪漫主義通過反諷實現世界的浪漫化,其出發點在于宗教衰落之后,以哲學與詩歌來填補宗教的形而上維度。浪漫主義者為了對抗世俗世界的價值虛無主義,以反諷進行價值創造,詩歌成為新的宗教,詩人成為上帝的代理者。有別于以往的宗教價值規范,浪漫主義的“上帝”無法提供可靠、穩定、普世的價值規范和精神信仰,“浪漫派拒斥那種進行審判的、道德化的上帝,而尋求在他們自己身上體現出來的上帝”。主體借由反諷創造新的價值,通過不斷否定自身的有限性,在更高層次上獲得新的歸屬感,一旦獲得滿足,他們又會開始新的否定和追尋。于是,浪漫主義的思鄉情結借由反諷而使故鄉變成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如果賜予浪漫主義者他們正在尋找的家園、給予他們談論的和諧與完美,他們卻會拒絕這樣的賜予”。在他們眼中,生命因世界的不可窮盡而只能無止境地尋找,反諷正是通過“永無止境地從反面對一切自身劃定界限的超越”,使追尋成為一種無止境的過程。
反諷作為詩歌中的一種思辨的樂趣,要求個體以強大的意志掌控世界,以一種趨向死亡的決心和勇氣去更新事物,融合對立之物,建立新的矛盾。但是,在不斷地調和與反復之后,反諷這一辯證運動的否定性力量消磨殆盡,如克爾凱郭爾所言,“反諷曾在狂妄的無限性中四下奔突,耗盡了精力”;科爾施密特亦指出,當兩個矛盾的概念同時出現于反諷時,“它便失去了絕對否定的分量。最后轉向創造分離存在與純粹虛無的可能性”。此種絕對的批判在文學中是反諷,在生活中則是死亡。雖然死亡意味著絕對的終結和真正的抵達,但浪漫主義者并不能借助詩而達到真正的死亡或絕對,浪漫主義的反諷最終成為“無根基性和相對性的證明”。盡管如此,浪漫主義者仍然沉醉于否定,因為只有反諷產生的不斷毀滅與建構,才能滿足浪漫主義者探索永恒的渴望。浪漫主義“作為一種主觀的機緣論,它沒有能力……使自己的精神本質客觀化”,一切主觀的美好愿景在喪失了批判性之后,成為一種心理慰藉,反諷所探索的真理在無限的否定中逐漸走向價值萎縮,它建構的神圣的形而上空間在不斷向上的推演中無處安放,追尋的主觀的家園亦不斷瓦解,這些都預示著虛無主義的產生。
浪漫主義的思鄉情結將故鄉視作一種“恢復神性的狀態”,但這種美好的愿景只能存留于記憶和幻想,成為永遠無法抵達的、“固化為典型的神話般的過去”。由于人的自由和世界的多樣性被淹沒在理性的光芒中,浪漫主義者試圖突破世界的局限性、恢復人性的完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爾指出,萬物的內涵和功用只有在無限中才能產生,“凡與無限沒有關系的,完全是空虛的和無用的”。對個體乃至所有人類而言,人的基本力量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其起源和終極目的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只有將自身力量納入無限,才能實現完整性。浪漫主義者以總匯詩所蘊含的宗教精神來超越當下、追尋無限,因為“詩只追尋無限,蔑視塵世的功利和文化,而這正是宗教中所包含的真正的對立”,其無限性大于一切文學體裁、囊括世間萬物,其中蘊藏著無限的矛盾和對立。
然而,追尋絕對的無限也給浪漫主義者帶來了毀滅性的痛苦。坎寧安梳理了哲學的兩個基本傳統:一個傳統是將所有問題回溯至終極答案的“本體神學”;另一個傳統是在“終極有物”之外,追問“為什么是有,而不是無”的“超本體神學”。前者走向虛無主義,后者則顯示了虛無主義的邏輯。浪漫主義的思鄉情結在尋求“故鄉”這一終極答案的同時,表現了虛無主義的邏輯,它通過反諷將有限性建立在無限性上,將故鄉建立在渴望上。一方面,對浪漫主義者而言,人作為擁有理性與自由的塵世之花,彰顯著“一種永恒的趨向無限的自我規定”,為了追尋絕對的無限,“他就只有一條出路:始終自相矛盾并包容對立的極端”。然而,此種悖論性的追求必然導致矛盾律的缺失,使無限失去任何規定性,最終成為一片空虛。另一方面,浪漫主義者認為,“犧牲的隱含意義是消滅有限”,絕對的無限便意味著犧牲和死亡,同時毀滅中也包含著創造,“只有在死亡的中心,永生的火花才點著了”。追求絕對無限使浪漫主義者只能通過犧牲和毀滅來獲得真正的無限,但他們在哲學與藝術領域中所追求的不斷毀滅只能加劇現實中的幻滅感,無法換得永生。這進一步造成了主客觀的分裂,此種以毀滅為完成態的追尋終將走向虛無主義。
浪漫主義者對無限的追尋最終導致了自我的磨滅。在無止境的追尋中,完美世界并未實現,而在追求絕對的過程中,永遠無法抵達則意味著什么都不存在,因此“‘普遍是對無的最好體現,也是對零的最好體現’”。同時,極度的痛苦加劇了個體內心的崩潰,對故鄉的渴望與愛也隨之瓦解,如諾瓦利斯所言,“他跟剩下的世界毫無關系,漸漸耗竭自己,按自己的原則,他已是厭世者和厭生者(Misotheos) ”。在尋找故鄉的過程中,浪漫主義者的熱情和意志消磨殆盡,從創造者變為懷疑者,從異鄉人成為厭世者,從對無限的向往走向虛無主義的深淵。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浪漫主義與后現代主義都發展出虛無主義,但與后者激進的相對主義不同,前者“從未質疑過人的精神的同一性”,它的思鄉情結始終將故鄉作為終極、絕對的神圣存在,只是追尋的方式與過程使它走向了虛無主義。
結語
反思德國早期浪漫主義的思鄉情結,無論是重新發掘中世紀文化以寄托思鄉之苦,還是以反諷為途徑否定有限的現實,將世界無限浪漫化,力圖以詩之本體重構家園,抑或詩人作為世間的立法者,以審美救贖為己任,都是回應啟蒙理性所造成的主客分離問題,以期實現世界的和諧與統一。但浪漫主義的思鄉情結蘊含著虛無主義的傾向,未能將故鄉實在化為可以棲居的家園,思辨層面上的反諷轉化為生存意義上的反諷。
當啟蒙理性祛除了世界的超越性與神圣性,重新追尋意義便成為現代性的一個重要主題。從盧梭的具有神性的自然到席勒的審美烏托邦,再到海德格爾將藝術中的諸元素以本源性的樣態表現于四重整體的世界,其間延續的思鄉情結都是對人與世界之潛在意義的執著,致力于反思現代性困境。盡管德國早期浪漫主義在追尋無限、絕對等思想時缺乏實踐基礎,但是它有別于后現代主義激進的虛無主義,蘊含著重建價值的契機,此種追尋在當下正是“作為一種鄉愁,創造出成為價值本身的事物:藝術、科學、社會理論和所有其他需要人們全身心投入的事物”。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責任編輯 吳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