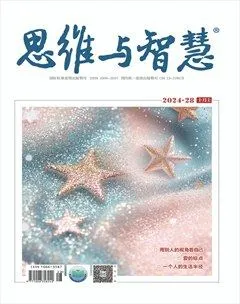累物與累心
劉義慶《世說新語·雅量》中有這樣一則故事:祖約喜歡收集金銀珠寶,阮孚喜好收集木屐,二者都是親自打理自己的收藏,由于這兩種愛好看起來差不多,所以人們也無從區分高下。
有一天,有人去祖約家中,恰逢他正在整理自己的財物,一看到客人來,他就把沒整理完的寶貝放到了自己的身后。盡管祖約已經藏起來了,但還有些忐忑不安的樣子。又有人到阮孚家中拜訪,看到他在給自己的木屐點火打蠟,還感嘆著:“這輩子剩下的時間不知還能穿幾雙木屐呀!”神色悠閑豁達,不因為旁人在側而有所改變。由此,人們對二人的收藏之樂有了高下的判斷。
愛財者如祖約,見有人來訪,就匆忙把珍寶藏起來,倒不是說不可以這樣,而是從他一系列的表現可以看出,他認為這種嗜好是丟臉的,或說是見不得光的,不可以與人共享這種感覺。這樣畏手畏腳,簡直就是單純的斂財者或收藏者,樂趣就在不斷增加外物的過程中,且自己深陷其中,無法自拔,身心之累可想而知!
與既累物又累心的祖約相比,愛鞋者如阮孚,他舉鞋把玩,絲毫不避客人,也不能說物不貴重,自己不在乎。事實上,對于喜好某種東西的人來說,好物值千金,滿足感千金難買。阮孚慨嘆一生能穿幾雙鞋,除了展現了對鞋子的喜愛外,還流露出對生命和光陰本身的嘆息,其率真高遠的名士情懷盡顯。他真的是雖累于物,卻不累于心。
這讓我想到了收藏大家張伯駒先生。當年,為了使展子虔的《游春圖》不落入洋人之手,他百般籌措資金,甚至以破釜沉舟之勇,賣掉自己的幾處私宅和夫人的首飾。之后,因他太喜歡這幅畫了,就把自己的住所更名為“展春園”,還自號“春游主人”。
張伯駒因物而累,可要是了解這幅畫,也就容易理解了。展子虔是北齊至隋之間的一位大畫家,《游春圖》是他傳世的唯一作品,上有宋徽宗的題簽,也是迄今為止存世最古的畫卷。
執著于物的追求如享樂,容易沉迷其中,而難于超脫出來。張伯駒深知自己只是暫時擁有,而不能長久獨占,故拿得起,也放得下。1952年,他們夫婦把《游春圖》和唐伯虎的《三美圖》連同幾幅清代山水畫軸均轉讓給了故宮博物院。無疑,這是如此寶貴的畫作最好的歸宿。
顯而易見的,張伯駒如阮孚,喜歡一物,就是真的喜歡,喜歡得自然,也近于灑脫。可惜的是,阮孚的那些木屐已無從尋起,而經張伯駒之手的畫作長存,光彩永照我們的文明史,讓我們一直感受著它們的光輝。
(編輯 雪彤/圖 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