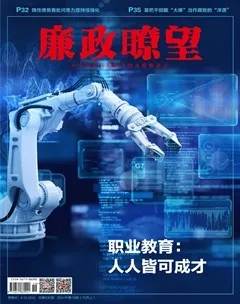回得了縣城,逃不了“內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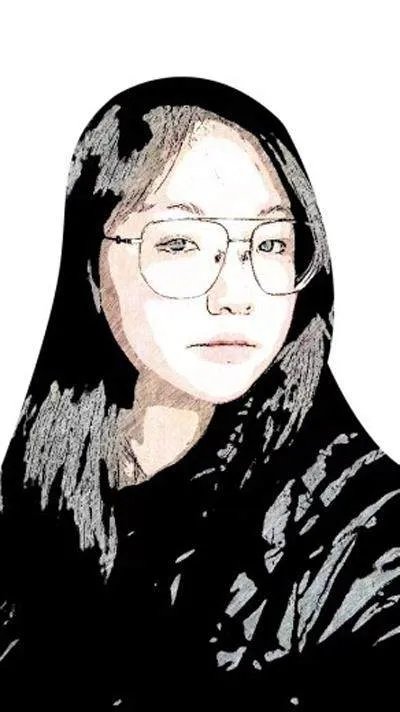
“從一線城市回到縣城是為了躺平。”這大概是很多人對“漂”回縣城的年輕人的想象。
但在前段時間的采訪中記者發現,小縣城里的年輕人似乎躺不平了。不少人自嘲回到縣城的自己是“仰臥起坐型”選手,一會兒想躺平,一會兒又得卷起來。
原因之一,縣城里被視為最穩定的體制內工作已經趨于飽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沖著體制內工作回到縣城,發現“上岸”變得不再輕松。“小縣城這幾年掀起‘考公考編熱’,‘上岸’壓力堪比一線城市。”當有人發現回到縣城并不能馬上解決就業問題,備考2年仍然沒有上岸時,焦慮情緒并不比大城市帶來的生存壓力小。
那些因學歷、能力一般而回到縣城尋求機會的人也發現,縣城體制內也開始卷學歷了。“一個縣城的崗位,過去本科生都不多見,現在則是一堆重點高校的本科生扎堆競爭,甚至還有一些博士生考到小縣城工作。大家都想回小縣城過得松弛一點,但縣城的優質資源也是僧多粥少。”從北京考回什邡市某黨政部門,又從該部門辭職到成都求職的吳瀟瀟說。
有的人認為,力爭“上岸”還算是良性的正向競爭,真正進入縣城體制內,才發現“內卷”是全方位的。“近幾年回縣城‘上岸’的人年紀都不大,許多還沒有真正到躺平的年紀,沒有幾個是真正不上進的,即使你不卷,別人也會卷你,最終還得跟著一起卷。有些工作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為了讓領導覺得‘做了工作’,一件事翻來覆去變著花樣做。”一位從杭州大廠辭職回安徽老家的干部說,自己單位有2個畢業就考回縣城的年輕人,年齡不大,工作特別熱情,點子也多,深受領導喜愛。對比之下,自己曾因在工作上沒有完成“額外動作”,被調侃“大廠出身,能力也不過如此”。
一些回到縣城的年輕干部發現,同事也開始加入雞娃大軍。為了不讓孩子輸在“眼界”上,從幼兒園就開始“卷”孩子的年輕人不在少數。有人調侃,自己終歸是走上了當年父母的路。“縣城教育資源有限,但孩子未來是要和全省的人競爭。那些從一線城市回到縣城的人,之前不少就是縣城里的‘卷王’,但從一線城市回來后,他們更加清楚教育資源帶來的差距,拒絕讓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一些家長還會利用假期時間,把孩子送去省會城市學一些當下新興的興趣班,比如建模、AI甚至計算機編程語言。”吳瀟瀟說。
記者發現,這些從一線城市回到縣城的年輕人也將一線城市的消費習慣帶回縣城,讓縣城的商業也“卷”起來了。以教育行業中的興趣班為例,不少發達一些的縣城,興趣班門類變得更加多元豐富,并不輸給省會城市。并且,由于縣城產業結構往往較為單一,能提供給年輕人的崗位并不多,不少人選擇加入創業賽道。當資源有限、競爭變大時,各個行業的“內卷”就在所難免。不少人發現,小縣城的創業競爭并不輸于大城市,短視頻抖音帶貨、品牌招商加盟之類的東西也到處都有,沒有兩把刷子,創業之路很可能中道崩殂。“回縣城優哉游哉開個小店養活自己的計劃,最后也成了夢幻泡影。”一名在縣城二度創業失敗的年輕人說。
其實,年輕人愿意回縣城本應可以為日漸“萎縮”的縣城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但一些縣城產業較弱的承接能力,以及人情社會帶給年輕人的文化沖突令人難以忽視,新的生存語境正在縣城書寫。
如今,在外部環境和內在需求的共同催生下形成的非良性競爭,隨著人口的流動與回籠,下沉到縣城。當年輕人在大城市面對過度且低效的競爭時,本想通過退而求其次來更換賽道,可事實說明,向后看永遠不是根本的解決方法。面對社會壓力,停一停無可厚非,但面對不斷加劇的社會競爭,努力提升自己,適應新環境才能找到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