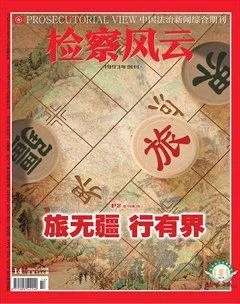黃昏時有來信

聽聞黃昏最得山水眷顧,一到此刻,云與天的繾綣柔情就被鑲上了數層金邊。鴉雀飛越山水歸巢,千重山上一棵棵老樹被霞光暈染,萬重水里一圈圈漣漪燦若金箔。霞光映出花草的影子,恍然間我與手中的書竟是互通了來信。
暮云低垂,山風穿林,霞光搖落一樹橙紅。低眉的女子倚著窗楹,幾縷殘紅透過窗欞落在她的手中。她抬眼看見云上有滾燙的熱情,云下有燦爛的風景,樹與樹隨著晚風輕搖,花與花相視一笑。她低頭想著,老者牽著黃牛走向炊煙,云朵在山間與月纏綿,離家的人應該踏上歸途了吧。于是,對鏡描妝,穿上新衣,等門扉被叩響,與故人訴衷腸。黃昏的酒意爬上她臉頰,胭脂更艷了幾分。可這樣一個黃昏,怎能枯等?紅顏易老啊,于是提筆寫下一句:黃昏釀酒,心憂離恨杯中盡;歲月不復,恣意瀟灑方是情。時光不該被辜負,這樣的黃昏尤其是。
黃昏時的江邊比其他時段平添了幾分溫柔,一道赤紅將江水斬成兩段。耀眼的紅色從遠方慢慢暈染,直至淺淺地凝在船的四方。一位詩人站在古舊的渡口,看一艘艘船越行越遠,直到融盡橙紅,化為江水之中的一點。此情此景,很難不讓人想起那句“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想來黃昏最適合分別,足夠溫柔的光景能讓人忘卻離別的苦痛。你走的話就帶一抹黃昏的詩意離開吧,浩浩湯湯的江水都是我對你不舍的情意。也許我們有一天會突然忘記彼此的容顏,可一定不會忘記這樣一個黃昏。而我,同樣也記住了這個黃昏,記住了這個關于離別的故事,記住了一首首關于離別的詩詞。文辭的奧秘從來都是欲言而止,就如同思念的長度無法度量。
如果寫黃昏,就不能單純地寫黃昏,要寫“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要寫少年意氣風發,辭親遠赴玉門;要寫黃沙漫天,將軍磨劍;要寫那場為國而戰的廝殺,黃昏的光線照在緊閉的城門,覆蓋在英雄的骸骨上。黃昏演繹著悲壯,那樣鋪天蓋地的絢爛豈是詞句所能窮盡?我從詩文中看見血染紅了邊疆,兵士們持戟的手上布滿了歲月的風霜。黃昏時的光和他們的眼睛是如此相像,黃昏在等山間的一輪月亮,他們在等戰事停止,回歸故鄉。此時的我甘愿做一只孤雁,往來南北之間。甘愿做個異鄉客,為他們寄去家長里短。在那樣的動蕩時局,有時候啊,我也免不了親手提筆,為他或者她寫下:安好,勿念。
風吹樹影搖,月升霞光隱,對于描寫黃昏,我總是詞窮。也許,黃昏應該是一個郵筒,詩人們曾寫下無數封信投遞進去,而我無以回贈。黃昏時讀詩文,文辭里有動人的聲音,而我知曉,那些都是時光的回信……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