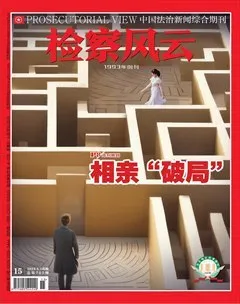主導“三次論戰”的新分析法學代表人

在哈特的學術生涯中,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三次著名的法學論戰。這三次論戰不僅展現了哈特深邃的法學思想,也是法學史上的重要篇章,至今仍被廣泛討論和研究。
牛津瑪諾園(Manor Place)有一座兩層樓的英式風格住宅,外墻由磚石構成,搭配著斜屋頂和煙囪,顯得古樸而典雅。房子的正面裝飾有白色窗框的矩形窗戶,其上的小拱形裝飾為建筑增添了美感。深色調的前門與淺色外墻形成對比,掩映于綠蔭之中。這就是著名法哲學家赫伯特·萊昂內爾·阿道弗斯·哈特(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的故居。
輾轉的求學生涯
1907年,哈特出生在約克郡的一個猶太移民家庭,他的父親西米恩·哈特(Simeon Hart)和母親羅斯·哈特(Rose Hart)都是波蘭和德國猶太移民的后裔。他們在哈羅蓋特鎮(Harrogate)經營著一家頗受歡迎的毛皮和女裝店,為幼年的哈特提供了相對舒適的生活。
哈特先是在鎮上的學校接受教育,隨后被送往著名的公立學校切爾滕納姆學院(Cheltenham College),開始了他的中學生涯。切爾滕納姆學院以嚴格的英式教育和體育競技而聞名,這對于哈特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在這里,他體驗到了與家鄉截然不同的教育環境和社會氛圍,他時常感到孤獨和沮喪。盡管如此,哈特顯露出的學術天賦仍然給老師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隨后,由于家庭生意不景氣,哈特轉而進入布萊福德文理學校(Bradford Grammar School)繼續他的學業。這對他來說是一個轉機。在布萊福德文理學校,哈特感受到了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學習環境,他的學術潛能也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可以說,在布萊福德文理學校的時光,對哈特的未來職業選擇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1926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并獲得了牛津大學新學院的獎學金。在牛津大學新學院完成學業后,哈特決定進入法律行業。他在倫敦的中殿律師會館(Middle Temple)開始了作為律師的學徒生涯。這是一個歷史悠久、聲望極高的律師會館,為英國培養了許多杰出的法律人才。然而,1931年,哈特因為騎馬事故嚴重受傷,不得不在醫院中度過數月,這對他的職業生涯造成了不小的打擊。不過,哈特并沒有放棄。他在康復期間堅持學習法律,希望能夠通過牛津大學畢業生民法學士學位考試,以獲得法律學術資格。
曾參與軍事情報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哈特的生活偏離了正常的軌道。1939年12月初,英國向德國宣戰后,哈特被征召。他參加了軍方面試,但由于心臟問題在體檢時被淘汰。隨后,他試圖成為戰地保安警察,但因為健康問題再次被拒絕。最終,在1940年的夏天,他加入了軍事情報部門,開始了與其后來法理學教授身份差異極大的“反間諜工作”。
在軍事情報部門,哈特主要負責阻止間諜活動,并鑒別英國境內的間諜。因為表現出色,哈特很快就坐上了發展反間諜政策的領導職位。他的學術訓練、職業經歷、高智商以及對語言的特殊天賦等,都為他勝任這一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這段工作經歷對哈特來說是十分寶貴的,因其不僅鍛煉了他的分析和判斷能力,還讓他深刻理解了法律與道德、安全與自由之間的復雜關系,更對他的法哲學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戰爭結束后,哈特面臨著職業選擇。他曾考慮繼續律師生涯,但1945年,牛津大學新學院的院長為他提供了哲學研究員的職位。于是,哈特回到了牛津。這一轉變不僅讓他站到了學術生涯的起點,也為他后來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基礎。1961年,他出版了代表作《法律的概念》。書中,哈特以法律實證主義為基礎,運用概念和語義分析法深入探討了法律概念的相關議題,系統闡述了他的新分析法學學說。這本書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法理學著作之一,它更新并激發了法理學的討論,對當代法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哈特的學術生涯與他的個人生活緊密相連。他與珍妮弗·威廉斯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不僅是他們個人情感的寄托,也是他們在社會和政治動蕩中尋求穩定和安慰的避風港。珍妮弗出身于一個富裕的精英家庭,她的父親是國際法律秩序的設計者之一,而她本人在內政部工作,并且在學術上也有很大的成就。實際上,哈特加入軍事情報部門,離不開珍妮弗的推薦,而哈特的職業發展,也離不開她的支持。
“三次論戰”打出現代法理學基本框架
在哈特的學術生涯中,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三次著名的法學論戰。這三次論戰不僅展現了哈特深邃的法學思想,也是法學史上的重要篇章,至今仍被廣泛討論和研究。
第一戰是哈特與富勒之戰。這場論戰始于1957年,富勒批判分析實證主義傳統,主張法律和道德、實然法和應然法不可分離。哈特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為法律實證主義辯護,回應了富勒等法學家對分析法學傳統的批判,并在《法律的概念》中系統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富勒則于1964年出版了《法律的道德性》一書,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并批評哈特主張的法律與道德分離論。這場論戰促使法學家開始思考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的原則。在這次論戰的推動下,以哈特為首的新分析法學正式誕生,自然法學也得以復興和發展。
第二戰是哈特與德富林之戰。這次論戰的起因是英國議會的同性戀犯罪和賣淫調查委員會報告。該報告建議取消對有關成年人私下自愿同性戀和賣淫行為的刑事制裁。德富林批評這一觀點,認為社會的共同道德觀念對維護社會的存在極為重要;而哈特主張應在公共道德與私人道德之間劃出一定的界限,反對法律不適當地干預私人的道德生活。最終,哈特在這場爭論中占據了上風,德富林本人也在1965年公開登報聲明放棄自己先前的保守立場。
第三戰是哈特與德沃金之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耶魯大學法學教授德沃金對英美傳統法學觀點進行了批判。德沃金指出,哈特的規則論模式賦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權,違反了民主政治的原理。在出現現有規則沒有提供解決辦法的疑難案件的情況下,法官必須從規則背后的原則、政策之中尋求正確判決,此時法官并不享有自由裁量權。哈特隨后對德沃金的批判做了回應,聲稱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后來,德沃金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但這并不意味著哈特的觀點就是錯誤的。哈特的學術思想,尤其是關于“法律規則”的論述,對現代法理學的形成與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德沃金的觀點也被大多數教科書采納,逐漸形成了法律是由規則、原則、概念三要素構成的法學理論。
到了晚年,哈特對法律實證主義的貢獻進一步深化。特別是在《法律的概念》第二版中,他對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他的晚年作品,如《法理學與哲學論文集》,集結了他一生不同階段的代表性論文,展現了他在法哲學領域的廣泛興趣和深刻見解。
1992年,哈特逝世,但他對法學界的影響持續至今。2007年,為了紀念哈特誕辰一百周年,英國科學院舉辦了一場重要的研討會。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法學家和政治哲學家探討了哈特在法哲學領域的貢獻。
如今,哈特在瑪諾園的故居,成為很多人參觀拜訪的地方。這里不僅保存了哈特的個人記憶,也保留了一個時代的學術研討和思想交流的痕跡,見證了哈特的思考、寫作和與學界同仁的交往。它提醒著后來者,偉大的思想往往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
編輯:張鈺梅" " zhangclaire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