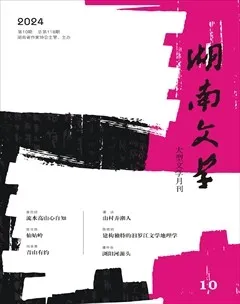建構(gòu)獨特的汨羅江文學地理學
余光中寫過一首名為《汨羅江神》的詩,里面有這樣的詩句:“烈士的終站就是詩人的起點?昔日你問天,今日我問河,而河不答。”顯然,這里寫的是屈原,汨羅江因屈原而在中國詩歌史上有著獨特的地理詩學位置,它幾乎是一個地理詩學的源頭。因為屈原流放在汨羅江一帶,在這里生活、思考過,而且有一個感天地泣鬼神的投江舉動,這個動作構(gòu)成了中國詩歌乃至中國文化一個奇特的富有象征意味的起點,也使中國詩歌獲得了地理學標識。圍繞屈原《離騷》的研究汗牛充棟,我沒有資格添磚加瓦。不過,我對汨羅江流域老百姓世代相傳的神話故事頗有興趣。這里略談一二。
按傳說的說法,汨羅江文化源頭可追溯至伏羲時代。傳說伏羲出生于磊石山的龍窩,他創(chuàng)立了天象、地理、結(jié)繩記數(shù)法,還識藥治病,以琴制樂,使嫁娶有禮……幾乎無所不能,是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始人。顯然,他是神祇。神還有真身,據(jù)說幕阜山上至今還存有伏羲墓,又證明了伏羲是肉身凡人,與百姓一起生活于汨羅江邊。更加浪漫的傳說乃是有關黃帝的,該傳說記載在《長沙府志》上。相傳黃帝在湘陰笙竹驛砍竹作笙,在磊石洞庭山上張樂,有十二只鳳凰到鳳凰臺上與之和鳴。黃帝在東町湖(鼎湖)乘龍升天,這大約是龍文化的起源之一,磊石洞庭山上還有龍神祠紀念黃帝。這可能就造就了汨羅江從古至今的龍舟文化傳統(tǒng),當然,也可能是后來的文化慶典儀式活動將其源頭追溯于黃帝。更富有遠古時代政治意味的傳說也在汨羅江的磊石洞庭山上演繹。相傳舜帝傳位給禹帝,然后把二妃留在磊石山上,自己南巡九嶷,后崩。二妃聞訊,追尋舜帝,淚灑湘江。數(shù)千年后,偉人毛澤東有詩:“九嶷山上白云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毛主席顯然欣賞黃帝舜帝的傳說故事,因為這里面包含的意義太豐富了。德里達曾寫有一本書——《友愛的政治學》,開篇就提到堯舜禪讓的故事,實際上,還有舜禪讓皇位給禹,當然還有商末伯夷、叔齊兄弟禪讓、不食周粟的美談,但那是發(fā)生在大西北的故事。舜帝的故事則在汨羅江畔留下一筆。毛主席作為湖南人,對故鄉(xiāng)的山河土地上流傳的故事也是頗為欣賞的,否則不會以詩回應。這里面包含著神話傳說與地理學的關系,也包含了政治想象與文學虛構(gòu)以及民間文化的親緣關系。
我們無法考證古代神話傳說的真實性,魯迅先生在小說《理水》中曾諷刺顧頡剛考證出禹是一只蟲的說法,當然,這是魯迅先生借小說諷喻現(xiàn)實。學術的考證當然有意義,但我們也可以去理解神話傳說中所投射的文化與政治想象。很顯然,因為與地理聯(lián)系在一起,神話傳說便具有了某種實在性,地理賦予神話傳說千百年流傳的在地性的物化特質(zhì),使得神話傳說在民間具有可崇拜的具象本質(zhì),也使口頭流傳的歷史在地理上留下各種印痕。圍繞舜帝的神話傳說演繹成了一個漫長的歷史化的文化事件,傳說舜帝離去后,湘妃溺于黃陵湘水,后世有建黃陵湘山祠以為紀念,還留下了二妃的相思宮、望帝臺、琴棋望、哀洲等遺址,這使傳說具備了地理學的賦能。其他關于帝王的傳說也可以在此展開想象演繹而具有合法性。傳說穆王兩次到達磊石山,留下了“穆屯”的地名和“八駿馬”的伏馬坡、穆溪春漲的典故。再有傳說秦始皇阻風于赭湘山,留下赭山、文武洲等遺址。湘山祠因屈原在此作《卜居》《天問》《湘君》《湘夫人》而名甲天下,在唐代又有李白、杜甫、韓愈等詩文唱和。屈原在磊石洞庭山所作《橘頌》在宮廷民間廣為流傳。所有這些,使得神話傳說演繹成文化史和文學史的有機部分,世代影響著汨羅江流域百姓民眾的生活習俗和節(jié)慶典禮。
文化形成的內(nèi)驅(qū)力在于使人們具備了想象的能力,有了情感歸屬的需要,并且可以使這種想象和情感合理化從而融入生活結(jié)構(gòu)。地理學賦能于神話傳說以落地的真實性,反過來,神話傳說重構(gòu)了地理的文化地位。在這里,文化、政治、地理三位達成一體,使得一個具體的地理具有了很高的文化象征地位,汨羅江流域、磊石洞庭山等這一片山水,經(jīng)過文化想象的重構(gòu)獲得了非凡的魅力,因此成為名勝古跡。
因為地理學賦能的緣故,我們今天完全可以理解關于舜帝的神話傳說,我們也樂于去相信、去想象這些傳說。在這些地理學表征的“名勝古跡”之側(cè),我們和古人仿佛是同時代人。在這樣一個意義上,我們對遠古神話的理解和感悟,對汨羅江和磊石洞庭山都可以有共情和共鳴。這些神話傳說和后世的文化回應,對湖南,尤其是對汨羅江流域的老百姓來說,都是家喻戶曉的故事,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可以隨時被提起。因為地理學標識的文化遺址可以固定下這些文化記憶。當我們說中華文明具有非常強大的韌性,它的傳承性、它的連續(xù)性非常有效的時候,其實我們說的是我們在精神上和我們的古人可以是“同時代人”,甚至我們可以沉浸于那些神話傳說的氛圍中。湯因比曾經(jīng)有一個“同時代人”的概念。他認為,可稱之為人類的時間可以從石器時代中晚期到新石器時期算起,這樣便有三十萬年的歷史。而人類文明(指有文字的現(xiàn)代人類文明)大約有六千年歷史,只占到五十分之一。這五十分之一的時間,從古至今的有文明的人類可以理解為“同時代人”。這當然是湯因比歷史研究非常獨到的地方。如果把地理文化遺址所建構(gòu)起來的文化記憶考慮進去,這個“同時代人”的概念可能更扎實。而中國文化傳承的堅韌性不只源于典藏典籍,還有這些與地理學標識的文化遺址聯(lián)系在一起的美妙的神話傳說,正是因為其感人至深的文學性,使得它得以世代相傳。這也是中國文化以其獨特的歷史事實性對湯因比大膽的理論設想的回應。
我們通常會把《詩經(jīng)》《楚辭》作為中國文學的起源。對文學起源的接近,有一種獨特的經(jīng)驗方式,那就是文學地理學的方式,親歷歷史文化傳承的遺址現(xiàn)場——盡管這個現(xiàn)場也是被文學虛構(gòu)并書寫的。但正像所有的起源都是一個共識的產(chǎn)物,這樣一個文學的起源,它能夠以文學地理學的標識為后人所經(jīng)歷,這是文學所獨有的,也是經(jīng)常性的形式。文學的追憶、懷念、憑吊經(jīng)驗依賴地理學建構(gòu)起來的標識,文學的歷史傳承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文學地理學,并非只是存在于典籍記載中,而且典籍記載經(jīng)驗也依賴地理學的實據(jù)。
這種文學的地理經(jīng)驗乃是非常普遍的,對于相當多的湖南、湖北籍的作家來說,屈原所代表的這種楚文化的文學起源構(gòu)成了他們文脈的內(nèi)在精神。
當然,我尤其想去思考關于汨羅江文學起源性特別豐富和富有啟示性的地方。這種起源包含了黃帝、舜帝、周穆王,甚至還有秦始皇,為什么這么多的帝王都來到汨羅江邊的山上呢?這一點意味著什么?就是說我們關于文學的起源性——如果我們可以把上古神話傳說看成文學起源的話——那么關于文化、文學的起源性,關于我們文明的起源性,關于我們政治的起源性,它在地理學這個意義上就能達到與文學的同構(gòu)。
回到我剛才說的這樣一種神話傳說與文學地理的關系,以及我們今人和古人的共同心靈經(jīng)驗的這種想象性建構(gòu)關系,這都是一種重建的文學的關系。這些都是很實際的存在:不管作家也好,學者也好,在地理學意義上所建構(gòu)的地理的想象,本身也是在建構(gòu)關于文學史的想象,他把一種神話的傳說實體化、地理學化,而地理學在這里重構(gòu)了我們關于文學史的想象。因關于上古帝王的傳說構(gòu)成了這些神話傳說的核心內(nèi)容,文學的虛構(gòu)想象和被時間化的實際的政治想象結(jié)合在一起,在中國文明的建構(gòu)當中,它便具有了某種優(yōu)先權。
在文學敘述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文學地理學的能量。尤其在重構(gòu)文化政治方面,重構(gòu)文學史方面,它有如此強大的功能。西方的后現(xiàn)代地理學算是頗為極端的地理學,它干脆把地理學的本質(zhì)看成是虛構(gòu)性的,把地理學看成是文學,地理學在根本上與文學沒有區(qū)別。當然這種極端的地理學觀念,贊同和跟隨的人并不多。但反過來講,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經(jīng)驗,文學虛構(gòu)了一種地理學,或者可以說虛構(gòu)了“文學地理學”——我是指在作家的想象性表述中。比如說中國作家所津津樂道的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莫言堅定地談論到的他書寫的高密東北鄉(xiāng),賈平凹后來也常常強調(diào)的他的家鄉(xiāng)秦嶺山脈。賈平凹在《山本》《老生》《秦嶺記》等作品中尤其把秦嶺作為一道文學扎根的山脈來寫。韓少功早在尋根時期就在創(chuàng)作談里提到汨羅江,后來的作品也經(jīng)常涉及,后來他干脆住在距離汨羅江不遠的山里。當然,還有更多的湖南、湖北的作家,如王躍文、劉醒龍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書寫著鄉(xiāng)村記憶,而這種記憶越來越具有地理學的準確性和具體性。關于地理的想象非常神奇地構(gòu)成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作家的寫作營地,他們更樂于扎根于泥土中或大地上,給予文學以地理學的堅實性和深厚度。
責任編輯:羅小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