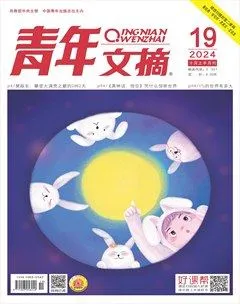李政道 :他的成就不只是一個諾貝爾獎

1957年,瑞典皇家科學院,藍色音樂廳內,掌聲雷動。李政道跟楊振寧一起獲頒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二人合作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理論,改變了科學界對對稱性的認識,為人類探索微觀世界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在獲獎演說中,李政道講了一個《西游記》的故事:“孫悟空翻了一串跟斗,以為已經到了宇宙的盡頭,實際上他還在如來佛的手掌中……我們離絕對真理還很遠、很遠。”
美國當地時間8月4日,李政道去世,享年97歲。這位曾“大鬧天宮”,徹底顛覆人類對物理學理解的“孫悟空”,就此騰云而去,化為繁星。
戰火中走出的“神童博士”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出生在上海一個富足的書香家庭。在良好的教育環境下,他很小就展現出過人的學習天賦。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風雨飄搖,沒有誰能安靜地讀書,即便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
1941年,日軍侵占上海,剛剛結束初中階段學習的李政道,不得已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求學生涯。昔日的安穩生活在炮火中灰飛煙滅,李政道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自學。他曾回憶那段過往,每天下午三四點鐘,日軍敵機進城轟炸,茶館老板都到城外防空洞避難,而他要冒著生命危險幫忙照看茶館,以換取一些客人的殘羹剩飯。
但也正是在這段時期,李政道讀到了廈大校長薩本棟所著的《普通物理學》,開始初窺物理門徑。他還讀到了愛丁頓的《膨脹的宇宙》一書,浩瀚宇宙的閃爍星光與射線之中埋藏的秘密,使他想去更遙遠的地方。
1943年,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學電機系。得益于教授束星北的啟蒙,李政道意識到物理學科的重要性,轉至物理系。也是在束星北的建議下,李政道轉學至西南聯大物理系二年級就讀,師從“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大猷。
“不知疲倦的物理奇才”,吳大猷從不吝嗇對李政道的贊譽,“無論給他什么艱深的書和難題,他都很快做完,又來索要更多的”。這就能理解,為什么吳大猷會力薦這個僅是大二的學生赴美留學。但由于戰亂,李政道從未取得過任何畢業證書,初到美國時沒有學校愿意要他,他只能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旁聽。好在僅僅一個月后,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費米教授便發現了他過人的天分,破格將其轉為自己的博士,“神童博士”自此聞名遐邇。
1950年6月,年僅23歲的李政道通過博士學位答辯。當時的芝加哥大學校長親自為他頒發學位證書,并說:“這位青年學者的成就,證明了在人類高度智慧的階層中,東方人與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創造能力。”
在美國讀書期間,李政道結識了同為優秀物理學家的楊振寧,兩人經常討論得熱火朝天。1956年,二人合作發表《對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恒的質疑》一文,提出了“宇稱不守恒原理”。這一顛覆物理學中基礎理論的論斷,很快被華人物理學家吳健雄等同行用實驗證實。1957年,李政道和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開全球華人之先。
為祖國做點有益的事
一個科學家的終極榮耀,李政道在31歲就獲得了,但這遠不是其科學征途的終點。在之后幾十年里,李政道又先后在量子力學、高能物理學等領域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與此同時,李政道始終牽掛祖國。他曾表示:“平生最大的心愿和安慰就是能夠為祖國做點有益的事情。”
從1972年起,李政道和夫人秦惠頻繁奔走于中美之間,以歸國講學、建言獻策、牽線搭橋等方式,希望中國盡快追上世界科技發展的腳步。他為當時中國理科教學中基礎科學的落后深感憂慮,便提議參考芭蕾舞劇團從小培養演員的模式,全民選拔十三四歲、有潛力的少年,這就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屆“少年班”的雛形。
1978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今中國科學院大學前身)成立后,時任副院長的錢三強詢問李政道是否愿意向國內的研究人員,介紹世界物理學的前沿成果。李政道欣然應允,還考慮到國內缺少相關教材,預先寄來100多冊文獻資料和參考書籍。此次李政道回國教授“統計力學”和“場論簡引和粒子物理”,硬是將原本需要兩三年時間的課程精練到7周。每天凌晨3點多,他就要起床準備,常常在臺上講得滿頭大汗。
與此同時,李政道覺得只舉辦講座遠遠不夠,便萌生了選拔學生到世界一流學府深造的想法。30多年前,吳大猷教授提供的一個機會,改變了自己的一生,他希望“讓更多類似的機遇能光顧其他年輕人”。
在其推動下,1979年,中美聯合招考物理類研究生項目CUSPEA應運而生。項目存續的十年間,共選拔了900多名中國學生赴海外公費留學,為中國物理學培養了一批中流砥柱。
那些年,李政道像個志愿者,親筆為這些同學寫申請材料,并逐一寄送;他們在國外的生活,也一應關心照拂。CUSPEA項目每年要用去他約1/3的時間和精力,秦惠曾回憶說:“你們不知道,為了中國的科教事業,他都快發瘋了。”而李政道則坦言,自己深知CUSPEA有價值、有意義,“從某些方面講,它比我做宇稱不守恒還有意義”。
此后,李政道又倡導成立了中國博士后流動站和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他還積極建議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建議建造正負電子對撞機……可以說,今天中國科技和教育事業的成就,從李政道處受益良多。
一位科學家的“藝術人生”
都說科學是嚴謹的,但科學家卻不能過于嚴謹,要不然哪兒來靈感的火花?李政道非常喜愛唐代詩人杜甫的名句:“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在科學研究之外,他也有著自己可愛而迷人的精神世界。
到美國讀書時,李政道曾制定過一個“10年奮斗計劃”,他暗下決心,不在學術上有所成就,不會過早地談戀愛、結婚。只是愛情來得太快,1948年,李政道在火車站接同學時,與秦惠一見鐘情。為了追求愛人,他不僅忘了“10年奮斗計劃”,還決心拿掉“小胖子”的頭銜,努力減肥,以至于其導師費米以為他在經濟上出現了困難。
李政道還是一位喜歡“自娛自樂”的畫家。他的畫數量眾多,畫風豐富,從中能看到他對科學的見解、對生活的向往和對妻子深深的愛。《憶》《念》《與愛賞》……秦惠的“”字頻繁出現在其隨筆畫題名中。
幾年前,上海交通大學原校長林忠欽到他家中做客,發現90多歲的李政道散步時揣著一個小本子,見到感興趣的風景就坐下來,隨筆涂鴉成畫。
當代著名畫家吳冠中對李政道的畫作給予高度評價,稱贊他“在無法之法中表現了對象的生動體態及情之所鐘,充分體現了形式構成之視覺美感”。似乎科學探索宇宙之奧秘,與藝術探索感情之奧秘間,隱有一道通途。李政道認為確實如此,他畫畫也并非僅僅出于個人興趣,而是一種推動科學與藝術融合的志愿。
1986年,李政道創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中心每年舉辦較大規模的國際學術會議時,李政道都會或邀請藝術家,或親自上陣,根據會議主題創作藝術畫,印在活動海報上。他希望用藝術的語言引導人們探索宇宙之奧秘。他說:“科學和藝術是不能分割的,它們是智慧和情感的關系,沒有情感,智慧能開創新路嗎?沒有智慧,情感能夠達到完美的程度嗎?科學與藝術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同是源于人類活動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卓越。”
他總希望后來的學生、中國各個年齡層次的科學家或藝術家要兼有科學精神和人文情懷,這是每個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氣質,也是大學精神最重要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