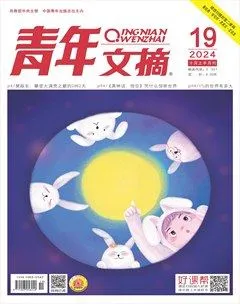《詩經》之“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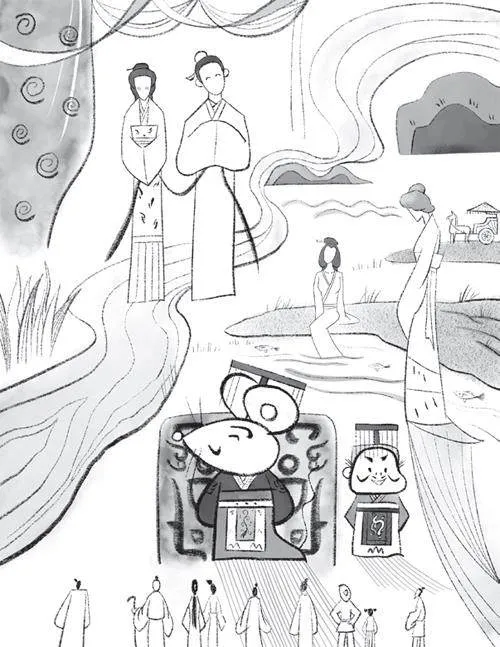
提到《詩經》,今天的人們都習慣把它當成高雅文學,說話或起名但凡能引用,便立馬有了提升品位的功效。然而,若拋棄《詩經》的“經典濾鏡”,回歸它當初誕生的場景,我們會發現,《詩經》亦有“俗”的一面,耐人尋味。
最能體現《詩經》“俗”這一面的,莫過于“國風”。當時,周王室會派專門的樂官到民間各地去采風,也就是采集當地的民歌,采完民歌后,再由專業人士進行藝術加工,就成為我們今天讀到的“國風”。因此,《詩經》里的風詩,其實是民歌與文人創作結合的產物,《詩經》從本質上來講就是一部“歌詞集”。
因為是民歌,來自民間,產自社會,因此《詩經·國風》里有鮮明的生活氣息,也不乏家長里短的故事、八卦。“國風”里的婚戀故事特別多,比如,《周南·關雎》是當時的“婚禮進行曲”;《衛風·氓》則描寫一個女子從甜蜜的自由戀愛走向苦澀的現實婚姻再到成為棄婦的悲劇,像晚間八點檔的家庭劇,一點都不超凡脫俗,卻那么真實、接地氣,“俗”得惹人共鳴。
再比如,流沙河先生認為《衛風·碩人》是站在一個平民的視角,圍觀國君衛莊公迎娶齊國公主莊姜,在婚禮上對美麗的新娘生發的贊嘆。故而,這首詩里既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這樣可能由文人雅士潤色過的清詞麗句,又有“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這樣樸實無華的比喻。畢竟“柔荑”(白茅芽)、“凝脂”(凍豬油)、“蝤蠐”(天牛幼蟲)、“瓠犀”(瓠瓜子兒)、“螓首”(蟬一樣的頭)、“蛾眉”(蛾子觸角一樣的眉毛),都是來自泥土的靈感,不高雅,但勝在鮮活、形象。
甚至《詩經》里罵人的話也不少。衛宣公強占自己的兒媳宣姜,衛國人民對這種荒淫行徑非常看不慣,就在《邶風·新臺》里罵他是個癩蛤蟆——“燕婉之求,蘧不鮮。”“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鄘地的統治者貪婪、虛偽,這一帶的老百姓深受其苦,就在《鄘風·相鼠》里把他們比作大老鼠,直接咒他們死——“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因此,《詩經》之“俗”,是通俗,是世俗,也是風俗。因為有“俗”這一面,《詩經》成為真實世界的鏡子,可觀宇宙之大,可察品類之盛,由此成為古代社會一部偉大的“百科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