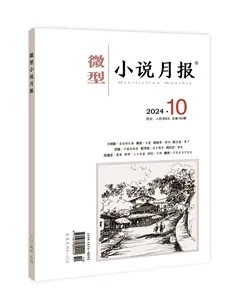游戲
敏子的媽媽走了,跟著一個賣小雞的中年男人走了。
那個時候,敏子才三歲多一點。而今,敏子滿五歲,往六歲上數了。從那以后,敏子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媽媽。
敏子跟著奶奶生活。但敏子并不知道媽媽撇下她,跟著一個賣小雞的男人跑了。奶奶哄著敏子,說媽媽去海邊一個小島上,幫助人家補漁網,掙錢來給敏子扯花布做新衣服穿呢。
敏子盼著媽媽回來。奶奶也盼著敏子媽媽某一天還能回來。可敏子媽媽始終沒有回來。
敏子跟著奶奶,整天喝稀粥、吃雞蛋、吃烤玉米和煎小魚。晚間,奶奶就像媽媽一樣摟著敏子睡。奶奶摟著敏子時,一邊捏著敏子肉乎乎的小腳丫,一邊給敏子講故事。慢慢地奶奶捏不到敏子的小腳丫了,敏子長高了。
奶奶看著敏子頭上的毛發長長了、變黑了,便給敏子扎起了一對羊角辮。敏子的奶奶常拿當院的石磨與敏子比高低——“你看看,咱敏子都快長到石磨那樣高了。”
敏子的爸爸在敏子一歲多一點的時候去南洋捕魚,遭遇狂風黑浪(其實就是臺風),死在海里了。早年,鹽區沒有氣象預報,漁民們出海捕魚,全憑望云層、觀星象來預測天氣,一有不慎,就將船毀人亡。
敏子對爸爸沒有印象。敏子只記得媽媽留著齊耳短發的俊模樣。敏子還記得媽媽總是會坐在當院的石磨旁織漁網。
敏子滿三歲的那年春天,小街上來了一個賣小雞的男人。那人挑著兩個扁圓的竹籮筐,大街小巷里吆喝:
“小雞喲——
“抓小雞——”
那人不喊“賣小雞”,他喊“抓小雞”。好像他竹筐里那些油菜花團一樣的小雞崽,全都跑出竹筐,需要人們來幫助他一只一只再抓回他竹筐里似的。其實,不是那樣的。
那個賣小雞的男人,面對竹筐里那些挨挨擠擠的小雞崽,他要一只一只地抓出來賒給人家,并不是當場出售小雞崽就可以拿到錢呢。這是那個年代賣小雞的常規。原因是賣小雞的進村時,多為春天。也就是民諺里所說的一年當中青黃不接的那個時間段,家家戶戶碗里沒有糧,菜園子見不到個“青頭”,到哪里去弄閑錢來買小雞崽?只有賒。再者,買小雞的人家想買母雞或公雞,那會兒一只只小雛雞全是油菜花團的模樣,怎么能分辨出哪只是公雞,哪只是母雞呢?
但賣小雞的人,偏偏就能分辨出來。他若沒有那個本事,怎么出來賣小雞、賒小雞,怎么好等到秋后上門來收那小雞崽的款項呢?
“抓六只小雞。”
這是敏子奶奶在說話。她要賒六只小雞。
那個時候,敏子還被媽媽抱在懷里。敏子奶奶顛著一雙小腳,到小巷口來抓小雞時,敏子媽媽停下手中的活計,抱起敏子到巷口來看熱鬧。
“要幾只公雞、幾只母雞?”
賣小雞的那個男人,如同賣豆腐、打涼粉的小販問人家稱幾斤豆腐、幾斤涼粉一樣,問敏子的奶奶要幾只公雞、幾只母雞。
敏子奶奶說:“一只公雞、五只母雞。”
話音未落,那人伸手拽出一只抬頭望天的小雞崽,口中念叨“公雞”,隨后又抓出五只吱吱鳴叫的小雞崽,說是五只母雞。其間,那男人抓小雞、扔小雞的動作,如同拋線團、扔氣球一樣,一只一只丟進敏子奶奶兜起的衣衫兜兜里,說:“好啦,五只母雞、一只公雞。”
敏子奶奶兜住那六只黃茸茸的小雞崽,思量了半天,可能是想到秋涼時,便是敏子爸爸的忌日,到那時,將要殺掉一只公雞來祭奠,剩下的母雞還需要有只公雞來領頭,便改口說:“要兩只公雞、四只母雞。”
賣小雞的那個男人瞪直了眼睛,問敏子奶奶:“你到底是要幾只母雞、幾只公雞?”
敏子奶奶說:“兩只公雞、四只母雞。”
那男人沒再說話,他伸手往竹筐內的小雞群里一抹溜,如同風吹麥浪一般,順手拽出一只冒尖的小雞崽,丟進敏子奶奶的布兜里,隨手又從敏子奶奶布兜里抓走一只低頭啄腳的小雞崽。然后,問起戶主的名字,他要把戶主的名字寫在他的賒賬本上,秋后好來討要小雞錢呢。
敏子奶奶開口就說:“王樹家。”
王樹,是敏子爸爸的姓名。
其實,那時敏子的爸爸早已經死去一年多了。賣小雞的那個男人寫下“王樹家”時,似乎也意識到這戶人家的男人可能不在了。
在外人看來,王樹,自然是一個人的姓名。王樹家,就比較模糊了,可以理解為王樹的家,也可以理解為王樹的家人,或是王樹家的媳婦。
當時,敏子媽媽就在跟前,但她并沒有在意那個男人去記誰的姓名,她倒是覺得那男人伸手抓出一只小雞崽,就知道是公雞、母雞好厲害呢,她問那男人:“你是怎么知道哪只是公雞,哪只是母雞的?”
那男人抬頭望了望敏子媽媽頭上掛的“夫孝”,說:“抬頭望天的是公雞。”言下之意是低頭擠在一起,或者是怕冷、害羞的那些小雞崽,長大以后都是母雞婆。
“噢——”
敏子媽媽輕噢了一聲,瞬間長了學問似的,又問他:“萬一,你抓出來的不是公雞而是母雞呢?”
那男人回答得很爽快,他說:“抓錯了不要錢。”
說話間,那男人又拽出一只抬頭望天的小雞崽來,示范給敏子媽媽看:“你看好嘍,這一只,我扔進筐簍里,不多一會兒,它又會把頭抬起來了。”
果然,不多一會兒,那只毛茸茸的小雞崽就仰起頭來四處張望呢。
敏子媽媽咂咂嘴,臉上頓時流露出很是佩服那個男人的神情來。
那男人跟敏子媽媽說:“公雞好斗,一出殼就好斗!它在雞群中,始終都要擺出一副爭斗的架勢來。”
敏子媽媽樂了。敏子媽媽心里想著公雞母雞原來是這樣呀!但這話她沒有說出口,便抱著敏子回家去了。
這以后,那個賣小雞的男人又來賣蓮蓬、賣鮮藕,秋天來收小雞款項時,他不知怎么就把敏子媽媽給勾走了。
敏子想媽媽時,奶奶就炒雞蛋、煎雞蛋,或是煮雞蛋給敏子吃,哄著敏子,說她媽媽到海島上幫助人家織漁網了,很快就會回來呢。
敏子忍不住想到海邊去看媽媽。奶奶就把大門給閂上,不許敏子往院子外面亂跑。
奶奶要做飯,要喂雞,還要給敏子補鞋子、添褲腳。奶奶顧不上看管敏子時,就讓敏子一個人在院子里追小雞、捉蜻蜓、給螞蟻畫地牢玩。偶爾,隔壁喜子媽媽要去場院里摘花生果,或是要去菜園子里拔青菜,不方便帶上喜子時,就會把喜子送過來,讓敏子奶奶給一起看護著。
那樣的時候,敏子會很高興。
喜子和敏子一般大。不過,喜子是個男孩子,他來了以后,就喜歡跟敏子鉆草堆、爬豬圈、捉迷藏玩。
敏子奶奶坐在當院的石磨旁,把兩個孩子閂在院子里,看管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她便在那兒“吱啦——吱啦——”地納那種麻臉的鞋底,或是把剛剛擇去的菜葉,再挑些綠色的,重新放回到籃子里。
回頭,喜子媽媽從場院里或是菜園子那邊拔了青菜回來時,會敲著敏子家的大門喊叫:“喜子——”
喜子在院子里聽到了,立馬就會回應一聲:“媽媽!”
“跟我回家啦!”
那時刻,敏子的奶奶便會顛著一雙小腳,去給喜子媽媽開院門。其間,喜子站在院門旁,等著敏子奶奶慢慢悠悠地走過來開院門時,他還會一聲一聲地對著門縫往外喊:“媽媽。”
“哎!”
“媽媽。”
“哎——”
院門開了,喜子撒著歡跟著媽媽走了,敏子卻站在院門前或是被奶奶閂在院門里頭,木呆呆地愣半天。
那樣的時候,奶奶會停下手中的活計,在鐵勺子里滴一點油星,給敏子煎雞蛋,哄著敏子不去想媽媽。
敏子呢,吃著奶奶的煎雞蛋,時而會噘起小嘴,把奶奶那油汪汪的鐵勺子給推翻,時而她吃著吃著還會吃出淚水來呢。
敏子奶奶看到那樣的情景,總是長長地嘆一聲:“唉——”
這一天,喜子媽媽又把喜子送來跟敏子一起玩,敏子不想與喜子鉆草堆捉迷藏。敏子跟喜子說:“我們今天裝成你媽媽敲門喊你吧。”
喜子問:“那怎么裝?”
敏子說:“我來裝你,你在門外當媽媽。”
喜子樂,喜子說敏子:“我是男孩子,你是女孩子,應該你來當媽媽,我還當喜子。”
敏子說:“不!我當喜子,你當媽媽。”
喜子想了想,反正就是做游戲,他便跑到院門外去拍門,學著媽媽的腔調,大聲喊叫著自己的名字:“喜子。”
敏子在院內,脆生生地應道:“媽媽!”
“喜子!”
“媽媽——”
“喜子——”
“媽——媽——”
…………
正在當院石磨旁納鞋底的敏子奶奶,聽到敏子在那兒熱切地喊“媽媽”,老人的心里先是咯噔一下子,隨之愣住了。她靜心聽著敏子那一聲聲撕心裂肺的呼喚,老人的心都快要被敏子給喊碎了。尤其是敏子連續喊了幾聲媽媽以后,突然放聲大哭起來時,奶奶眼窩里的淚水,撲簌簌地滾下來。
選自《三角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