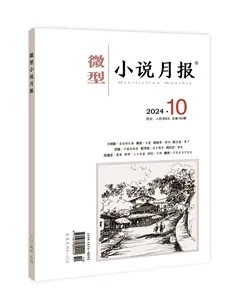回鄉(xiāng)偶書(shū)
張水昌做出這個(gè)決定時(shí),自己都嚇了一跳。他要學(xué)習(xí)家鄉(xiāng)話,地道的家鄉(xiāng)話。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半個(gè)月來(lái),張水昌親眼看見(jiàn)窗前那棵梧桐樹(shù)寬大的葉子,像一群受驚的麻雀,紛紛逃離枝頭。枝頭漸漸空虛起來(lái),孤獨(dú)寂寞。
張水昌不禁心生感慨。老了,退休了,有病了,一無(wú)是處了。張水昌覺(jué)得他的雙腿變成了樹(shù)干,他花白的頭發(fā)變成了焦黃的葉子,一片片旋轉(zhuǎn)著飄落。北風(fēng)吹落,沒(méi)有什么是比這一刻更蕭索的了。他嘆口氣,習(xí)慣性地從口袋摸煙,口袋空空如也,想起醫(yī)生的話:“想多活幾年,戒煙戒酒,清淡飲食,心情愉悅。”身體背叛了自己,連曾經(jīng)難以割舍的習(xí)慣也被迫放棄,他還能做什么?
“真真是沒(méi)意思。”張水昌腦海里突然閃現(xiàn)出這么一句話,一句口音極重的家鄉(xiāng)話。“真真”兩個(gè)字的讀音不是原有的zhēn,而是接近zhɑng的發(fā)音,且兩個(gè)字之間的調(diào)拐著彎,聽(tīng)起來(lái)極有韻味。張水昌一下興奮起來(lái),這句鄉(xiāng)音在他腦子里一直回蕩,他覺(jué)得格外親切,心里猶如十冬臘月喝下一杯熱茶般熨帖。
在張水昌的記憶中,這句話出自父親。張水昌父親說(shuō)這句話時(shí),鄰居正扛著一袋子玉米棒子來(lái)到他家道歉。鄰居收玉米時(shí)沒(méi)看清楚地界犁溝,掰了張水昌家一行玉米。父親哈哈笑著,抽了一口煙對(duì)鄰居說(shuō):“你看你這人,真真是沒(méi)意思,不就一行玉米嘛,至于這么較真嗎?”彼時(shí),張水昌和母親在玉米堆上掰玉米皮。小小的他看見(jiàn)晚風(fēng)在父親紫紅的臉龐上偷偷吻了一下便溜走了。父親額頭上深深的皺紋,像一塊塊正在游走的梯田,生動(dòng)極了。
嗬,父親,母親。張水昌的思緒有一瞬間的空白,一些尖銳的東西瞬間涌上來(lái)。張水昌搖搖頭,將心里翻滾的東西壓制回去。
張水昌試著把這句話說(shuō)了一遍,卻覺(jué)得不是那個(gè)味。他一遍一遍在腦中咀嚼著這句話的發(fā)音,再慢慢地說(shuō)出來(lái),還是不對(duì)味。他突然對(duì)自己一口標(biāo)準(zhǔn)的普通話厭惡起來(lái)。他此刻特別急迫地想聽(tīng)到這熟悉的鄉(xiāng)音。
周末,張水昌買了一些水果,驅(qū)車趕往故鄉(xiāng)。臨出發(fā)前,兒子跟他吵。
“你是不是閑得慌,老家都沒(méi)人了,就你這身體,一個(gè)人開(kāi)車幾個(gè)小時(shí)往老家跑,不想活了是不是?”兒子怒氣沖沖,眼睛里冒著火。
張水昌沒(méi)有多說(shuō)什么,只是說(shuō)了一句“我就是閑得慌”。他不怪兒子。兒子出生在城市,跟故鄉(xiāng)沒(méi)有一點(diǎn)血緣關(guān)系。可他不同,他的臍帶連接著故鄉(xiāng)。
按照導(dǎo)航的提示,車離故鄉(xiāng)越來(lái)越近。連續(xù)幾個(gè)小時(shí)開(kāi)車,張水昌疲憊不堪。但他仍舊抑制不住地激動(dòng)。故鄉(xiāng)的變化太大了。自從父親十年前去世后,他再也沒(méi)有回到過(guò)故鄉(xiāng)。父母不在了,他已經(jīng)沒(méi)有了歸路。張水昌減緩速度,車窗外熟悉又陌生的景物,讓他目不暇接。他的眼眶漸漸濕潤(rùn)了。
張水昌把車停在村口一塊空地上,下了車。寬敞的街道上,一輛白色汽車開(kāi)過(guò)來(lái)。
張水昌伸手?jǐn)r下了車。車?yán)镆粋€(gè)小伙子疑惑地看著他。
“哦,我是海根的兒子。”張水昌說(shuō)。
“噢。”小伙子一副恍然的表情。看樣子,張水昌的名字他聽(tīng)說(shuō)過(guò),樣貌卻是不認(rèn)識(shí)。
張水昌向小伙子打聽(tīng)了幾個(gè)老人的名字。小伙子說(shuō)都不在了。
張水昌想了一下,說(shuō):“大中叔呢?”
“大中叔倒是身體還行。他家往前走,往右拐個(gè)彎,紅磚三層樓就是。”小伙子說(shuō)的話大部分是普通話,夾雜著一小部分的方言。
謝過(guò)小伙子,張水昌順著小伙子的指示往前走。賀知章那首《回鄉(xiāng)偶書(shū)》倏地涌上心頭:“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無(wú)改鬢毛衰。兒童相見(jiàn)不相識(shí),笑問(wèn)客從何處來(lái)。”此刻對(duì)于張水昌來(lái)說(shuō),是真實(shí)再現(xiàn)啊。而張水昌覺(jué)得慚愧,賀知章在外游歷多年,鄉(xiāng)音仍未改,而自己卻連一句完整的家鄉(xiāng)話都說(shuō)不標(biāo)準(zhǔn)。
原本張水昌是要先回父母居住的老屋看看。他猶豫了片刻,改變了主意。老屋里有太多回憶,有太多父母留下的氣息。他不敢輕易去觸碰這些事物,只能將它們封存起來(lái)。現(xiàn)在,他已過(guò)花甲之年,越是想把記憶封存忘記,記憶越是清晰。
張水昌一路走著,碰到熟悉的不熟悉的人打著招呼。這些人的方言里已經(jīng)有了不同程度的變化。拐個(gè)彎,他看見(jiàn)幾位老人坐在大門前的大石頭上聊天曬暖陽(yáng)。深秋的風(fēng)已然有了涼意,幾位老人的臉頰卻有一些微微的潮紅。陽(yáng)光的暖意剛剛好。
“大中叔、來(lái)寶叔,你們好啊。”張水昌幾步跨上去,激動(dòng)地跟幾位老人打招呼。
“這是……水昌?”幾位老人也認(rèn)出了張水昌。
“是,是我。我來(lái)看看你們。你們身體還好嗎?”
張水昌找了幾塊磚頭摞起來(lái)坐在上面,聽(tīng)?zhēng)孜焕先死页!_@個(gè)說(shuō)東家生了個(gè)大胖小子,十斤呢。那個(gè)說(shuō)西家娶了個(gè)洋媳婦,那眼睛藍(lán)瑩瑩的。這個(gè)說(shuō)李家承包了一百畝土地種藥材呢,聽(tīng)說(shuō)賺大發(fā)了。那個(gè)說(shuō)王家的孩子考上博士了,這博士是啥呀。
此時(shí),陽(yáng)光像嬰兒粉嘟嘟的臉頰般柔美爽滑,輕輕地貼在張水昌的臉上。他的臉頰竟然也起了潮紅。他一會(huì)兒豎起雙腿,一會(huì)兒盤起雙腿,愜意地享受著這一刻的舒適。他不記得他有多久沒(méi)有像這樣放松過(guò)了。
返回時(shí),夕陽(yáng)掛在山梁的尖尖上顫悠,一不留神就會(huì)滾落。張水昌站在村外,回望村子,兒時(shí)的云朵向他飄來(lái)。這個(gè)時(shí)候,各家的炊煙升起來(lái)了。不同樹(shù)枝冒出不同顏色的炊煙,你追我趕,就看到每戶人家鍋里的飯。炊煙是村莊的頭發(fā)呢。張水昌小時(shí)候這樣比喻。
張水昌坐在書(shū)房的椅子上,靜靜地聆聽(tīng)著他悄悄錄下的幾位老人的聲音,一句句鄉(xiāng)音濃郁純正,該揚(yáng)就揚(yáng),該拐就拐。他一句句跟著說(shuō),品咂著方言里的韻味。他相信,只要他經(jīng)常回去看看,每天聽(tīng)錄音,用不了多久,他一定能重新學(xué)會(huì)那熟悉的親切的不摻雜任何雜質(zhì)的鄉(xiāng)音。
門外,隱隱傳來(lái)兒子的聲音:“真是不要命了。”
張水昌淡淡一笑。
選自《荷風(fēng)》
2024年春夏卷
- 微型小說(shuō)月報(bào)的其它文章
- 萬(wàn)先生與方女士
- 天職
- 守鳥(niǎo)人
- 告別
- 禮物
- 愛(ài)情的語(yǔ)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