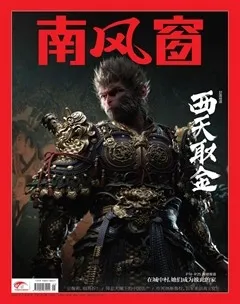放生變“放死”,亂象何以出現?

2019年,白玉梅父親患癌,為了給父親祈福,她堅持每天放生。
一年后,父親去世,但白玉梅放生的習慣,堅持到了現在。只不過當下她放生的所求,變了。
“我現在每天放生是為了找工作。”白玉梅告訴南風窗,此前她干了20多年的公司沒扛住壓力,裁了一批年齡大的員工,她是其中一個。
被裁后,找工作受挫,白玉梅想了下,覺得是自己福報不夠,應堅持日日放生。所以,她每天會去菜市場買一兩斤泥鰍、河蝦或者螺螄,去河邊放生。
而買放生動物的錢,是她通過網絡貸款借來的。“因為我找不到工作,體質又不好,老生病,花錢多,所以就借錢放生。”白玉梅說。
白玉梅堅信,放生是莫大的福報,所求皆能如愿。所以,她也熱衷于鼓勵他人參與到放生活動中。可她不知道也不在意的是,放生在當下的輿論環境中,已經走向了某種“詭異”氛圍和讓人難以理解的方向。
而這,基于近期接連出現的“放生亂象”和“奇葩”放生行為。
2024年9月8日,據媒體報道,上海蘇州河42公里岸線貫通后,吸引了不少人專程跑來放生。而錯誤的放生讓蘇州河多次因大量死魚登上熱搜,今年還創下了1天撈出一噸死魚的“新紀錄”。
2022年,蘇州河撈出的死魚約6.82噸,今年已撈出7.5噸,預計到年底將超過去年的7.9噸。
此外,8月,河北廊坊和吉林松原,各有人在小區內放生大量蟑螂,引發爭議。更出乎意料的是,此前有媒體報道,有人在河邊“放生”礦泉水和魚豆腐;也有人放生巴西龜、“清道夫”等外來入侵物種,給當地動物生態帶來威脅。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環境經濟與社會政策委員會委員王豁告訴南風窗:“放生的初衷雖好,但盲目放生卻可能帶來嚴重后果……(甚至)放生相當于放死。”
不過在白玉梅眼里,不管是蟑螂或是其他,皆是生命,都可以被放生并由此獲得福報。
放生之人,皆有所求
白玉梅參與放生,是很早的事情。
2007年,自覺姻緣不順的白玉梅皈依了“佛門”。那年,她26歲。此后,白玉梅就跟師兄們一起放生。再后來,她加入了一個放生團體,進行了多次放生,那個團體人多的時候有近萬人。
2019年父親患癌后,她開始獨自每天放生,并堅持到了現在。她堅信書里說的,放生是莫大的功德,可以滿足所有的心愿。
“放生,是人們出于對生命的尊重、宗教信仰或個人祈福等目的,將捕捉或養殖的動物放歸自然。”王豁告訴南風窗,這一源于宗教信仰的傳統習俗,如今已成為一個社會現象。
王豁表示,目前民間放生群體的規模龐大,且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大體上,放生可分為個人放生和有組織有規模的團體放生。
“個人放生,通常是出于宗教信仰、祈福等目的購買少量動物放歸自然,或出于偶爾救助個別動物,將其放生到自然環境中。”王豁說,而有組織有規模的放生,則是由團體策劃、組織的大型放生活動,涉及大量動物,“若是深究,背后常涉及野生動物非法捕捉、貿易”。
2021年,長江生態保護基金會曾對武漢長江流域公眾放生現狀做過調查,結果顯示,參與放生的群體廣泛,既有佛教信徒,也有無宗教信仰者,且放生群體及活動已經呈現全國化、網絡化協同。
運氣不好就放生泥鰍、黃鱔,可以轉運;身體不好或者求長壽,就放生烏龜;小孩子要考試,就放生鯉魚;求子的放生魚籽或者懷孕的魚……
“(放生)在全國都有分布,沿海發達地區規模化程度較高,放生隊伍非常龐大。”長江生態保護基金會“長江有魚”項目負責人陳中和告訴南風窗,經他們調查了解,當下的放生呈現出幾個特點:資金規模大,“一些放生團體每年累計放生資金達百萬級”;活動組織頻次高,每周每月都有活動;穩定的參與人群(民間信眾、環保人群、公益人士);參與人群呈年輕化趨勢。
“原來我們覺得放生的可能都是年紀大的人,但其實現在年輕人慢慢成了放生團隊中的重要角色。”陳中和說,在當下的放生活動中,年輕人會承擔組織活動、聯絡捐贈人和做數據報表等重要工作。
此外,上述調查還提到,民間放生主要目的在于祈福,同時也是人們追求自我內心、祈求美好愿望的一種方式。
按白玉梅所言,放生之人,皆有所求。“有的人是為了求子,有的是為了找工作,有的是為了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有的是為了罹患癌癥的父母能康復。”白玉梅說,她現在放生是為了能找到一份工作。
對另一些人而言,放生的吸引力在于增加財富。社交媒體上,不少人分享放生后帶來的改變,有說自己收入增加了多少倍、天上掉餡餅的事輪到了自己;也有說自從放生后,自己生意好得像是坐上了火箭;更有人寫長文論述,稱放生是其試過所有方法中來財最快最猛的方法。
白玉梅聽他人說過,放生不同的動物,代表不同的寓意,但她不怎么在意。
社交媒體上,有人為此做了總結:運氣不好就放生泥鰍、黃鱔,可以轉運;身體不好或者求長壽,就放生烏龜;小孩子要考試,就放生鯉魚;求子的放生魚籽或者懷孕的魚……
因而,每一個被放生的動物,都承載著一個世俗的心愿。
放生、殺生,一步之遙
“放生動物一般是去農貿市場、商戶小販或生鮮市場買的。”白玉梅說,這其中有兩種考量:一是出于方便,二是放生的人都認為,菜市場的動物是最容易被人吃掉的生命,因而放生它們更有功德。
王豁也告訴南風窗,水產市場是最常見的放生動物來源之一。“鯉魚、鯽魚、泥鰍等水生動物因價格低廉、易于購買,成為放生者的首選。”王豁說。此外,寵物市場也是放生動物的來源之一,龜、蛇、鳥等寵物被一些人購買后被放生或棄養。
而據一些調查志愿者的反饋,一些規模較大的團體放生活動,甚至會從養殖場或其他專門供貨商批量購買動物。
白玉梅在獨自放生前也參加過放生團體。“厲害的放生團隊,幾千幾萬人的都有。大部分成員是我們當地的,也有從周邊城市過來的。這些人都是佛門弟子,在家修行的居士。”白玉梅說,放生團體一般有自己的微信群,每次放生活動前會招募人員和款項,再定好放生時間、地點,到時用貨車從水產市場或養殖場拉魚或其他動物到目的地,大家一起誦經放生。
而陳中和告訴南風窗,從菜市場或養殖場買來的魚等,可能并不適合放生。“它們都是人工養殖的,被放生后不一定能適應野生環境。”陳中和說,對這類魚養殖的目的就是供人食用,一般經過基因改造或是外來物種,如果把這些魚放到野生環境里,會對原生魚類造成基因污染或危及原生魚類的生存環境。
此外,這些被買來放生的魚,此前疫病都是通過人工投放藥物控制,如果脫離人工養殖環境,很可能會把疫病傳染給其他魚類。
王豁也指出,由于缺乏科學知識和對生態系統的了解,許多不當放生行為反而導致了動物的死亡,甚至破壞了當地的生態平衡。“比如將外來物種放生到本地水域,可能導致本地物種的滅絕,或將淡水魚放生到海水中,則會導致其死亡。”
放生時不能放外來物種,這點白玉梅清楚,但從菜市場賣魚蝦放生是她堅持做的事。每次放生,白玉梅都要進行簡單的放生儀軌,稱名(各大佛和菩薩名號)、懺悔、皈依、念佛、放生、回向。白玉梅稱自己的這套儀軌已屬簡單,幾分鐘就能做完,而有些放生團體的儀軌,可能要進行一個多小時。
而實際中,長時間的放生儀式,是讓放生動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白玉梅反對這種冗長的放生儀式,她說她在佛經上看過,放生儀軌不宜太長,否則有些“眾生”很容易因為拖延時間而死掉。
但他們放生群體還有一個說法,“只要不是你(直接)造成的死亡就不算你殺生”,這種在運輸途中死去或放生后死去的情況,是動物自己的因果。不過,白玉梅跟南風窗強調,放生的人在買魚蝦的時候就應該考慮到運輸時長,給它們充足的氧氣。
而對放生的人來說,這些不算是最緊要的事情,如何避免自己放生的魚蝦被別人撈走才是。
貓鼠游戲
白玉梅每次放生,都要謹慎地避開有人釣魚的河道,她怕自己剛放生的魚蝦被他人釣走或捕撈。
也由此,放生群體和釣魚、捕魚群體常年在進行貓鼠游戲。往往是前腳有人放生,后腳就有人把放生的魚撈走,再進入市場循環。
放生群體和釣魚、捕魚群體常年在進行貓鼠游戲。往往是前腳有人放生,后腳就有人把放生的魚撈走,再進入市場循環。
“這兩年大家沒有浩浩蕩蕩的一群人放生了,都非常低調,三五個一伙,在不同的地段放生,因為捉魚的人太多了。”白玉梅說,如果一次性有成百上千人放生,就會引起捕魚人“圍攻”。
為了避開這些“捕獵”的人,放生團體甚至到深山老林去放生。“到山里放生,有河的話可能是放魚蝦一類的,沒河放蛇或鳥,放牛羊的也有。”白玉梅說,市面上買不到蛇,有專門賣蛇的,“暗地里賣給放生的人,(不過這是)國家禁止的”。
王豁告訴南風窗,某種程度上,某些有組織的放生已經形成了一條產業鏈,涉及動物的捕撈、運輸、銷售等環節。“比如,我們的志愿者曾發現,放生組織者一方面組織放生,過一會兒又去悄悄捕撈或捉回,下一輪繼續賣。”王豁說,地下產業鏈的形成,加劇了放生的商業化,也催生了放生亂象。
他以鳥類放生為例向南風窗解釋,放生人群從鳥市或其他地方購買的鳥類,其實是來自野外捕捉的,背后往往隱藏著一個殘酷的真相:大量的同類在捕捉、運輸的過程中死亡。
“捕捉野生鳥類時,通常會使用鳥網、粘網等工具,這會導致許多鳥類受傷甚至死亡。”王豁表示,被捕獲的鳥類往往有強烈應激反應,又加上裝在狹小的籠子里,在長時間的運輸過程中,它們缺乏食物和水且環境衛生條件差,很容易生病死亡。
這導致許多鳥類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就已經死亡,而為了保證市場供應,鳥販子往往會捕獲大量的鳥類,以彌補運輸過程中的損失。
因而,王豁認為,這類放生并非善舉,反而導致悲劇,使放生變成“放死”。
陳中和也表示,民間放生目前已經成為一門生意。他此前接觸的放生活動中,有些組織者本身是養殖戶、水產批發商或是賣宗教用品的。“其實有不少跟這些(產業)相關的人在做這些事情。”
不過,這也并不意味,針對民間放生應“一棒子打死”。長江生態保護基金會前述調查報告提到,放生人群的目的雖與科學放流不同,但大多也是正向需求,宜積極引導,不應一味排斥。
科學放生,也是保護生態

“以正確的方式進行,放生也是一種保護生態的方式。”陳中和說,民間放生雖無法像科學放流那樣規范,但應滿足一些基礎的要求:選擇本土物種,不放生外來種和雜交種;放生地要合適,選擇相關部門指定或開放性水域;放生前要跟相關部門報備;不要追求放生數量等。
王豁表示,科學的放生首先要守法,按照法律要求履行報批程序;其次應該選擇本地物種,且放生地點應適合動物的生存。放生前,最好咨詢相關專業人士的意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傷害。放生后,進行回訪,了解放生動物生存狀況,并及時采取措施應對可能出現的問題。
王豁和陳中和都認為,除了倡導,對放生亂象的監管也同等重要。
陳中和告訴南風窗,目前,野生動物保護法,長江保護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規定、刑法等,都對放生做了相關的規制和要求。
但對民間放生的監管還是有難度,因為放生比較分散和頻繁,每天都在進行,很難去實時監管。而且現在主要是漁政部門在執法,其執法力量、人員和能力等相對不足。
不過,2023年2月3日,全國首例非法投放外來物種民事公益訴訟案在南京宣判,對放生亂象的治理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放生許久,盡管工作還是沒有找到,但白玉梅依然相信放生是能帶來好運的。
據《法治日報》報道,2020年12月15日,徐某等人到常州市錢資湖放生時,被相關工作人員和周邊群眾阻止,后一行人偷偷轉至金壇長蕩湖某港口,放生了2.5萬斤鲇魚。
不久后,徐某放生的鲇魚大量死亡。長蕩湖漁政監督大隊組織人員打撈,歷時10天累計打撈已死亡鲇魚2.02萬斤,支付打撈費、存儲費、無害化處置費等應急處置費用共計9萬余元。
后經專業鑒定,徐某等人放生的鲇魚為革胡子鲇,系外來物種。
2023年2月,南京環境資源法庭依法判決被告徐某承擔因其非法投放外來物種革胡子鲇所造成的生態資源損失3萬元、服務功能損失5000元、事務性費用1.8萬元、懲罰性賠償5000元。同時,賣魚給徐某并協助其放生的商家劉某也被判對上述款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王豁認為,這是很好的范例,他建議以后這類案件的開庭審理,可以對公眾直播,并且邀請中小學生來聽,提升有關“非法放生”的公眾意識。
此外,針對放生亂象,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也提出,嚴厲打擊非法引入外來物種行為,實施重大危害入侵物種防控攻堅行動,加強“異寵”交易與放生規范管理。
2023年11月1日,國內首部專門規范野生動物放生的地方性法規——《廣州市野生動物放生管理規定》開始施行,其中明確要劃定野生動物放生區域,建立野生動物放生信息管理平臺,建立放生行為日常監管機制等。
作為堅定的放生者,白玉梅也希望相關部門可以給他們劃定一片區域或建一些放生池供他們放生,以避免他們放生的動物被他人撈走。
放生許久,盡管工作還是沒有找到,但白玉梅依然相信放生是能帶來好運的。
她拿之前的經歷舉例:“我以前上班的地方是商場,柜臺里面三個人和我搶生意,我搶不過她們。后來我放生,一直做到銷冠,她們做不到大生意,那種蠻橫無理、要退貨的顧客,總會遇到她們的班上。”
說完這些,她又想到一個例證:“我老早的時候騎車經常被人撞到,可是我現在開車有時候開得快,也從來沒有遇到過車禍,這絕對是放生帶來的。”
(文中白玉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