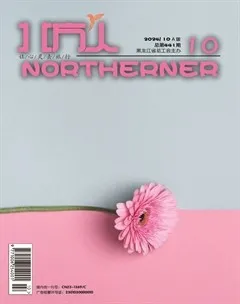不能度己,何談度人
“首先為你們的不幸感到惋惜,”他說,“我是OPO(醫院人體器官獲取組織)辦公室的協調員,接下來由我協助你們完成器官捐獻事宜。”
“目前患者腦死亡診斷明確,器官功能符合捐獻要求。一旦移植成功,這些器官將伴隨移植受者的生命存活下去,而你們親人的愿望也將得以實現。”
“但是,”他繼續說,“人的大腦功能沒了,其他器官也會很快出問題,所以咱們在流程上要抓緊。”講到這里,他把早已準備好的文件和筆拿了出來。
患者的父親從兜里掏出眼鏡盒,哆嗦著打開,把老花鏡戴上。他拿起筆,握筆的手也開始止不住地抖……
這時,患者的妻子站了起來。她語氣平靜地說:“我后悔了,我不同意。”
深昏迷的患者
患者為男性,35歲,騎摩托車時在山路上發生車禍,好幾十公里的時速,頭部劇烈地撞擊在路邊的電線桿上,當時就沒了心跳和呼吸。盡管急救人員的現場救治讓患者恢復了心跳,但他的腦組織損傷太重,逆轉的希望微乎其微。
治療了3周,他沒有一點好轉,所有的征象都指向我們最不愿看到的結果:腦死亡。
每天來探視患者的有他的父母、妻子,以及一對兒女。他們站在ICU門口圍著我,聽我給他們講患者的病情變化、對患者的病情進行解釋,還有即將對治療方案做出的調整。其實對這個患者的家屬,我完全不需要介紹得這么詳細。患者的父母都是做醫療工作的,他們退休前在一家大學附屬醫院工作,父親是資深的泌尿外科教授,母親是婦產科的護士長。他們每次顫巍巍地給患者擦完身子,和我簡單地溝通檢查結果和治療方案后,從不多問一句,很顯然他們對患者的未來看得很清晰。我第一眼見患者的父親時他還挺著身子,3周里,他的背越來越彎。每次他們來探視時,我都想和他們多說幾句。但說什么呢?大家都是同行,我想不出什么話語可以安慰他們。
患者的兩個孩子看上去都沒到上學的年齡,大人說話的時候,他們倆蹲在地上嬉笑打鬧。患者的妻子一邊聽我說病情,一邊不時地回頭輕聲呵斥:“小點聲,大人說話呢!”她個子很高,是附近一所教培學校的英語老師,舉手投足間透著干練。每次聽我說患者的哪項指標不好,她都會很激動地說:“他這么年輕,薄醫生你看看他的這對兒女,無論他變成什么樣,我都不會放棄,變成植物人我也養他一輩子。”
她這么說,我可以理解。除了真愛,她堅持讓他接受治療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她混淆了植物人和腦死亡的區別。
“植物人”只是大腦皮層受到嚴重損害或處于抑制狀態,但是患者的生命中樞——腦干功能還在,還有自主呼吸和腦干反應,有醒來的微弱可能,雖然希望很小,但人還活著。腦死亡則是包括腦干在內的全腦功能不可逆轉地喪失,一旦作為呼吸、心跳中樞的腦干死亡,人的呼吸、心跳遲早也會停止。醫生可以用藥物維持患者的心跳、血壓,用呼吸機幫助患者呼吸,但這只是人為地延長了患者存活的時間。大腦是人類意識的載體,腦死亡意味著作為人的本質特征的意識已經消失,換句話說,這個人實際上已經死亡。
腦死亡評定
有一天下午,探視時間過后,那名患者的家屬找到我。我帶著他們從病房往我的辦公室走,前后不到二三百米的距離,老兩口緊跟著我,而患者的妻子遠遠地跟在后面。
到了辦公室,患者的妻子最后進來,她關上門后背倚著門,沒抬頭看我們,只是低頭不停地刷著手機。患者的父親說:“3周多了,我們想給他做個腦死亡評定,有個判斷我們也好做下面的決定。”
“決定什么?您想要決定什么?”沒等老人說下去,患者的妻子大聲地喊了起來,“我說過很多次了,他不是腦死亡,他還能醒,他身體那么好!”因為激動,她滿臉通紅,音調很高,聲音顫抖著。
兩位老人一聲沒吭,我猜他們早已料到兒媳婦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大家沉默許久之后,我說:“一直這么蒙著眼走路也不是長久之計。做一個吧,不論什么結果,大家心里也有個數。”
她不置可否。
第二天,評估團隊來了。他們認真地聽了我的匯報,看了患者住院以來所有的影像學資料和其他的資料。他們檢查了患者的生命體征,又給他做了腦干反射檢查、自主呼吸激發試驗,還帶了幾臺儀器,有的用來做腦電圖,有的用來測腦組織的血流信號,有的用來做誘發電位。所有這些都會為評估腦功能提供客觀依據。
第三天,評估團隊又來了一次。臨走時,他們說:“太可惜了,這么年輕,趕緊商量一下后面怎么辦吧。”
我們想捐獻
雖然評估團隊沒有直接提到器官捐獻,但我,還有患者家屬都能聽出他們的意思。
那天,他們誰都沒說話。我想,接受這個結果確實需要時間,我沒去催他們趕緊對下一步的計劃表態,我對他們說:“你們也別太傷心,確實病情太嚴重了。”
幾天后,患者開始出現高熱,也發生了尿崩。這幾乎在我的意料之中。我還像做腦死亡評定之前一樣,每天守著他,時刻盯著他身體的每一項指標。
有一天,患者的父母又來找我,可能他們也意識到永別真的要來了。
他父親說:“薄醫生,我們想了很久,有個事兒我一直想對你說,我們全家,包括我兒子,都登記過器官捐獻。”他的語氣很堅定,“我們想捐給有需要的人。”
當他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我竟不知道怎么接,我的心猛然間緊了一下,有種類似心臟缺血、缺氧那樣的疼。
我想不到他們最后能達成一致。我問他:“您和您的兒媳婦商量好了嗎?”
“她完全同意。謝謝你,薄醫生,我們都知道你很盡心。”老人說。
“我馬上通知醫院OPO辦公室,他們會來人安排接下來的事情。”我說。
我后悔了
拋開情感,客觀地說,這個35歲的腦死亡患者確實是很好的供體。他年輕,出車禍前沒有任何基礎疾病,所有能捐獻的器官都充滿了活力,沒有感染,血管彈性好,器官功能儲備完好,無論是角膜、腎臟,還是肝臟,功能都完好無損。這樣的器官移植到有需要的患者體內,不僅能救命,而且移植效果和患者未來的生存質量可能都會很好。
但那天,當患者的父親馬上要簽署器官捐獻相關文件,患者的妻子站起來說“我后悔了,我不同意”時,我反而松了一口氣。這是種很奇怪的感覺,我甚至微微有種背叛了醫學偉大的奉獻精神的感覺。
我平心靜氣地對患者的家屬說:“還是要抓緊,別錯過了機會。不論你們做什么樣的決定,都不會影響我們的治療,接下來我們會繼續好好治。”
但是,患者的病情還在快速惡化。我想拉住他,想給他的家人更多時間,可我發現自己越來越無力。他一輪一輪地感染,我給他輪換著用各種類型的抗生素,他肺部感染的多重耐藥菌對所有常用的抗生素都耐藥,身體內部也開始出現深部真菌感染的跡象。他的臉龐、四肢、軀干的肌肉完全萎縮。他的生命像斷了線的風箏般快速墜落。
又過了幾天,患者的妻子慌了,她找到我,說:“我想清楚了,我應該尊重他,我想現在、立刻、馬上進行器官捐獻。”
此時,已經太晚了。
他走的那天,她抱著他已經涼透了的身體號啕著:“我錯了,對不起,對不起!”
悲憫與理性的糾纏
這個病例最讓人遺憾的地方在于,患者是有很大機會捐獻器官的:他的父母是醫生,懂得腦死亡的不可逆,更清楚捐獻器官、拯救他人對患者、對社會、對活著的人的價值和意義;而他的愛人是老師,有學識、有愛心,她只是在情感上一時過不去;更關鍵的是,患者生前登記過器官自愿捐獻,他有這個意愿。如果當時我能夠堅定有力地多去鼓勵患者的愛人,那她很可能就同意了。為什么?為什么我沒能推她一把,她幾乎就在同意的邊緣了。
我是患者的主治醫生,我每天給他治療,我眼里全是他、他滄桑的父母、他尚不懂事的孩子、他執著不放手的妻子。我每天盯著他的血壓、中心靜脈壓、尿量、電解質、血氧……我會為他生命體征的短暫穩定而欣喜,也會為一個指標的異常而焦慮。我會反復思索、檢索文獻,還會找各個科的同行一起解決問題。我原以為醫生做久了會越來越中立、冷靜地看待患者的病痛,但沒想到,我越了解患者和他的家人,就越發現在這場和病魔的浴血奮戰里,我早已把他們當成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深深地陷入他們的生命中。
器官捐獻的價值和意義我懂,但面對我的患者,我更能真切地感受到家屬的痛、家屬的苦、家屬的無奈和不舍,而對于正在苦等著器官移植的人,我雖然能夠理解他們的渴望,但無法感同身受。所以我像我的患者的親人們一樣不甘心、不舍得。
當然,我舍不得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我聽他妻子說過很多關于他的事,從而得以走進他的世界,甚至對他有了朋友一樣的感覺。
她對我說:“我看ICU墻上掛著很多自駕去西藏無人區的照片,那是你拍的吧?我愛人也喜歡自駕。
“我們倆是2010年認識的,后來約了幾個朋友去稻城亞丁。到了亞丁村的民宿里,由于缺氧再加上發燒,我覺得我堅持不住了,我想連夜撤回去,再好的風景我也不看了。可他說,人生所有的事別管有多難,就分為兩種:堅持下來的,放棄了的。他一間一間地去敲民宿的門,去給我借氧氣瓶。第二天一早,他拉著我的手,我們一起看到了日出。”
對他這樣一個不輕言放棄的人,我同樣不舍得放棄他。
把情感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的一場修行,而我越來越相信,救命這件事是修行中的修行。在我看來,所謂醫生的修行,則是在治療患者的過程中治療自己。
人類真正救命的知識不在書本上,而是在救命現場,在命懸一線、云譎波詭、瞬息萬變的臨床實踐中。這是關于人類的苦難、堅韌、不放手,是關于醫學的悲憫、安慰和日趨堅定。醫生不過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但他要體恤人間最痛的苦,見證最深的愛、最復雜的人心、最無奈的放棄、最不舍的告別,感受世上最痛苦的無助;他要日漸堅強,更要良知未泯,要睿智,更要善良;他要清洗、縫合別人的傷口,同時也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舔舐、包扎自己的傷口;他會無時無刻不在科學的理性與人性的悲憫里糾纏,永遠不可能像個旁觀者一樣置身事外。
有人說,醫生度人不度己。要我說,這不對,如果我連自己都度不了,何談度人?
當死亡化作生命
在收到人體器官志愿捐獻卡后,我一直把它藏在車里。
但是經歷這個病例后,我想找個時間和妻子好好聊聊,我很擔心她也會像這個病例中的妻子一樣舍不得。
那天下午,我開車帶她去郊區轉轉。她坐在車后座上,我先從這個病例講起,她邊聽邊落淚。果然,如我擔心的那樣,聽完后她擦了擦眼淚,說:“如果是我,我也不舍得,那么親的人,誰忍心在他離開后還要把他的皮膚劃開,切下他的器官捐給素昧平生的人?”
我說:“你知道一個人的器官進入另外一個人的身體里會發生什么嗎?有個做了肝移植的女孩,術后能進食后的第一餐,她就讓她的母親給她買漢堡。這太不可思議了,以前她從不吃漢堡。這次,她不僅吃了,還覺得很好吃。
“她想,會不會是捐獻給她肝臟的那個人生前喜歡吃漢堡呢?在有些國家,移植手術完成一定時間后,獲得器官的人是有機會得到捐獻者信息的。后來,她終于知道捐獻者是個男孩。她找到男孩母親的電子郵箱,一封接一封地寫信表達她的感恩之情,講述她接受移植后身體的變化,以及她的重生。但每次寫的信都如石沉大海。
“為什么這個男孩的母親不愿意給她回信?
“這位母親始終處在痛苦和愧疚中。她愧疚沒有好好管教兒子,以致他在一場槍擊案中喪命。她自責、內疚,如跌落深淵般痛苦。
“最終,她還是忍不住給這個女孩回了一封信。信不長,她在信中講了兒子的成長經歷、她對他的愛,還提到了兒子喜歡吃漢堡。
“女孩收到信后身體顫抖,眼淚奪眶而出,她高聲地喊,我就知道,他喜歡吃漢堡!
“男孩的母親終于釋然了。她知道兒子的肝臟不僅活著,還改變了另外一個人的一生,同樣的還有他的肺、心、腎臟、角膜……它們已經化作新的生命。”
在醫學的每個領域,我們畢生都在與死亡做斗爭,而在器官移植領域,死亡是我們的另一個起點。我們可以換個角度審視:器官捐獻不是放棄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讓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活下來;它其實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幾乎放棄自己的所有,讓你身體的一部分活下來。
我繼續給妻子講。
“有個小姑娘在車禍中喪生,她的母親痛不欲生,但還是忍痛把她的器官捐給了不同的人。過了幾年,這個母親去參加醫院組織的聚會(有些國家為了鼓勵自愿捐獻,受者在手術一段時間后是有機會見到供者的親人的)。
“人們在綠地上親密地交談,追憶器官捐獻者的往事,表達對他們的感激。而這個母親獨自坐在角落里抽泣,因為對女兒無盡的思念。
“一位高大的男士向她走來。他蹲在她面前,掀開自己的衣服,并遞給她一把聽診器。
“他說:‘女士,你聽聽我(的心跳)。’
“那是她女兒的心臟在跳動,她仿佛在說:‘媽媽,你不要哭,你聽到了嗎?我并沒有離去。’
“這個母親哭著哭著就笑了。”
我把我的人體器官志愿捐獻卡遞給妻子,說:“這是我的,我怕你不高興,就一直藏在車里。”
我說:“萬一有一天我出了意外,我說萬一,你記著把我捐了。”
妻子泣不成聲。“我可以考慮,”她說,“但前提是你得好好地活著,這比什么都重要。”
(摘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命懸一線,我不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