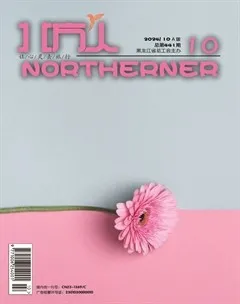我所追求的只在于寫作本身

二〇一六年有一段時間,我暫住在一個朋友的工廠宿舍里。有一天他對我說,和我同住的人告訴他,我每晚把所有時間都用來讀書,他沒想到我竟然這么好學。他用了“好學”這個詞,這讓我愣了一下,當時我已經三十七歲,有很多年沒聽到過這個詞了。隨即我意識到——當然不是單從這件事上,而是從我對他方方面面的了解上——對他來說,讀書就是為了提升自己、掌握技能、獲得知識,然后以此來改善生活;假如不帶有這些目的,那讀書就是浪費時間。可是我不知道,像《包法利夫人》《卡拉馬佐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城堡》《追憶似水年華》這樣的小說,我讀了之后如何學以致用?幸好他不清楚我在讀什么書,否則他就會對我失望和擔憂,因為在他看來,我的閱讀是在虛擲光陰。
當時,我剛讀完他推薦給我的幾本書,書名我現在記不起來了,內容是關于創業和互聯網思維之類的,因為我和他正好在合伙搞生意。或許他是以為,我又搞來了幾本同類的書,每晚在宿舍里繼續進修和提升,為我們的創業打好基礎。可是那幾個晚上我其實是在讀布考斯基。我對這件事記憶猶新,是因為當時我覺得,用“好學”來形容讀布考斯基好像有點反諷——我能通過讀他學到什么呢?學他如何玩世不恭、放任自流,還是如何任性地把所有事情搞砸?我讀布考斯基別無其他,僅僅因為喜歡而已。
我早就清楚,文學不能幫我獲得別的東西。比如說,它不能為我找到一份工作。當然,我也不需要它為我找工作。文學只能帶我進入文學,而這就是我想要的。不過我朋友的觀點也無可厚非,他把讀書看作一種手段,他讀的也大多是工具書,那當然就要考察其有效性,去區分有用和沒用。
至于文學到底有什么用,或者它應不應該有用,莊子有句話經常被人引用:“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這句作為總結的話,出現在《莊子·內篇·人間世》的結尾,在原文中有比較明確的意指:莊子認為人生于亂世,假如既有才華也有志氣,就很容易受到上位者擺布,成為他人的工具,甚至淪為犧牲品;反倒是那些沒有才華和志氣的人,甚至是身體有殘缺的人,最后得以保全自身。不過今天人們在引用這句話時,一般已摘除了原文的語境,使它的能指變得更加豐富。
比如在我的印象中,做哲學的人就喜歡借此以自況,因為大眾普遍認為哲學研究沒什么實際用途,對此解釋起來未免費勁,倒不如借莊子之言以解嘲。但“無用之用”對于哲學研究者來說,當然不是指成為廢才以保命,而是指哲學一般不會直接、明確和具體地作用于我們生活的某個方面。但它會作用于我們的精神方面——它關注更根本和終極的問題,更抽象并囊括萬事萬物。
閱讀和寫作之于我的情況也與此相似,起碼在二〇二〇年之前,我的寫作幾乎不為人知,也沒帶來過什么經濟回報。至于二〇二〇年之后情況有所改變,那是因緣和運氣使然,機會掉到了我頭上,我恰好接住了而已,并非出于規劃或爭取。我從二〇〇九年開始寫作,早年也投過稿,也渴望發表或出版,但發表和出版從來不是我寫作的目的。對我來說,寫作首先是我的個人表達,是一種以審美對待人生的形式,能發表或出版固然好,不能我也不會為之調整。
《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后,我經常被問到,將來會不會選擇一份寫作方面的工作。這個問題從前我沒考慮過,因為以我的履歷、學歷和年齡等條件,根本就不可能找到這類工作。但是現在既然有人問了,那我也只好認真想一下。我覺得自己并不抗拒通過寫作掙錢,比如從事一份文字工作——當然我會對工作內容有所挑剔——只是我不認為工作性質的寫作能代表我,我仍然需要在工作之余保持個人寫作,這才是對我真正重要的事情。而在個人寫作方面,我所追求的就只在于寫作本身,而不在寫作之外的任何地方。我認為藝術是務虛的——我是指狹義的藝術——它不是工具、手段或途徑,而就是目的本身。
我對卡佛說過的一句話印象深刻:“作家要有為普通的事物,比如為落日或一只舊鞋子感到驚訝的稟賦。”在我看來,文學不是向讀者傳遞些什么,而是觸動讀者身上的什么。特殊的事物往往有更明確和具體的特征、內涵、趣味、意指或意圖等,要不就受到更多巧合因素的擺布,因而遠離了事物的本質性和普遍性——藝術的意象其實天然地親近普通的事物。而“普通的事物”也是我寫作的耕耘之地。
和絕大多數人一樣,我只是一個普通人,至少在四十歲之前,做過的都是再普通不過的工作,經濟收入還拖了人均收入的后腿;從來沒有人用“優秀”來形容過我,也沒有人真正關心我的內心世界。總之,我不是山尖上刻有海拔高度的那塊石碑,而只是山腳下隨處可見的一塊小石子。某種意義上,《生活在低處》這本書中全部的內容,都來自那些在低處生活的饋贈。
(摘自湖南文藝出版社《生活在低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