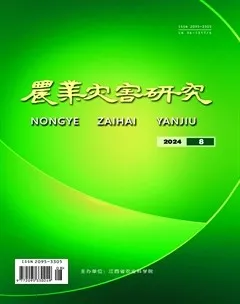基于時序遙感數據的東南丘陵地區撂荒耕地提取









摘 要:近年來,我國耕地撂荒現象十分普遍,已對國家糧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通過使用遙感技術,人們能夠及時獲取撂荒耕地信息,為撂荒耕地治理工作提供數據支撐。東南丘陵地區地形復雜、耕地地塊破碎、混合像元較多,基于傳統方法的撂荒耕地提取精度難以滿足當前要求。基于此,以福建省閩清縣為研究區,基于谷歌地球引擎云平臺(Google Earth Engine,GEE),利用Sentinel-2和Landsat8數據,結合耕地圖斑矢量邊界,構建地塊級長時序歸一化植被指數(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數據集,并采用年際NDVI最大值,結合LandTrendr算法和年內NDVI差值法提取撂荒耕地。利用研究區高分影像和119個野外實地調查樣點數據,驗證了本方法撂荒耕地提取精度為85.71%,表明該方法可以減少混合像元的影響,有效提取東南丘陵地區撂荒耕地信息。
關鍵詞:撂荒耕地;東南丘陵;遙感數據
中圖分類號:S127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2095–3305(2024)08–0-05
耕地撂荒是指土地利用類型為耕地,但由于某些自然或人為原因致使耕地長期停止耕種而荒蕪的狀
態[1]。撂荒造成耕地資源嚴重浪費,不利于耕地流轉,影響耕地資源的統籌規劃,并且出現由于人多地少迫切需要開墾土地以增加耕地保有量,但各種原因使得耕地大面積被閑置棄耕的矛盾[2]。因此,及時、準確地提取撂荒耕地信息,有助于促進土地流轉,提高農用地效益[3]。
與實地調查等傳統方法相比,遙感手段提取的撂荒耕地信息更為高效,且能更好地展現撂荒耕地的時空特征[4]。NDVI是地表植被特征的重要指標,當前對丘陵山區的撂荒耕地提取研究多基于NDVI的不同時間變化[5]。程維芳[6]通過Modis/Terra 2000—2009年的NDVI數據產品,分別針對不同土地利用類型采樣點生成時間序列曲線,研究表明:NDVI時間序列曲線能夠有效定量反演農作物生長過程,從而識別撂荒地。
當前,針對東南丘陵地區的撂荒耕地提取研究較少,且大多數研究是對區內全要素進行解譯和識別[7]。
但是,東南丘陵地形復雜,耕地地塊較為破碎,容易出現錯分、漏分問題。此外,多數撂荒耕地遙感提取基于像元級別分類方法,由于東南丘陵地區混合像元較多,撂荒耕地遙感提取精度普遍不高。撂荒耕地是因為長期沒有耕作導致耕地荒蕪,但在年度變更成果數據中的地類還是屬于耕地,有著明確的耕地地塊邊界,采用耕地地塊矢量邊界數據輔助提取農用地信息,可以有效改善由于混合像元無法準確提取耕地范圍的問題[8]。
以福建省閩清縣為例,針對東南丘陵地區地形復雜、耕地圖斑破碎、混合像元較多且多云雨天氣的特點,基于GEE,使用Sentinel-2和Landsat8數據構建長時序NDVI數據集,結合耕地邊界數據,以無人管理而荒蕪一年及以上的耕地為提取撂荒耕地的判定依據,通過撂荒耕地與長期穩定利用耕地之間地表特征的差異提取撂荒耕地數據,為東南丘陵地區有效處理撂荒耕地問題提供技術支撐[9]。
1 研究區概況和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閩清縣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西北部、閩江中下游地區,地理坐標為118°30′~119°01′E,25°55′~26°33′N,地貌以丘陵、山地為主,根據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結果統計,2020年閩清縣土地總面積為149 435.39 hm2,其中耕地圖斑面積為12 412.42 hm2,占土地總面積的8.3%。耕地以水田為主,面積為11 930.83 hm2,占耕地總面積的96.12%;旱地面積為417.77 hm2,占耕地總面積的3.37%;水澆地面積為63.82 hm2,占耕地總面積的0.51%。閩清縣主要種植作物為水稻、甘薯、花生及蔬菜,且種植結構較為復雜。
1.2 GEE平臺
GEE是基于云端的地理空間信息可視化分析平臺,擁有海量數據集和PB級的數據運算能力。用戶通過在線編輯器,無須構建編譯環境,即可進行影像的裁剪、鑲嵌、融合與各種分析處理。
1.3 數據來源
1.3.1 遙感數據
東南丘陵地區云雨天氣較多,單一的遙感影像數據易受天氣影響而出現數據不連續問題。因此采用
10 m空間分辨率的Sentinel-2影像及30 m空間分辨率的Landsat8影像,協同構建長時間序列遙感影像數據集。Landsat8與Sentinel-2影像具有相近的波段范圍,兩種數據直接融合使用對耕地變化監測的影響較小。此處所采用的遙感影像數據均來自GEE平臺,包
括2016年1月—2021年1月Sentinel-2 L2A級別數據和Landsat8 SR數據,以及2020年4月9日空間分辨率為0.54 m的谷歌影像。圖像預處理過程包括輻射定標、大氣校正、幾何校正、圖像裁剪等。
1.3.2 基礎地理數據
東南丘陵地區耕地分布破碎分散,且面積較小,耕地地塊一般有著相對固定的邊界及單一的權屬。以耕地地塊為基本單元,提取農作物信息能夠有效改善耕地分類精度。耕地矢量邊界數據來自閩清縣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數據庫,共有耕地圖斑22 415個。研究區高分影像結合野外實地調查,采集耕地圖斑內375個樣本點,含長期耕作的穩定利用耕地和撂荒耕地樣本,隨機抽取256個為訓練樣點,119個為驗證點(圖1)。
2 研究方法
技術路線如圖2所示。將Landsat8及Sentinel-2影像進行預處理后計算NDVI值,疊合耕地地塊矢量邊界數據,構建地塊級NDVI數據集。首先,利用年際NDVI最大值法初步提取撂荒耕地;其次,利用年內NDVI差值法進一步提取年際NDVI最大值法無法判斷的撂荒耕地;最后,合并兩者,提取結果并得到研究區撂荒耕地分布情況。
2.1 構建地塊級時序NDVI數據集
第一,利用GEE平臺在線編輯器對預處理后的2016年1月—2021年1月的Sentinel-2 L2A級數據和Landsat8 SR數據構建循環,利用質量評估波段(QA)對所有影像進行云掩膜處理,對去云處理后的影像計算NDVI指數。由于Sentinel-2影像和Landsat8影像的分辨率不同,對Lansat8影像采用三次卷積內插方法重采樣為10 m分辨率。第二,對于每月內的多期NDVI數據,通過mosaic函數進行逐個像元有效最大值或最小值合成,構建逐年逐月最大NDVI和最小NDVI值數據集;再以耕地地塊矢量邊界數據為掩膜,對數據集進行裁剪,剔除非耕地地塊,通過Mean函數對每個地塊進行均值合成,生成各個月份的地塊級時序NDVI數據。
2.2 年際NDVI最大值合成法
年際NDVI最大值合成法通過逐個像元比對每月內各期NDVI值,選取有效NDVI最大值并合成該月NDVI最大值圖像,利用年內各月NDVI最大值圖像,生成該年NDVI最大值圖像,再利用正常耕作耕地和撂荒耕地的年際NDVI最大值顯著差異,提取撂荒耕地。撂荒耕地由于無人耕種而逐漸荒蕪長草,因為自然生長草本的全年NDVI最大值一般比成熟期農作物的NDVI要小,所以耕地撂荒后,其年際NDVI最大值會顯著減小。
如圖3所示,2016—2018年該地塊正常耕作,年內NDVI最大值(約0.6)出現在夏季,年內NDVI最小值(0.1~0.2)出現在冬季。2019年該地塊開始撂荒,2019年全年各月NDVI都較小且變化緩慢,2019年NDVI最大值(約0.22)明顯小于前三年有耕作行為的NDVI最大值(約0.6);2020年該地塊繼續撂荒,但由于植被持續生長,其年內NDVI最大值提高到0.31。
不同作物種類的年NDVI最大值差異較大,部分學者[10-11]使用Sentinel-2數據分析,得到穩定利用耕地的NDVI最大值分別為0.48~0.72或0.3~0.93。通過GEE平臺調用qualityMosaic函數,對研究區地塊級時序NDVI影像進行年最大值合成,結合野外實地調查耕地樣點的NDVI值進行趨勢面分析,得到研究區耕地NDVI最大值的區間為0.46~0.92,綜合趨勢面計算的最小值0.46作為判別研究區耕地是否撂荒的臨界值,并且利用LandTrendr算法對年際NDVI最大值變化進行檢測。LandTrendr算法基本過程是將年際NDVI最大值時序軌跡簡化為一組相連的線段,并對分割后的線段進行線性擬合,提取年際NDVI最大值大幅度減小,且小于0.46,地塊為撂荒耕地。
2.3 年內NDVI差值法
東南丘陵地區部分耕地撂荒后由于氣候條件較好,易生長雜草。特別是耕地撂荒多年后,草木生長旺盛,其NDVI最大值可能高于0.46,導致年際NDVI最大值合成法可能無法有效提取撂荒耕地。雖然雜草生長旺盛的撂荒耕地的NDVI最大值與穩定利用耕地相似,但由于草本自然生長無人工干預,其年內NDVI變化緩慢,而穩定利用耕地的年內NDVI由于人工種植和收割活動會出現有規律的增減現象。撂荒耕地年內NDVI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差值比穩定利用耕地的差值更小,因此利用兩者的年內NDVI變化差值大小可以進一步提取撂荒耕地。
相關研究表明,耕地年內NDVI差值大小與種植類型及耕地撂荒密切相關。統計研究區內已知種植或撂荒情況的256個訓練樣本點的年內NDVI差值區間為0.02~0.22,以0.01為步長,計算不同區間的訓練樣本中撂荒耕地的比例(P):
(1)
式(1)中α、β分別為年內NDVI差值區間的上下限,區間步長為0.01;S荒為在該區間內的撂荒耕地數量;S樣為該區間內耕地樣本總量。圖4顯示,當年內NDVI差值小于0.03時,訓練樣本中的撂荒耕地比例小于20%,其原因為這些耕地大部分種植果樹、樹苗等常綠植被,使得年內NDVI差值較小。這些耕地被認為是“非糧化”利用的耕地,不屬于撂荒耕地。當年內NDVI差值在0.04~0.10時,撂荒耕地比例顯著增加,達到80%以上;當年內NDVI差值大于0.10時,撂荒耕地比例顯著減少(小于20%),這些耕地絕大部分種植農作物,年內NDVI變化呈現明顯的增減現象。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確定研究區撂荒耕地年內NDVI差值區間為(0.04,0.10)。
3 結果分析
3.1 撂荒耕地提取結果的驗證
通過上述方法提取閩清縣2016—2020年的撂荒耕地,再利用高分影像結合野外實地調查,共計驗證119個樣點地塊,發現其中102個樣點結果正確,提取精度為85.71%。這表明該提取方法優于傳統遙感分類提取方法,可以有效提取撂荒耕地信息。
如表1所示,2016—2020年閩清縣撂荒耕地面積分別為4 678.25、4 327.02、4 457.09、4 279.78、4 644.56 hm2,
分別占全縣耕地總面積的37.69%、34.86%、35.91%、34.48%
及37.42%。2016—2020年各年份拋荒率在35%左右,耕地撂荒現象較為嚴重。根據閩清縣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結果,2019年未耕種耕地面積為4 502.03 hm2,與本方法提取的2019年撂荒耕地面積4 279.78 hm2的數值十分接近,證明了本撂荒耕地提取方法的可靠性。
3.2 撂荒耕地的時空分布特征
通過疊加2016—2020年份撂荒耕地提取結果,得到撂荒持續時間分別為1~5年的地塊分布,共計15 757個圖斑。由表2可知,研究區耕地持續撂荒1~5年的面積分別為1 394.31、1 894.23、1 745.44、1 774.48、773.94 hm2,分別占研究區耕地總面積的11.23%、15.26%、14.06%、14.29%及6.23%。
從閩清縣耕地撂荒持續時間分布圖(圖5)可以看出,撂荒地塊多分布在閩清縣東南部、東北部等海拔較高的、耕作不便的丘陵地帶,這些地塊面積相對較大且比較集中,其余地區分布則較為零散。1~2年撂荒耕地多分布在農村居民地附近,其原因包括農作物經濟效益較低導致農戶耕作意愿下降、農村人口外流導致勞動力不足等,使得農戶只耕作部分耕地以實現口糧自足目的,而選擇性或間斷性地撂荒部分耕地[12]。持續撂荒3年以上耕地主要分布在距居民區的較遠地帶,這類耕地位置偏遠、耕作不便,農戶主動復墾該類撂荒耕地的可能性較小。
3.3 撂荒耕地的核密度分析
對2017—2020年撂荒耕地提取結果進行核密度分析,如圖6所示。從整體看,閩清縣撂荒耕地分布廣泛且散亂,各年份的聚集程度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撂荒地高聚集度的區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區的東南和東北區域。云龍鄉和三溪鄉在2017—2020年都存在明顯的高聚集,下祝鄉除2019年也存在明顯的高聚集,這3個區域的地形多為山地,農用器械使用不便,加上農村常住人口較少,勞動力的不足,致使耕地常年撂荒。坂東鎮和塔莊鎮在2017、2020年存在明顯的高聚集,這2個地區雖然有較多的常住人口,但其城鎮化水平相對較高,有相對較多的工作崗位,而農業生產過低的收益使得農戶放棄耕作轉而從事其他工作,導致耕地撂荒。
4 結束語
針對東南丘陵地區耕地破碎、混合像元較多、種植結構復雜等導致撂荒耕地遙感提取精度較低的問題,以耕地邊界信息結合NDVI,通過最大值合成法結合LandTrendr算法和年內差值方法,能夠有效提取東南丘陵地區的撂荒耕地。研究結果可以為東南丘陵地區撂荒耕地信息獲取提供有效方法。以Sentinel-2影像及Landsat8影像協同構建時序遙感數據集,解決了東南丘陵多云雨天氣導致的單一遙感數據源有效數據不足的問題。
本研究采用年際NDVI最大值合成法和年內NDVI
差值法提取撂荒耕地,可以有效解決不同作物物候期不一致的問題。由于數據源的局限性,Sentinel-2和Landsat8時間分辨率不夠高,未必能夠獲取作物收獲后至下一輪種植前的時點影像,年內差值法可能無法識別出這些輪耕地塊。此外,研究區內種植情況復雜多變,種植作物類型完全受農戶控制,部分耕地轉為種植油茶樹、果樹等常綠植物,年內NDVI差值小于種糧耕地,而這些“非糧化”耕地有可能被誤判為撂荒耕地。因此,在實際中需要結合物候特征進一步的分類提取。
參考文獻
[1] 陳欣怡,鄭國全.國內外耕地撂荒研究進展[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8,28(S2):37-41.
[2] 陳航,譚永忠,鄧欣雨,等.撂荒耕地信息獲取方法研究進展與展望[J].農業工程學報,2020,36(23):258-268.
[3] 李升發,李秀彬.耕地撂荒研究進展與展望[J].地理學報, 2016,71(3):370-389.
[4] 陳航,譚永忠,鄧欣雨,等.撂荒耕地信息獲取方法研究進展與展望[J].農業工程學報,2020,36(23):258-268.
[5] 李加林,劉闖.基于MODIS的杭州灣南岸農業生態系統NDVI季節變化特征研究[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5 (3):30-34.
[6] 程維芳,周藝,王世新,等.基于多光譜遙感的撂荒地識別方法研究[J].光譜學與光譜分析,2011,31(6):1615-1620.
[7] 王佑漢.基于遙感的四川省撂荒耕地多尺度空間格局及機制研究[D].成都:成都理工大學,2020.
[8] Qiu B, Luo Y, Tang Z, et al. Winter wheat mapping combining variations before and after estimated heading dates [J]. 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 Remote Sensing, 2017, 123(1): 35-46.
[9] 羅婷婷,鄒學榮.撂荒,棄耕,退耕還林與休耕轉換機制謀劃[J].西部論壇,2015,25(2):7.
[10] 王利軍,郭燕,賀佳,等.基于決策樹和SVM的Sentinel-2A影像作物提取方法[J].農業機械學報,2018,49(9):146-153.
[11] 韓圣其.撂荒地遙感監測與空間分布規律研究[D].北京:北京林業大學,2019.
[12] 程先同.農村勞動力結構對耕地撂荒的影響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