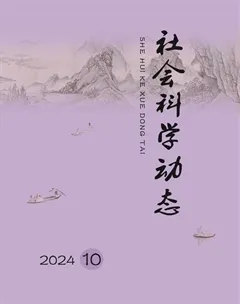論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的癥候閱讀
摘要:對于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癥候閱讀的研究,目前學界多側重于癥候閱讀方法論本身的機制研究或側重于阿爾都塞解讀《資本論》的多元結構研究,對方法與文本的結合關注較少。阿爾都塞通過問題域的轉變找出古典經濟學的空白,進一步確立了《資本論》對象的特殊性。然而,利用結構主義方法論來閱讀《資本論》還有深究的空間。《資本論》是在以物質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社會存在中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重要著作,是結構性主體和實踐性主體雙重問題域下的具體歷史的統一。
關鍵詞:《資本論》;馬克思;癥候閱讀;阿爾都塞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國外新黑格爾式馬克思主義批判研究”(21BZX031)
中圖分類號:B565.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4)10-0014-06
《資本論》是馬克思思想體系中的重要著作,對其進行多維度的理論闡釋是學界研究的重點之一。或從具體科學角度來研究《資本論》,或從哲學角度來研究《資本論》,其中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兼顧科學和哲學的統一,立足科學認識論的角度開創了對《資本論》的哲學閱讀范式。學界關于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的解讀研究主要是以《讀〈資本論〉》為依托,或側重于對阿爾都塞解讀《資本論》時所使用的癥候閱讀法本身進行研究,包括理論的來源、闡釋和應用;或側重于討論阿爾都塞對《資本論》解讀的多元結構或經驗結構。由是觀之,當前的研究要么關注方法論本身,要么強調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認識論。與上述方法不同,本文將癥候閱讀與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的認識發生過程結合論述,以批判性反思的態度考察癥候閱讀,展現《資本論》的真正價值。
一、出場:阿爾都塞對柵欄閱讀的批判與癥候閱讀的呈現
對《資本論》的閱讀從未停止,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所主張地閱讀《資本論》尤為重要。在阿爾都塞看來,捍衛馬克思的科學性應當回到《資本論》中,從閱讀《資本論》著手以應對人道主義意識形態危機。阿爾都塞承擔了這個使命,在《讀〈資本論〉》開篇,前提性地澄清了“閱讀”這一認識行為本身所具有的原罪性。任何人在實際閱讀過程中都會因時代背景和生活閱歷而預先代入主觀觀念,站在自身立場上加之“理論負載”之原罪,更進一步說,無辜的閱讀還表現為從文本的部分直接讀出文本的“絕對真理”即本質的閱讀。(1)根據阿爾都塞的語境,弗洛伊德、馬克思和斯賓諾莎三個人對突破無辜的閱讀的界限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指認,表面的聽、說隱含著人們的真實欲望;其次是斯賓諾莎通過想像和真實之間的距離來說明文本和現實歷史之間的距離;還有馬克思,“建立了歷史理論以及意識形態和科學之間的歷史差別的哲學”(2),完成了理論變革。由此,阿爾都塞得出結論,閱讀之前就確定了答案且能夠不受干擾讀出本質的閱讀是意識形態指導下的閱讀,同科學認識論是相對的,一言以蔽之,無辜的閱讀是不存在的,閱讀是有罪的。
“如果說不存在無罪的閱讀,那么這是因為每一種閱讀就其教益和規則而言只是反映了真正負有罪責的閱讀”(3)。既如此,什么才是有罪的閱讀呢?或者說什么才是阿爾都塞所要求的閱讀呢?阿爾都塞將討論點立足于哲學閱讀上面,致力于探尋一種新的閱讀理論以達到對《資本論》解讀的真正目的。他對《資本論》哲學解讀中體現的雙重閱讀原則即“柵欄”和“癥候”進行分析,指出癥候閱讀正是在與柵欄閱讀進行比較的結果上體現其方法論視域的。
所謂柵欄閱讀實際上就是一種認識的主體式映現閱讀。“柵欄”即為理論先見,通過以馬克思本人的理解為尺度來衡量古典經濟學家(例如斯密)文本中的功績和缺陷,閱讀得到的結果為兩者之間一致性與否的記錄。顯然,這種閱讀是極為明確的,以讀者的視域為標準來總結和補充文本的理論空白,抹殺了作者的無意識以及文本理論的歷史性。在這樣的情況下,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家之間并沒有什么本質區別,只是由于看的能力的高低所造成的理論結果的不同,因為任何人都會有視而不見的時候,馬克思并不比斯密高明,只是擁有更完美的目光神力,“馬克思借以思考他在理論上始終與斯密不同的那種歷史距離消失了”(4),閱讀的差別僅在于量的不同。
阿爾都塞認為柵欄閱讀的根本缺陷就在于看見與疏忽相統一。在《資本論》中,古典經濟學家混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以及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關系等失誤,都被馬克思通過自己的視域呈現出來。這樣一來,任何認識過程中出現的概念體系的空缺都可以歸結為看的行為:如果說看得不全整帶來的是疏忽,那么擁有敏銳的目光就能獲得問題框架中的全部認識。然而就文本作者來說,同時存在著看到的意識和看不到的無意識,看不到不是因為視力好壞而看不到,恰恰是因為看到了卻“視而不見”,只能停留在表面文本,對存在和空缺進行簡單填補,看不到問題的反思和解決。
進而言之,透過此種直接“看”的線性認識論邏輯,就能發掘背后的實質其實是經驗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阿爾都塞看來,打開書馬上就可以看到的回顧式閱讀表現為認識自映的神話,類似于一種閱讀《圣經》時的態度,所遵循的是“從根本上把全部認識工作歸結為看的簡單關系再認識:把認識對象的全部本質歸結為客觀存在的簡單條件”(5)。按照這種閱讀只能判斷出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的差別在于“辯證的”和“形而上學的”純粹形式上的差別,從而不可避免地陷入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對象的連續性假設中。總之,表層結構上的柵欄閱讀無法發現文本深層的內容,只體現為同一問題框架內的簡單差別。
阿爾都塞提醒我們,在馬克思那里還有另外一種閱讀的形式即癥候閱讀。相比于柵欄閱讀,癥候閱讀改變了看的方式。它力圖從看得到的東西中去揭示隱藏著的看不到的東西,把主體看到和看不到之間的視力對比轉變成看到與看不到之間的結構性問題。
癥候閱讀借助精神分析的無意識理論來考察文本的深層結構。阿爾都塞強調,癥候閱讀不止步于發現前者的遺漏之處,更在于超越已有的東西,我們在閱讀時,要想從整體上理解文章的未盡之言,就要將表層語言的連續性向著不同方向撕裂開來,抓住必然的空白并對其進行研究,那些空白就是“癥候”。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論中詳細探討了“癥候”的含義,“我承認我自己向來很重視對于神經病癥候的解釋,因為這些癥候視為占據病人心內的‘無意識觀念’的表示。”(6)他指出,病患所表現出來的狀況只是冰山一角,內心的欲望由于被壓抑而無法正常得到釋放,由此就變成了病理的“癥候”,精神分析法的目的就是消除“癥候”。拉康在淡化弗洛伊德主觀臆測的基礎上,結合語義學使得“癥候”的運用由生物學領域擴展至理論領域,提出了“無意識具有語言的結構”的論斷。按照拉康的意思,語言處在無意識發生之前,并創造了無意識。同樣,主體也并非與生俱來,只有經過語言在不同階段的發展刻畫才能變成獨立的主體。與弗洛伊德不同,拉康更加強調了符號界比之想像界的優先性,自我不再處于中心位置而隸屬一定的秩序。可見,阿爾都塞是在吸納二者理論的基礎上再對深層結構指向的理論進行整合與改造,提出并實踐了他的“癥候閱讀法”。
看的方式改變和無意識的挖掘必須通過總問題的轉換來實現。癥候閱讀法通過捕捉既定文本中的“癥候”來把握作者理論的深層認知框架,蘊含著觀察和提問方式的變化,故而其實質是總問題的閱讀。可以說,阿爾都塞將總問題看作是作者進行思考和寫作的一種特定生產方式,它不僅規定了文本的內在邏輯體系,而且決定了讀者的認識內容,不同的總問題相應地派生出各自理論的邏輯以及闡釋體系,規定著理論的生產過程,起到了一種“權利話語”的作用。當運用癥候閱讀法進行認識的建構時,開放著的結構視域會形成新的思想問題和答案,以區別于經驗主義的反映論認識,所以要想理解文本的真實思想關鍵就在于抓住總問題,言下之意,只要發現了總問題,文本中的那些空白和沉默就能夠接受光的普照。“所謂癥候閱讀法就是在同一運動中,把所讀的文章本身中被掩蓋的東西揭示出來并且使之與另一篇文章發生聯系,而這另一篇文章作為必然的不出現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7)癥候閱讀的對象是兩個關聯文本,其中第二個文本在統一運動中作為第一個文本的必然缺場存在,但是第二個文本不是現實的文本,只是第一個顯性文本中隱含著的無意識內容并且通過第一個文本表現出來,這里所說的缺場就是指第二個文本沒有被明確呈現出來但又必然從第一個文本的空白中找到。
二、圖式: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癥候閱讀的論證
(一)轉換《資本論》至新的問題域
癥候閱讀目的就在于從文本之外的空白進入,產生出一個全新的問題域。這個問題域是指因現實難題的存在而提出的那個無意識的框架性的東西,它規定并限定著人們所能夠提出的問題以及提出方式,決定著對那些問題的回答,因而問題域反映的是思想家提出問題時所面臨的時代難題和所使用的概念體系,不僅折射了思想家身處其中的現實形式,同時折射了思想家身處其中的理論形式。
古典經濟學家處于經驗主義意識形態問題域中,決定了他們必然會“把被理解為現實對象的現實組成部分的認識納入這一現實對象的現實結構”(8),阿爾都塞將這種認識過程定義為一種經驗抽象的活動。以“淘金”為例,類比經驗認識的過程,就是指認識對現實對象本質和非本質部分的區分,“現實的本質作為現實本質存在于包含這一本質的現實之中”。(9)礦石和金子是不同的,但它們處于同一礦脈中,就是說經驗主義認識論把認識對象等同于現實對象,所得出的認識不過是一種幻象。
與此相反,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摒棄了這種混同,強調認識對象和現實對象的異質性,現實對象始終獨立存在,認識對象是作為思維具體通過思維自身生產出來的。馬克思的認識是結構性的生產過程,認識作用的不是現實對象,而是它自己的對象,這個對象在特定的概念順序中被生產出來,是理論實踐的產物,也就是在理論實踐的過程中,馬克思建立了新的問題域,走出了意識形態封閉的圓圈。為了更好說明問題域的轉變過程,阿爾都塞以《資本論·工資篇》為例。古典經濟學從“勞動的價值”出發,得出了“勞動(……)的價值等于維持和再生產勞動(……)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的結論,括號內的省略號是阿爾都塞設置的,他認為這是馬克思根據古典經濟學本身所指出的其應該表達但卻沒有在行文中說出來的內容。去掉括號還原句子,就會發現問題:什么是維持勞動?勞動怎么去再生產勞動?顯然這句話因同義反復而毫無意義。如果更改一下,把后面的勞動換成勞動(者),回答就變成了“勞動的價值等于維持和再生產勞動(者)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無獨有偶,新的矛盾又出現了,勞動和勞動者概念所表達的內容不一致,存在邏輯缺漏,既然現有詞匯無力表述句子的含義,那么必須引入新的概念。確切地講,再生產的并非是勞動本身而是勞動力,勞動其實是貯藏在勞動者體內勞動能力職能的物質體現,只要將勞動的省略處補足,句子就有了意義,即“勞動(力)的價值等于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現在我們就可以說馬克思創造了“勞動力”這樣一個新的概念。新的概念的表述,不僅生產出這個新概念的重新回答,也生產出這個回答所對應的那個迄今為止還沒有提出的新的總問題。于是,經過上述的復雜過程,馬克思實現了“勞動的價值是什么”向“勞動力的價值是什么”的轉變,馬克思同古典經濟學之間的“斷裂”就顯現出來了。
(二)發現古典經濟學的空白
問題域的場所變換必然會導致空白的凸顯,馬克思抓住了古典經濟學的總問題,順著這樣一種邏輯自然就會發現舊的視域中的“內在黑暗”。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空白不是文本中實實在在的缺漏,不是顯現出來的“沒有”,而是有中之“無”,故而要想確立空白之下的結果即《資本論》的對象,就必須先對古典經濟學的對象進行考察。
古典經濟學以同質性經濟事實為研究對象。“政治經濟學首先包含著一定領域內的‘經濟的’事實和現象,這一領域具有同質領域的屬性……是可以直接看到并觀察到的。”(10)首先,這個領域內的具體經濟事實是既定存在,理解它們無需批判理論作為前提;其次,這些經濟事實具有同質性,通過比較就能量化蘊含的價值大小,這一點是古典經濟學最基本的原則。在阿爾都塞看來,既定存在的對象具有虛幻性,古典經濟學只關注價值量而忽視了對價值形式的分析,相反,馬克思所關心的是既定事實背后的特定概念,“沒有數量的規定”卻能夠作為那些可以量化的概念的標準,所以馬克思要建立新的對象的概念。
阿爾都塞認為對象分析概念就是總問題變異的結果,《資本論》正是從一系列與新的對象相關聯的基本概念出發才能夠指認新的對象的確立,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剩余價值,它關乎《資本論》對象的結構。阿爾都塞提到了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言中敘述的拉瓦錫發現化學元素氧氣的例子,他認為這與馬克思發現剩余價值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氧氣發現以前,大多數化學現象都可以歸結為物質吸收或釋放燃素的過程,這種燃素說束縛了普利斯特列和舍勒,他們雖然已經析出了能夠使化學理論發生變革的氧氣,但是卻沒有獲得認識上的碩果,直到拉瓦錫通過實驗確定了空氣中促進燃燒的氣體物質是一種元素,提出了新的燃燒理論,才推翻了統治近百年的燃素說。同樣,以前的古典經濟學家其實已經確定了剩余價值的存在,但是他們“總是在利潤、地租和利息的形式上分析‘剩余價值’因而剩余價值總沒有以它自己的名稱而是以別的名稱來稱呼”(11)。馬克思從被忽視的“這部分價值”中發現了剩余價值理論,突破了古典經濟學家面臨的詰難,馬克思比之斯密和李嘉圖的關系正如同拉瓦錫比之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關系,“的確是他發現了剩余價值,而他的先驅者僅僅是析出了剩余價值”(12)。古典經濟學家固守在尋求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問題領域內,注定無法觸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本質,剩余價值的一般形式就變成了古典經濟學的空白。
(三)重新確立《資本論》的結構性對象
既然找到了空白,明確了古典經濟學的對象,就意味著具有這種特性的經濟事實所構成的理論只能用于解決具體的問題,完全服從于經驗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此而言,馬克思立于不同問題域下所面對的對象必定不同,新的認識對象的確立不僅影響著理論加工的過程,還會帶來現實對象認識的不斷深化。
阿爾都塞指出,馬克思在拋棄既定經濟現象所構成的同質領域這樣一種實證觀念的同時,也清洗了背后的人本學基礎。首先從消費領域來看,其中的生產性消費不管是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都是為了滿足生產過程中的各種消耗,主要來自生產本身,據此馬克思區分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以及兩個部類,這是古典經濟學含混不清的東西。至于消費領域包括的一定比例的滿足人的“需要”的個人消費,阿爾都塞隨即表明這部分需要只有真正作為經濟的需要即在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才能夠成立,這就意味著關鍵不在于人而在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結構規定。接下來是分配領域,包括收入的分配和生產過程中使用價值的分配。收入的分配被歸結為生產關系,而使用價值的分配在第一部類的產品中表現為壟斷資本家之間的劃分,在第二部類的產品中由個人收入所決定,因而分配的兩個方面實質上體現的是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分配。綜上,基于消費和分配領域人本學的清除必然會回到經濟的真正規定——生產。生產領域由勞動過程和生產關系兩個要素組成。就勞動過程來說,它是生產的物質條件,具有兩個特點:一是以物質條件為前提,二是勞動資料的支配作用。正是基于上述特點馬克思才得以創造出生產方式這個歷史的概念,確立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生產過程中的物質條件表現出人與自然的關系,社會條件就是生產關系,這種關系在馬克思那里“是生產過程的當事人和生產過程的物質條件的特殊的‘結合’”(13)。據此阿爾都塞得出結論,社會的上層建筑都包含在生產關系的結構中,生產關系的概念要通過社會整體的概念規定才能完成,而要建立自身的概念,就必須確立生產關系作為社會整體結構中的一個區域性結構,這個結構決定其領域內的要素,決定生產當事人的地位和職能,最終取代“現實的人”成為真正的“主體”。
行文至此,阿爾都塞關于《資本論》對象問題的獨特性得以明晰。第一,《資本論》的對象是一個復雜結構形成的認識對象。這個結構取代了以經濟事實為對象所構成的同質性平面空間,是“在決定經濟現象的‘生產關系’的支配下思考經濟現象的結構”(14)。第二,總結構劃分并規定各個區域性結構,占支配地位的區域性結構又對其他從屬結構起作用。馬克思巨大的理論革命就是立足于異質性的社會整體結構,在生產關系的區域性結構中通過剩余價值這個核心概念來規定經濟現象。第三,結構的因果性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線性因果性和表現因果性。結構的作用不是外在于經濟現象的本質體現,而是存在于它的要素當中。
三、反思:阿爾都塞論證的癥結與《資本論》的雙重問題域
在阿爾都塞那里,《資本論》同所謂的人道主義之間的認識論界限已經明晰,但他主張在社會歷史的整體結構中構造出認識對象,強調生產關系這一區域性結構的支配作用,顯然并未真正理解《資本論》唯物史觀的內在意蘊。事實上,《資本論》直面感性對象性的活動,考察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系,關注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體現的是歷史主體的具體性。
(一)對阿爾都塞《資本論》癥候閱讀的批判
阿爾都塞運用癥候閱讀這一理論工具開創了解讀《資本論》的結構主義新思路,傳達了思想深處的無意識話語,然而其對《資本論》的認識發生過程還存在明顯的理論缺陷,并未揭示《資本論》學說的本質。
第一,囿于純粹理論的解蔽陷入循環論證的漩渦。在阿爾都塞那里,只有把經濟事實上升到概念的層面,在思維中再現現實社會關系,才能夠鑒別馬克思的對象同其他對象的區別。根據這一立場,阿爾都塞指出,研究《資本論》的對象首先要突破經驗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然后才能在理論實踐的過程中把握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換言之,阿爾都塞預設了一定的理論前提,強調認識對象本身的獨立性,完全沉浸于共時性的結構分析,始終沒有理解促使總問題變化的真正源泉歸根結底是對現實的反映,按照這樣的邏輯循環展開對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明顯懸置了作為現實對象的社會存在,只能在概念層面上定義《資本論》的對象。不同于這種理論實踐,《資本論》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應用于現實社會的體現,它作為理論成果所具有的革命意義首先就在于它是內在地建立一種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有力批判,而不是一種外在的抽象性反思,馬克思將哲學理論與現實經濟社會創造性地結合起來,脫離了思辨的范圍,使得《資本論》成為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的批判科學,挖掘階級立場的矛盾,洞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社會根源。(15)
第二,結構大于主體的視角消解了人的主體性。阿爾都塞雖不承認自己是一個結構主義者,但在他的理論發展中處處透露出結構主義的痕跡。從阿爾都塞的論述來看,青年馬克思受到意識形態總問題的束縛,直接從經濟存在的表相中讀出了人的異化本質,但到了《資本論》中,馬克思轉向了現實歷史,建構了新的理論實踐,在肯定成熟時期思想科學性的同時,阿爾都塞也把《資本論》同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區分開來,強調一種科學和意識形態的絕對對立。伴隨著總問題基調的變換,阿爾都塞指出,立于無意識之上的癥候閱讀過程實則是一個無主體的客觀過程,只有生產關系的結構才是真正的主體,“在這種變化中,主體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它自認為起到的作用而是過程的機制賦予它的作用”(16),總問題發生作用的行為與現實存在的主體無關,歸根結底是結構在發生作用,然而這樣一種無主體理論同馬克思的理論是涇渭分明的,《資本論》從資本視角以生產力、生產關系等概念代表了對人的本質的闡述,主體的向度一直存在于馬克思思想當中。
(二)《資本論》是結構性和實踐性的具體歷史的統一
阿爾都塞對《資本論》進行癥候閱讀的過程就是他自身結構主義認識論的發生過程,即馬克思經歷了由意識形態到科學的斷裂后所創建的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行的歷史理論過程,但阿爾都塞對社會現實本體和歷史主體的忽略,背離了《資本論》唯物史觀的基本視域。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之稱的《資本論》,其方法離不開辯證性的規定,其對象是結構性主體和實踐性主體的結合。
首先,《資本論》以現實的人的感性活動作為本體。《資本論》的結構分析固然體現其客觀規律,但理論建構的歷史終究不能代替人類實踐的歷史。從認識論層面考察《資本論》表現為一種理論邏輯的展開過程,但是,《資本論》始終與工人運動緊密相連,考察社會現狀,表明工人運動由自發走向自覺的歷史發展,資本作為一種歷史性產物,要透過物質載體理解背后的社會關系。“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17),《資本論》所描繪的是資本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表現為整體性的歷史活動即社會通過自我否定的矛盾運動逐步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進程,馬克思在強調商品、貨幣等范疇的同時也聚焦于背后的社會歷史內容,商品到貨幣再到資本的經濟學表現形式是在社會的內在矛盾中推衍出來的,歷史性就體現在這些物質載體背后的社會形式之中。生產關系的結構與人類主體的交互活動相關,隨著特定歷史時期的更替,新的生產方式也相應地出現,只有依托社會存在才能對價值形式做出分析,超越社會事實結果的簡單描述,在物質生產方式的基石處研究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理論。(18)概言之,實踐主體的活動構建社會存在的過程恰恰指明了《資本論》的方法不僅是結構的,而且是歷史的。《資本論》在邏輯敘述時總是會滲透著歷史性的分析,歷史的建構是邏輯開始的起點,馬克思清楚地認識到當勞動力成為商品時,有關工廠制度的問題就會隨之作為歷史前提被提出。因此,《資本論》是以生活方式為前理解的實踐解釋學,始終建立在世界體系的完整感和關聯性之上,體現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結構,這個客觀結構是由社會的形式所建構出來的。歷史并非是邏輯預設下機械的發展,也不是想象主體的抽象思辨,“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9),歷史性始終奠基在具體現實之上。
其次,歷史唯物主義的對象是結構主體性和實踐主體性的統一。馬克思在建構資本邏輯的同時,更強調主體歷史的具體性,馬克思的問題域具有結構性和實踐性的雙重維度。《資本論》的結構性主體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形成的生產關系,經濟、政治和法律以及意識形態組成社會基本結構,貫穿著資本的自我矛盾運動,但是“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20),《資本論》更深層次的是要考察現實的人在實踐領域內所進行的對象性活動。在馬克思看來,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主體的社會實踐本身就包含著理論的存在,認識的不斷深化恰恰就是實踐環節推進的過程,主體在進行這些活動的時候,只有歸于實踐的根基才能剖析社會生活的本質,因為“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21)。機器發展和社會分工使得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人類勞動逐步擺脫外在形式,勞動產品變為商品,為了更好地進行交換,貨幣被充當為一般等價物,商品似乎都要以貨幣來表現自己的價值,但這其實是一種假象,商品中內涵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才是其自身價值的真正體現,這種交換價值的實現帶來的是資本“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22),只有回到實踐主體自我革命的現實道路,才能應對私有制條件下發生的勞動異化,解決社會對抗。就《資本論》而言,無論是論述資本主義經濟進程還是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其最終都指向的是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這個崇高目標,實踐主體的總體性活動既體現著革命性的政治實踐,又體現著革命性的生產實踐。(23)因此,探求《資本論》從勞動價值的表層結構到勞動增值的深層結構,需要抓住蘊含于其中不斷生成的實踐主體。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作為“普照之光”,不論是商品交換的形式化結構還是剩余價值形態的變化都意味著主體必須被納入資本邏輯;另一方面,從根本上說,關注人的本質是擺脫拜物教統治的必然要求,社會變革終歸要訴諸主體及其能動性。
注釋:
(1) 張一兵:《析阿爾都塞的“癥候閱讀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2)(3)(4)(5)(7)(8)(9)(10)(11)(12)(13)(14)(16) [法]路易·阿爾都塞:《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5、23、7、7、16、26、31、146、78、138、159、152、16頁。
(6) [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02—203頁。
(15) 王慶豐、劉也:《〈資本論〉的政治實踐——論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的激進政治解讀》,《社會科學輯刊》2022年第1期。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頁。
(18) 俞吾金:《馬克思的實踐釋義學初探》,《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頁。
(20)(2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501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頁。
(23) 袁蓓:《馬克思的主體理論變革及當代審視——重思〈資本論〉中的“主體”問題》,《哲學動態》2021年第2期。
作者簡介:代利剛,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江蘇無錫,214122;葉帆,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無錫,214122。
(責任編輯 木 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