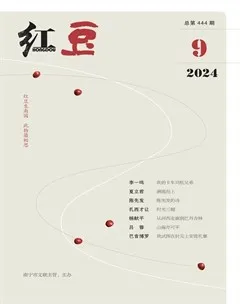老林
1
那天早晨,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十分悲傷地說,她父親走了。臨終,她父親叮囑她一定通知到我,希望我能去送他最后一程。
我一怔,一個身影立馬在腦海中浮出:身量不高,穿一身深色的中山裝,頭發濃密且黑,總是梳得一絲不茍,操一口福建味普通話,說話有板有眼。一九七六年,當時我二十二歲,他已年過不惑,是中國青年出版社一編室副主任林君雄,我們稱呼他老林。一天午飯后,他把我叫到辦公桌前,很認真地問:“你愿意來出版社當編輯嗎?”當編輯?這提議來得太突然了,像是幸運之神從天而降,讓我有點兒猝不及防。見我一臉愕然,老林猜到我在想什么,笑了笑,用手捋捋整潔的發型,語氣中充滿鼓勵:“你行,只要努力,會成為一名好編輯。”
一九六三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姚雪垠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書出版后,作者寄了一套給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很是稱贊,給了作者極大的鼓舞。為排除各種噪聲的干擾,創造更好的寫作環境,姚雪垠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再次寫信給偉人,很快得到毛主席親筆批示,同意作者繼續完成《李自成》第二至第五卷的創作。因為要出版《李自成》第二至第五卷,停業十年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全面恢復了業務。一編室人手短缺,便從工廠和北京大學中文系抽調了一些文學青年和工農兵學員幫忙。一九七六年初,我退伍回到北京第一機床廠,經廠團委推薦,奉命參與了中國青年出版社兩本書的編輯工作,得到老林賞識。不承想,這竟成了改變我的命運。
可是,我調動的過程并不順利,因為車間主任不放。
同年十月,“四人幫”被粉碎,老林認為事情會有轉機,又一次騎著自行車跑到位于東郊的新鑄工車間,請求主任高抬貴手,沒想到小老頭兒仍不為所動。老林向我描述當時的情景:“小杜到出版社工作,也是為‘四化’作貢獻嘛!”或許是被找煩了,車間主任眼皮也不抬,一揮手,說:“少來,凈想著進高樓、坐辦公室,我問你,翻砂的活兒誰干?”
老林儒雅,但并不意味著他沒有性子。我曾隨他到南方某省出差,親眼見證過他的脾氣。中國青年出版社是團中央直屬的出版社,到各省搞調研或組稿,對口的接待單位一般是團省委。那天,我和老林下了飛機,輾轉找到團省委,辦公室的一個女干部看了介紹信,不冷不熱地說了一句:“你們坐在這兒等一下。”轉身就出去了。老林開始還耐心等待,過了半個小時仍不見人來,明顯焦躁起來。他站起身,在房間里來回踱步,又不時看看手表,嗔怒道:“怎么搞的?”又過了二十來分鐘,火山終于突破了噴發的臨界點,他從沙發上一把拎起皮包,臉色鐵青地招呼我:“小杜,走,我們走!”一拉門,昂著頭,甩著胳膊,沖進樓道里,狀態很像一頭被激怒的公牛。樓道很長,進出辦公室的人見到老林怒氣沖沖的樣子,不明所以,不便問,也不敢攔,還是那個接待我們的女干部從后面跑上來賠禮道:“不好意思,因為一點兒事耽擱啦,對不起。”老林不理她,只顧往前走。女干部緊跑兩步,攔住去路。老林停下腳步,憤然道:“五十分鐘了,不理不睬,太過分了吧?我們是來談工作的,不是來受冷落的!”那個女干部自知闖了禍,忙不迭賠著笑臉說:“老師,是我工作失誤,我向您賠禮道歉。宣傳部部長請您到他的辦公室,商量一下工作如何對接。”
和老林共事十年,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見他發火。
調動未成,廠里把我叫回。本來去之前我在車間搞宣傳,小老頭兒沖天一怒,我無辜躺槍,被“發配”到班組當了翻砂工。那是我一生中最迷茫的時光,如同一片枯葉,心里落滿惆悵。同年進廠的師兄弟早就出徒,一個個手藝杠杠的。我當了好幾年兵,技術上完全是一個“小白”,修出的鑄件慘不忍睹,必須由師兄弟返工。人們看我的目光,有同情,有理解,也有嘲弄和輕蔑。一道道目光織成一張網,我就是一條被網住的魚,每天都在痛苦地掙扎。日子像一塊沉重的磨盤,在我的精神和肉體上碾過。萬幸,老林做事很有韌性,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打來電話,問問我的現狀,讓我安心工作,說社里從未放棄調我的想法,正努力做通廠里的工作。于是,我內心重新燃起了希望。
2
一九七八年,在老林的努力下,我終于成了中國青年出版社最年輕的編輯。
報到時正是人間四月天。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辦公地點是一座清朝時的王府,幾座四合院相互勾連,布局規整,端方有序,綠樹掩映,曲徑通幽。院子里鮮花盛開,有櫻花、玉蘭,印象最深的是一片翠竹,生意盎然。我的心境和美麗的春天一樣,所有的惆悵都如云煙一般散去,灑滿生命天空的凈是美好的光影。我回來了,以前我只是圣殿的一名香客,從今以后,我也是這座院子的主人之一了。命運真是一個魔方,不斷變幻,呈現出它的無窮魅力。
我很快進入角色,提出的選題一個個被通過。端詳著發稿單上責編一欄“杜衛東”的簽名,我覺得,這才是命運該有的樣子。生活如同兌了奶的咖啡,芳香四溢。正當我以為整個世界都在為我喝彩時,我突然遭遇一記“迎頭棒喝”。一天上班,我走進編輯室,氣氛有些詭異,同事們沒有像往常一樣和我打招呼,而是沉默不語,埋頭看稿。我坐下,桌面正中擺著一個文件夾,編輯室用它傳閱重要的文件和通知,看后,每個人要在自己的名字上畫圈。房間里的氣氛暗示我,今天傳閱的內容非同一般。是什么?任免名單,處分決定?有同事在偷瞄我,無疑,和我有關。我長噓一口氣,定定神,打開文件夾——是老林的一個批示,并附有我寫的一份審讀報告,上面用紅筆一一標明了好幾處錯別字和語法錯誤。他的批示措辭嚴厲,說:“不論是水平低還是工作疏漏,都不能成為被原諒的理由。編輯是很嚴肅、很高尚的職業,要對作品進行整理、加工和修改,通過編輯的書籍傳承優秀文化。這樣的審讀報告,何以匹配編輯稱號?何以履行編輯職責?”
我蒙了,大腦被按下暫停鍵,一片空白。前幾天,老林已經“修理”過我一次:我擔任一本詠物抒情談哲理的散文集的責編,送審時夾帶了一篇私貨——我寫的《荷花賦》。那時,我在文學的道路上剛剛起步,很想在公開出版的書刊上發表作品,躍躍欲試寫了一篇。可是老林招呼也沒打就撤掉了。我頓時蔫頭耷腦,如同一朵剛被風雨吹打又被陽光暴曬的花兒。
午飯時,老林從抽屜里拿出一只藍花大瓷碗,起身走到門口書柜的玻璃窗前停下,用手捋捋頭發,探頭照照,然后招呼我:“小杜,走,喂腦袋去。”我站起身,無精打采地跟在他的身后。一編室主要出版青年修養讀物,作者以黨政干部、學者和教師居多,我曾建議請作家撰稿,改變一下文章風格。老林一直不置可否。就是在那天的飯桌上,他肯定了我的想法。或許,每個人的心里都有一個陌生的自己。老林的支持一下子點燃了我的熱情,我的潛能得到超常發揮。隨后,我列出的幾十個選題把當時的文壇名家幾乎“一網打盡”。蘇叔陽住在北京的一個小四合院里,我找到他時,他正悠閑地躺在葡萄架下的躺椅上,搖著扇子,閉目養神。劉心武用一把鎖鎖門,當時的北京出版社在一座破舊的小樓上,條件很簡陋。蔣子龍剛剛出差回來,正清點票據,聽我說明來意,他友善地搖搖頭,說:“咳!打個電話就行了,這么遠,還用跑一趟?”王蒙到社里文學編輯室找王維齡、許岱聊天,見到冒冒失失闖入的我,很爽快地認領了一個題目:《真理是時間的女兒——青年人怎樣對待流言蜚語》。冰心坐在灑滿陽光的書房里,和藹的微笑至今仍在我的記憶深處綻放。她站起身走到寫字臺前,從筆筒里取出一支鉛筆遞給我,柔聲批評我的情景歷歷在目:“小伙子,當編輯的怎么能不隨身帶一支筆呢?”在張潔的住所,我見到了她的母親,那個世界上最疼她的人,善良而慈祥。王安憶、張抗抗也都答應撰稿。最難忘的是王愿堅,約完稿后,他送我走出很遠,一路上多有鼓勵和叮嚀。后來,詩人華靜采訪王愿堅的夫人翁大姐,老人家居然還記得我——當年那個上門約稿的小編輯。我和秦牧先生從未謀面,可是在廣東省作家協會門口,看到一個器宇軒昂的老人,我斷定他就是我要找的文學大咖,追上去一問,果然是。他耐心聽我說明意圖,欣然接受了我的約稿。這之后,我們的合作愉快而持久,印象中他從未拒絕過我,如果稿件遲交幾天,還會專門寫信說明原委。有同事從廣州組稿或開會歸來,常常會捎來他的問候。一向對名人大家敬而遠之的我,春天時會接到秦牧先生的電話,告訴我他來北京參加全國兩會,下榻在某飯店,約我有時間一晤。一次老林聽到是秦牧電話,要和我一起前往。他從飯店出來后仍興奮不已,原來他也是秦牧的鐵粉。一九九二年,驚聞秦牧先生辭世,我含淚寫了一篇文章《心香一瓣祭秦牧》,發表在《人民日報》的大地副刊上。
老林對我的工作很滿意,不過對我的個人創作卻表現冷淡。比如他有時會悄悄走到我身后,窺視我看的書或寫的文字,如果發現是在經營“自留地”,他臉一沉,沒好氣兒地說:“工作時間,不要干與工作無關的事。”只是,我對寫作有了濃厚興趣,嘗試著寫了兩篇思想散文。《我們還年輕》《露珠在陽光下才會閃光》,很快在《中國青年》雜志和《中國青年報》刊出。我大受鼓舞,于是突發奇想,列出了二三十個題目連同幾篇樣稿,寄給上海人民出版社,咨詢能否結集出版。一個月后,辦公室的門被敲開了,進來兩個操上海口音的中年人,自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張志國和顧興業,專程來北京組稿,順便見一見我。他們表態說,如果我的文章整體水準不低于樣稿,可以酌情考慮。我太興奮了,像是穿越草地的行者,突然見到漫天花雨。我送走客人,興沖沖找到老林請創作假。老林正在看稿,聽我說明了情況,端起茶杯吹吹上面的浮葉,兜頭澆過一盆冷水:“簽合同了嗎?沒有。對吧?整體達到樣稿水平,怎么把握?怎么衡量?很難有一個恒定的標準嘛!你也是編輯,難道聽不出來,這不過是一種客套?書能不能出完全在兩可之間。”他放下茶杯,咚的一聲,動靜有點兒大,看我的目光也如同秋天的風,帶著些許寒意,“況且,現在編輯室工作也很忙,你這時候請假去搞個人創作,合適嗎?”我無言。我承認,老林說的不無道理。但是,有些機會是單行道上的風景,一旦錯過就很難再次相遇。那年月還不興自費出書,在國家正規出版社出一本書有如攀登蜀道,要經過嚴格的選題論證和三審,許多喜歡文字的人終其一生也難有一本著作問世。我怎么能輕易放棄這個機會?我不想在生命中留下遺憾,即便沒有撞線,也不能放棄奔跑。
不給假就挑燈夜戰。那一段時間,我每天只睡五六個小時,除了上班就是寫作,熬到后來,每天暈暈乎乎的,走起路來就像腳踏五彩祥云。幾個月后,我懷著忐忑的心情將謄寫整齊的一摞書稿寄出。不久,由秦牧先生作序的青年修養散文集《青春的思索與追求》,就擺上了各地新華書店的書架。這件事后,老林看我的目光中有驚詫,也有歉意。
那時,我太年輕了,對圖書編輯的慢節奏漸生厭倦,對老林不支持我寫作也心存怨懟,動了調動的念頭。一九八四年,《中國交通報》創刊,曾是交通部政策研究室筆桿子的柳萌推薦我去。面試我的報社人事處處長王靜,是一個很干練的老大姐,她對我的情況很滿意,當即讓我填寫了“干部登記表”,并說:“只要中國青年出版社同意,交通部馬上下調令。”新的工作崗位對我很有誘惑力,尤其王靜處長的一句話更是令我神思飛揚:“來吧,年輕人,《中國交通報》雖是專業報紙,但它的活動半徑廣闊,世界上凡有港口的地方,你都有機會去。”
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在食堂找到老林,說:“我想和您說點兒事。”
老林很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把沒吃完的菜往碗里一扣,起身就走,說:“這幾天我很忙,沒空。”那時,他已升任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總編,分管好幾個部門,工作頭緒確實很多,但是再忙也不會抽不出幾分鐘吧?我感覺他是在刻意回避我。
忍了兩天,實在起急,一天下班后,我敲響了老林的家門。
老林開門,見是我,神情并不意外。他接過我帶去的一袋蘋果,隨手放在桌上,招呼我坐下,問:“你這么著急找我,有什么要緊的事嗎?”
我直截了當說了自己的想法。他或許是聽到了風聲,神色平和,坐在沙發上,右手的食指一下下有節奏地敲擊著扶手,問:“他們給了你什么承諾?”我回答:“記者部副主任。”又補充了一句,“沒主任。”老林點點頭,“噢”了一聲,說:“我們對你的安排也正在考慮呀!”我又補充了一句:“還答應給我分一套兩居室住房。”
老林又點點頭。那時我們一家三口住在不到八平方米的平房里,老林去過,深知它的逼仄。出版社宿舍緊張,他雖是副總編輯,卻不分管后勤。這回總沒話說了吧?不想,老林依舊不慌不忙地說:“出版社正計劃蓋職工宿舍。”
想到當初老林調我時的艱難,又看到他誠意滿滿,我調動的念頭開始動搖。但一想到無垠的大海和多彩的世界,我還是想走,就祭出撒手锏:“我不想編書了,想辦報或辦刊。”
這個要求無解。辦報、辦刊牽扯的方方面面太多了,非個人能夠協調。
沒想到,老林似乎已有思想準備,還是點點頭,微微一笑,說:“你想辦刊,不是不可以考慮呀。你搞一個方案,社里研究一下。”
就是那次談話之后,一本新刊《追求》橫空出世,并風行一時。
一九八七年,因為年少輕狂,在編輯理念上時與老林發生碰撞,又恰逢朋友不斷伸來橄欖枝,我還是決定調離。這一次,老林聽了我的想法,沉默不語,許久,才說:“你去找老闕吧。”老闕叫闕道隆,年過五旬,不茍言笑,時任中國青年出版社總編輯。他顯然和老林有過溝通,言辭懇切地挽留了我一番。他見我去意已決,便抽出一支煙點燃,默默吸了兩口,在煙灰缸的邊沿輕輕蹭去煙灰,說:“不急,你回去再想想,如果主意不變,三天后找我簽字。”
離開中國青年出版社后,我和老林的往來漸漸稀疏。一編室的老人幾次聚會,目睹時光如一把刻刀,把他從一個儒雅中年人雕刻成了菊老荷枯的長者。
我也不再年輕。往昔的一切隨時光走遠,留宿在一個叫“記憶”的客棧。
3
二〇一四年,我的長篇小說《江河水》出版,我意外地接到老林的電話。原來他看到了報紙上刊登的評論,很是高興,打電話希望我送他一冊簽名本。耄耋之年,老林還有精力讀完一本七十萬字的紙質書嗎?我很懷疑。沒想到,他不但讀了,還寫來了詳細的讀稿札記。這是他長年養成的習慣,審稿或看書,每每會記下一些稍縱即逝的感想。老林說:“小說可讀性很強,我是一口氣讀完的,如果改編成電視劇會很好看。”
不能不說,老林具有很高的文學鑒賞能力,他的讀稿札記頗有見地,對故事推進和小說的人物命運走向都有獨到見解。而且如他所料,小說出版后很快被影視公司買斷版權。可惜的是,四十四集電視連續劇《江河水》在江蘇衛視播出時,他已作古。
老林不事張揚,行事低調,我曾對他的文字水平有過質疑。一次我去送稿,無意間看到他辦公桌上攤開的本子,上面是他隨手寫下的讀稿札記,言簡意賅、文辭秀麗,而且字跡工整、娟秀飄逸,令我很是折服。還有一件事也糾正了我的認知。一九八〇年,老林接到一個約稿電話。我清楚地記得,他準備走時已是下午三點,他一邊穿風衣一邊對我說:“我要趕一篇稿子,先走一會兒。”第二天早上,署名“林君雄”的大塊文章《青年與修養》,就赫然在《中國青年報》頭版占據了半個版面。出手之快,令人咋舌。
老林很有才情,如果他專注個人寫作,也會成為作家或學者。他放棄了,他的志向是風,看上去無形,卻能吹動風車歡快地歌唱。他不鼓勵我個人寫作,希望我也成為一名專心致志的好編輯,并親自為我打了樣兒。印象中,老林用《青年與修養》的稿費買了一大包糖果,與編輯室的同事共享。這樣做很重要的原因是,文章的寫作占用了工作時間,報社約稿又與他所擔任的職務相關。那時候,中國青年出版社風氣很正,工作時間在院子里基本見不到人影,每個人都在埋頭工作。休息鈴聲一響,院子里才會熱鬧起來,打羽毛球的,練太極拳的,三五成群聊天兒的,都有。同事之間從不稱呼職務,即便是老社長朱語今,一個一九三六年參加革命的前輩,每天騎一輛半舊的自行車上班,人們見了他,也只是點頭一笑,叫聲“老朱”。整個出版社像一臺高速運轉的機器,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恪盡職守。
嚴苛是老林的表象,表象后面,其實也飛翔著一個很有趣的靈魂。
比如他不支持我個人寫作,卻暗中為我送來祝福。《荷花賦》被他斃掉后,我不服,投給了《奔流》。沒想到,這篇自由投稿很快被雜志采用了。同事小徐告訴我,老林在資料室看到《奔流》上刊登的《荷花賦》,興奮地對正在查找資料的他說:“如果我們編輯室未來能出一個作家,就是小杜。”說這話時他兩眼放光,好像這篇散文的作者不是我而是他。這個預判太令我震撼了,那是我的夢之鄉,能否抵達,心懷忐忑,老林的話無疑點亮了我心中的那一盞燈。嚴苛的老林有著非常寬厚的一面。一次,他帶我出差,晚上,我被他風箱一樣的呼嚕聲吵得無法入睡,翻身、咳嗽,一點兒也降低不了鼾聲的分貝,便去前臺另開了一間房。老林早晨起床后不見我的人影,急得夠嗆。后來,終于在服務員的引領下推開我的房門,走到床頭,他掀開被子,扒拉扒拉我的腦袋。我睜開眼,見是老林,以為他會生氣,不承想,老林的神色竟充滿驚喜,像是沙漠中的跋涉者終于看到了一泓清泉。他堆出滿臉苦笑,親切地問:“睡好了嗎?現在起來,還趕得上吃早餐。”
有一年夏天,中國青年出版社組織員工到北戴河休養,一編室下榻在一棟臨海的別墅里。當天晚上,老林張羅了一次螃蟹宴,在別墅的大露臺上,大家一人手捧一只大海蟹,蘸著加了姜末的醋,品蟹賞月。老林還用他那福建口音很濃的普通話朗誦了曹雪芹的《螃蟹詠》:“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茲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那晚夜色真美。海風輕拂,像綢緞劃過面頰。從陽臺望過去,無垠的大海就在眼前,夕陽的余暉映照在海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有萬千碎金在海面浮動。偶爾會看到數只海鷗如箭鏃一般掠過,幾艘帆船像倦鳥一樣歸巢。
螃蟹宴后回到房間,老林意猶未盡,坐了一會兒,又對我說:“走,讀海去。”
讀海?我還是第一次聽說,有些懵懂。隨老林來到海邊,我們并肩坐在沙灘上。
這時,晚霞早已退去,月亮緩緩升起,天色逐漸暗下來。夜一抖黑色的大氅,罩住了世間萬物。大海如一個飽經滄桑的長者,在濃濃的夜色中沉睡。海浪有節奏地拍打沙灘,發出一陣陣高亢的呼嘯,那該是大海發出的鼾聲吧。老林一直沉默,許久,才喃喃道:“你不覺得,海浪拍岸的聲音正是大海最深情的詩篇嗎?它讓我們領悟什么叫壯美,什么是永恒。而且海是由無數的江河匯成的,它的包容和坦蕩多么令人崇敬。”在月光的映襯下,老林做思考狀,面孔呈青銅色,很有一點兒羅丹的雕塑作品的范兒,“你再想,大海的深處有些什么?海溝、沉船、巨獸,或者遠古的城池遺址?哪樣不和時光相連?時光是歷史的載體,沒有了時光,一切歸零,而我們則是時光的剪裁者。”
或許是因為晚宴喝了點兒白酒,那天晚上,老林妙語連珠,頗有哲思高論。他告訴我,一個人不僅要讀書,還要讀山、讀水,總之,要努力領悟自然,使自己的心智更加健全。
這個場景定格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距今已過了四十余年,仍恍如昨日。
老林是我編輯生涯的第一個老師,他的嚴苛猶如一座山,看上去巨石突兀,卻也有溪水潺潺。這么多年過去,心中的芥蒂早已隨風消散,剩下的只有自省與感慨了。無邊往事難忘卻,心向昨天覓舊篇。蠟燭有心始垂淚,一夢依稀四十年。什么是感恩?真正的感恩不在乎是否有過嫌隙,只要他是一束光,曾經照亮你的人生。牢記逝去的美好,珍惜相伴的日子,一生有一生的緣分,一程有一程的芬芳。
我抑制住內心的悲傷,告訴來電話的老林的女兒小英:“去,我一定去!”在老林的遺像前,我會深深鞠上三個躬,并虔誠地說一句:“敬愛的君雄老師,一路走好!”
——敬愛的君雄老師,您是我生命中的啟明星,在那些暗淡的日子里,是您給了我前行的勇氣與方向。
【作者簡介】杜衛東,曾任《人民文學》副社長、《小說選刊》主編。已發表各種題材文學作品五百余萬字。結集出版四十余部,作家出版社出版四卷本《杜衛東自選集》。出版長篇小說《吐火女神》、《山河無恙》、《江河水》(與人合作),散文集《歲月深處》由美國全球按需出版集團譯成英文在全球發行。散文《明天不封陽臺》被收入蘇教版初二語文課本和香港高中語文教材。曾獲《人民文學》報告文學獎、《北京文學》散文獎、全國報紙副刊年度金獎等。另有編劇作品《洋行里的中國小姐》《江河水》和《新來的鐘點工》。
責任編輯 練彩利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