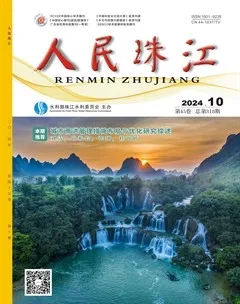長江中下游流域基流時空變化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摘 要:基流是徑流的重要組成部分,選擇合理的基流分割方法對基流進行估算,了解流域基流和基流指數的變化特征,明確基流和基流指數變化的驅動因素對于河流生態的保護與管理至關重要。基于長江中下游流域64個水文站點日徑流數據和氣象數據,對比分析3種數字濾波法(Lyne-Hollick法、Chapman-Maxwell法、Eckhardt法)和平滑最小值法的基流分割結果,并從氣候因素和下墊面因素兩方面分析基流和基流指數變化的驅動因素。結果表明,Chapman-Maxwell濾波法更適用長江中下游流域的基流分割;長江中下游流域干流的基流遠大于支流,豐水期基流大于枯水期,而基流指數則沒有明顯的干支流區別,枯水期的基流指數明顯大于豐水期。氣候和下墊面因素是豐水期與枯水期基流變化的驅動因素。其中,氣候是豐水期和枯水期基流減少的主導因素,而下墊面因素在枯水期基流的增加上占主導地位。
關鍵詞:基流;基流指數;氣候因素;下墊面因素;長江中下游流域
中圖分類號:TV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9235(2024)10-0076-12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ase Flow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JIANG Lei1,2,3, HE Ya'nan4, GU Xihui1,2,4*
(1. The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Disaster Prevention,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29, China; 2. Key Lab of Basin Water Resource and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 in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10, China; 3. Shenzhen Longgang Drainage Co., Ltd, Shenzhen 518116, China; 4.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Science,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Base flo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noff, so it is important to choose a reasonable base flow segmentation method to estimate base flow, understand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base flow and base flow index, and identify the driving factors of base flow and base flow index chang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river ecology. Based on the daily runoff data and meteorological data of 64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base flow segmentation results of three digital filtering methods (Lyne-Hollick method, Chapman-Maxwell method, and Eckhardt Method) and smoothing minimum method werecompared,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base flow and base flow index change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climate and underlying surface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pman-Maxwell filtering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r base flow segment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base flow of the main stream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much larger than that of tributaries. The base flow is greater in wet seasons than in dry seasons, while the base flow index i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main stream and tributaries, and the base flow index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dry seasons than in wet seasons. Climate and underlying surface are the driving factors of base flow changes between wet and dry seasons. Specifically, climate is the dominant factor in the reduction of base flow in wet and dry seasons, while the underlying surface is the dominant factor in the increase of base flow in dry seasons.
Keywords: base flow; base flow index; climatic factors; underlying surface facto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徑流由坡面流、匯流和基流組成[1-2]。基流通常被定義為水流中緩慢變化的部分,主要由地下水儲存或濕地、湖泊、冰雪融水等具有延遲特性的水體組成[3-5]。基流是枯水季節徑流的主要組成部分,且相對穩定[6]。因此,了解基流的變化及其驅動因素對于維持河流生態、水環境保護、以及水資源的管理和規劃至關重要[6-7]。
基流無法通過測量技術獲取,需要對徑流利用分割方法進行分割。采用合理的基流分割方法對基流進行估算,是研究基流的基本支撐,且對于地區水平衡和水資源管理具有重要意義[7-8]。常見的基流分割方法包括數字濾波法[9-11]和平滑最小值法[5]。張泳華等[5]采用數字濾波法對東江流域的基流進行分割,且認為在該區域數字濾波法優于平滑最小值法。王晨楊等[7]對比分析局部最小值法、單參數濾波法和遞歸數字濾波法,發現遞歸數字濾波法更適合密云水庫白河流域的基流分割[7]。
變化環境下的徑流演變,是科學研究的熱點[12],氣候變化影響的基流變化及其主要影響因素正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13]。呂向林等[14]采用數字濾波分割基流,得到汾河在2016年的過去60多年呈現出顯著的下降趨勢,究其原因,主要歸因于人類活動中的煤礦開采和地下水開采,另有9. 96%歸因于降水量的減少。王曼玉等[9]基于Chapman-Maxwell濾波法研究了1963—2015年的潮河流域基流變化及其影響因素,發現潮河流域基流呈現顯著下降趨勢,并分析得出降水與基流量呈現正相關,潛在蒸散發與基流量呈現負相關。賈建偉等[15]針對長江流域的12個二級水資源分區的逐年基流總量,發現長江上游逐年基流趨勢性較中下游河段更顯著。近年來,氣候因素(包括降水、氣溫、潛在蒸散發、干旱指數)和下墊面因素(包括陸地儲水量和植被葉面積指數)都在響應氣候變化,且這些因素影響了基流和基流指數的變化。目前,中國基流變化的歸因,主要針對小范圍支流區域的研究,通常這些區域更容易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而對中國第一大水系——長江中下游流域的基流時空變化分析及其歸因分析研究較少[16-17]。
因此,本研究針對長江中下游流域的基流主要開展以下三方面的研究:①采用Nash-Sutcliffe效率系數(NSE)、平均絕對誤差(Mean Absolute Error,MAE)以及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對基流分割結果進行評價得到長江中下游流域最優基流分割方法;②分析長江中下游流域基流及基流指數的時空變化特征;③將基流與基流指數的變化與流域氣溫、降水、潛在蒸散發、干旱指數、陸地儲水量和植被葉面積指數(單位土地面積上植物葉片總面積占土地面積的倍數)聯系起來,分析影響流域內基流的主要驅動因素。
1 研究數據
1. 1 氣象數據
本研究選用的氣象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氣候變化研究中心(http://data.cma.cn/)1961—2020年逐日的CN05格點化觀測數據集[18],包括降水、日最高氣溫、日最低氣溫、日平均氣溫、風速等變量,空間分辨率為0. 25°×0. 25°。潛在蒸散發通過彭曼-蒙特斯公式計算獲得[19]。干旱指數是年總潛在蒸散發量除以年總降水量。
1. 2 水文數據
本研究選取了長江中下游流域64個具有代表性的水文站[20],水文站徑流數據為實測的日徑流數據 (http://113. 57. 190. 228: 8001/web/Report/RiverReport? WxUg5ztDmi=1656282535688# 和http://yzt. hnswkcj. com:9090/#/),來源于湖北省水文水資源中心和湖南省水文水資源勘測中心。每個水文站點都有10 a以上的完整觀測數據(年缺測率在10%以下為一個完整的觀測年份)。為了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和連續性,采用同時期平均值對缺測數據進行了插補。數據起始年份多集中于1986—2006年,結束年份主要集中在2015—2018年,完整的記錄年數均在20 a以上,少量站點達到了50 a以上,缺測率集中在2. 5%~3. 5%。
1. 3 下墊面數據
陸地儲水量來源于Li等[21]的數據集(https://datadryad. org/stash/dataset/doi: 10. 5061/dryad.z612jm6bt),空間分辨率為0. 5°×0. 5°。1982—2018年植被葉面積指數數據采用GLOBMAP LAI(Version3)數據集[22](https://zenodo. org/record/4700264#. Yjxa3U1ByUk),空間分辨率為0. 072 727 3°×0. 072 727 3°。
2 研究方法
2. 1 基流分割方法
基流是河道內常年存在的那部分徑流,基流指數是基流占河流徑流的比重。基流不能直接通過觀測或者測量獲取,只能通過基流分割的方法來獲取。基流指數可以用基流分割獲取的結果計算獲得。從已有的多種基流分割方法中選取了廣泛使用的4種方法,分別是3種數字濾波法(Lyne-Hollick法[19]、Chapman-Maxwell法[23]、Eckhardt法[24])和平滑最小值法(UKIH)[25]。數字濾波法來源于信號分析,將信號分析與水文研究相結合,主要原理是將日徑流看作是由高頻信號(快速徑流)和低頻信號(基流)組成的,再通過濾波函數將高頻信號和低頻信號分離,從而獲得基流[6,2627]。平滑最小值法是英國水文研究所在1980年提出的一種基流分割方法,主要原理是將日徑流序列按照N天分為不重疊的多個時間段,篩選每個時間段內徑流最小值,用于確定拐點;根據拐點進行線性插值求出基流值[5,28-30]。用枯水指數(Q90/Q50)[26,28,31]乘以年總徑流來估測年總基流值,以此作為標準,與不同基流分割方法的結果進行對比,使用Nash-Sutcliffe效率系數(NSE)、平均絕對誤差(MAE)以及均方根誤差(RMSE)來對估測值和基流分割結果進行評價[13]。
結果顯示,Lyne-Hollick法(LH法)、Chapman-Maxwell法(CM法)、Eckhardt法(ECK法)和平滑最小值法(UKIH法)的Nash-Sutcliffe效率系數NSE(Nash-Sutcliffe efficiency coefficient)分別為-0. 51,0. 96,0. 20和-0. 25;Lyne-Hollick法的平均絕對誤差MAE(Mean Absolute Error)和均方根誤差RMSE(Root Mean Square Error)分別為1 663、3 061;Chapman-Maxwell法中MAE和RMSE分別為333、639;Chapman-Maxwell法的MAE和RMSE分別為2 255、4 194。NSE越接近1,MAE和RMSE數值越接近0,模擬效果越好。通過上述比較,Chapman-Maxwell法基流分割結果更接近基流估測值,故選擇該法對長江中下游流域進行基流分割(圖1)。
2. 2 不同驅動因子對基流和基流指數的貢獻
基流變化一方面取決于降水、氣溫、潛在蒸散發、干旱指數等氣候因素,另一方面取決于陸地儲水量和植被葉面積指數等下墊面因素[32-34]。首先基于Mann-Kendall非參數檢驗[35]對長江中下游流域的基流和基流指數進行趨勢檢測。采用線性回歸[1]對基流及基流指數與驅動因子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然后使用偏微分方程法對不同驅動因子對基流和基流指數的相對貢獻進行分析,最后通過利用多元線性回歸系數與各因子的趨勢值的乘積估算基流和基流指數,將其變化趨勢與利用CM法獲得的基流和基流指數的變化趨勢進行對比,來驗證不同驅動因子相對貢獻的可靠性。
偏微分方程法是由Roderick等[36]和Naeem等[37]提供的一種利用偏導數計算每個影響因素的單獨貢獻的方法[36-37]。該方法基于偏相關系數的基本原理,通過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來衡量2個隨機變量之間的關聯程度,從而使每個影響因子的單獨貢獻更加可靠。所有的數據集都被歸一化到基流(基流指數)的范圍,以量化每個因素的貢獻。歸一化方法見式(1):
式中:x為歸一化時間序列;x'為某影響因子1979—2018年的值;xmin為1979—2018年影響因子的最小值;xmax為1979—2018年影響因子的最大值;y為1979—2018年基流(基流指數)的最大值。上述方程適用于每個影響因子。
dt dt
儲水量、濕潤指數、潛在蒸散發、降水和溫度的斜率;R為偏微分方程的殘差。
通過將與平均值的絕對變化代入上述方程,可以得到式(3):
3 研究結果
3. 1 基流和基流指數的時空變化特征
圖1展示了長江中下游流域基流和基流指數的年內變化特征。從整體上看,基流的年內變化呈現中間高兩邊低的特征,年內基流量主要集中在豐水期(6、7、8、9月);基流指數呈中間低兩邊高的特征。基流占比最大的月份出現在7月,7月基流量約占全年的13. 2%;最小的在2月,2月基流量約占全年3. 7%。年內占比最大月份與最小月份差值為9. 5%。基流指數反映的是基流占總徑流的比值,在北半球冬半年,基流指數較大,夏半年基流指數則較小;基流指數最大的月份在10月,中位值為0. 62;最小值在5、6月份,中位值為0. 42。
從季節上看,豐水期(6、7、8、9月)的基流占全年比值最大,枯水期(12、1、2、3月)最小。基流指數的最大和最小值出現的月份都位于平水期(4、5、10、11月),最大值出現在豐水期結束后的平水期,這可能是由于基流性質比較穩定,變化幅度較小,豐水期結束,降水減少,徑流隨之減少,而基流此時減少不明顯,基流指數增加;最小值出現在枯水期結束后和豐水期開始前的平水期,枯水期結束,平水期開始,降水較之前有所增加,徑流隨之增加,此時基流增加不明顯,基流指數減小。
基流和基流指數的年內變化趨勢具有較大的差異,基流和基流指數的空間分布也具有較大的異質性(圖2)。從整體上來看,長江中下游干流的基流較大,這與長江中下游干流徑流量較大有關。全年和豐水期的干流基流大都大于5 000 m3/s,枯水期大約在2 000~5 000 m3/s(圖3a—3d)。整個流域豐水期的基流量較大,枯水期較小,這是由于豐水期降水充沛,徑流量大,基流也隨之增加。流域內基流指數在全年分布較均勻,主要集中在0. 45~0. 50,沒有明顯的區域差異。枯水期的基流指數高于全年、平水期和豐水期。在枯水期,長江中下游流域偏北的子流域基流指數更大;豐水期與之相反,流域偏南的站點基流指數更大;平水期基流指數分布與枯水期相似(圖3e—3h)。豐水期的基流量大于枯水期,枯水期基流指數高于豐水期,這與上文基流與基流指數的時間分布特征相一致。
整體上看,在1979—2018年,全年基流量上升和下降的站點數量相當。枯水期的大部分站點呈增加趨勢,呈增加趨勢的站點比例約為78%,其中顯著增加站點的比例高達42%;豐水期大部分站點呈減少趨勢,呈減少趨勢的站點約占67%(圖3a—3d)。這一現象很可能與水庫的建設有關,水庫起到了“削峰補枯”的調蓄作用,調節了豐水期和枯水期的徑流量。全年、枯水期和豐水期大部分站點的基流指數都呈增加趨勢,其中豐水期呈增加趨勢的站點比例最大,呈顯著增加趨勢的站點比例也最大。水庫調蓄使得豐水期徑流減少,基流減少不明顯,基流指數增加。枯水期和豐水期基流指數增加的區域位置略有不同,在枯水期,呈增加趨勢的站點主要分布在干流以南;豐水期,主要聚集于干流周邊,南北都有分布(圖3e—3h)。
3. 2 基流和基流指數變化歸因
對基流和基流指數的6個影響因子(降水、溫度、潛在蒸散發、干旱指數、陸地儲水量和植被葉面積指數)的變化趨勢進行分析(圖4)。
結果顯示,以西南縱向的山區為界,流域東側的陸地蓄水量呈現顯著增加的趨勢;而西側流域上游地區的基流大面積呈現出顯著減少的趨勢。從整體上看,植被葉面積指數在全年、平水期和豐水期大部分區域都呈增加趨勢,其中豐水期呈現顯著增加趨勢的區域比例最大;相反,枯水期大部分區域呈現顯著減少趨勢。豐水期和枯水期植被葉面積指數的空間變化趨勢恰好相反。在過去40 a,長江中下游流域大部分區域氣溫呈顯著增加的趨勢,平水期和豐水期增加趨勢不及全年和枯水期顯著。
降水在流域大部分區域呈增加趨勢,但是除豐水期增加趨勢較為顯著之外,其他時期增加趨勢并不顯著。潛在蒸散發主要受氣溫的影響,大部分區域呈顯著增加趨勢,豐水期潛在蒸散發的空間變化趨勢與氣溫基本一致。干旱指數受到降水和潛在蒸散發的共同影響,主要呈現出減少的趨勢,表明流域內正在變干,不過顯著的區域較少。
圖5、6分別展示了基流與基流指數變化趨勢和影響因子變化趨勢的相關性。
年尺度上,陸地儲水量、植被葉面積指數、氣溫和潛在蒸散發變化趨勢與基流變化趨勢呈負相關,而降水和干旱指數與基流呈正相關。平水期與豐水期陸地儲水量和植被葉面積指數與基流的相關性與全年一致,而枯水期恰好相反。氣溫升高導致了蒸散發的增加,從而使得基流量減少。氣溫升高也會導致高海拔地區冰川和冰雪融水量增加。在北半球的枯水期,氣溫升高導致基流量的減少與冬季積雪融水導致的基流增加量相抵消,所以枯水期基流隨氣溫變化不明顯,但是全年和平水期、豐水期的基流隨著氣溫升高而減少。枯水期和平水期的降水與基流相關性不明顯,這影響了干旱指數的變化。年尺度上,隨降水和干旱指數的增加,基流增加,與之相反,隨潛在蒸散發的增加,基流減少。年尺度上,6個影響因子的變化趨勢與基流指數的變化趨勢相關性不顯著。在枯水期,陸地儲水量、氣溫和潛在蒸散發與基流指數呈負相關,植被葉面積指數、降水和干旱指數與基流指數呈正相關。豐水期,除了植被葉面積指數外,其他5個影響因子與基流指數的相關性都與枯水期呈現出完全相反的趨勢。在平水期,植被葉面積指數與基流指數呈負相關,隨著植被葉面積指數的增加,基流減少。而在豐水期和枯水期,都隨著葉面積指數的增加,基流增加。由于枯水期、平水期和豐水期各影響因子與基流指數不同的相關性之間相抵消,導致各影響因子對全年基流指數的變化沒有展現出明顯的相關性。
整體上看,降水和干旱指數對基流的相對貢獻最大,其次是陸地儲水量,主要體現在全年和豐水期(圖7)。
年尺度上,陸地儲水量、降水和干旱指數主要驅動了基流的增加,氣溫和潛在蒸散發主導了基流的減少;豐水期和平水期基流變化的主導因子基本與年尺度上一致;枯水期則只有陸地儲水量主要驅動基流的增加。潛在蒸散發對豐水期基流的減少的影響較大,這可能與中國豐水期處在夏季有關,氣溫升高,潛在蒸散發增大。在豐水期,氣溫也驅動了絕大多數的站點的基流量的減少,與潛在蒸散發的影響一致。在枯水期,氣溫對一半站點基流量的增加有貢獻,這可能與春季氣溫增高,冰雪融化,增加了徑流量有關。
對比分析基流指數,從空間各站點看,降水和干旱指數相對貢獻最大(圖8)。整體上看,單影響因子對基流指數減小的貢獻高于對基流指數增加的貢獻。降水在4個時期較為一致驅動了基流指數的減小,主要是因為降水是徑流的主要補給來源,降水增加,徑流增加,基流指數減小。在豐水期,植被葉面積指數、陸地儲水量和潛在蒸散發驅動了大部分站點基流指數的增加。在平水期,除氣溫外,其他因子驅動了大部分站點的基流指數減小。在枯水期,陸地儲水量、干旱指數、潛在蒸散發以驅動基流指數增加為主導,而降水以減少基流指數為主導,氣溫和植被葉面積指數對基流指數增加產生積極和消極的影響的站點相當。
下墊面因素(陸地儲水量和植被葉面積指數)在枯水期基流的增加上占絕對的主導地位。在平水期,下墊面因素對基流指數增加的貢獻大于氣候因素(氣溫、降水、潛在蒸散發和干旱指數),其他時期二者對基流指數增加的影響不相上下。在豐水期和平水期,與下墊面因素相比氣候因素對基流指數減小的貢獻更大。
4 結論
本文利用長江中下游流域64個水文站點日徑流數據,通過基流分割方法適用性分析,選擇適用于長江中下游流域的CM法來分割基流,計算基流指數,分析基流和基流指數的時間和空間分布特征及變化趨勢,并進一步探討下墊面和氣候因素對基流和基流指數變化的影響。初步得到以下結論。
a))豐水期基流在年內占比最大,枯水期最小;基流指數最大值出現在豐水期后的平水期,最小值出現在枯水期結束后和豐水期開始前的平水期。
b))長江中下游流域干流的基流遠大于支流,豐水期基流大于枯水期,而基流指數則沒有明顯的干支流區別,枯水期的基流指數明顯大于豐水期。
c))1979—2018年,枯水期的基流明顯增加,而豐水期的基流則以減少為主。且枯水期,基流指數增加的站點主要位于干流以南。
d))氣候因素(干旱指數、潛在蒸散發、降水和氣溫)是豐水期和枯水期基流減少的主導因素,而下墊面因素(植被葉面積指數、陸地儲水量)在枯水期基流的增加上占主導地位。
參考文獻:
[1] TAN X J, LIU B J, TAN X Z. Global Changes in Baseflow Underthe Impacts of Changing Climate and Vegetation[J].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2020, 56(9). DOI:10. 1029/2020WR02-7349.
[2]許心怡,李建柱,馮平.不同降水產品在灤河流域徑流模擬中的適用性[J]. 水力發電學報,2021,40(12):25-39.
[3]譚光超,李姍姍,李智民,等. 多種數值模擬基流分割法在鄂北丘陵山區隨縣的應用對比研究[J]. 資源環境與工程,2018,32(4):611-616.
[4]董廣博 . 皖南郎川河流域基流分割[J]. 科學技術創新,2020(30):141-142.
[5]張泳華,劉祖發,趙銅鐵鋼,等. 東江流域基流變化特征及影響因素[J]. 水資源保護,2020,36(4):75-81.
[6]周星,沈忱,倪廣恒,等. 結合退水曲線的數字濾波基流分割方法[J].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7,57(3):318-323,330.
[7]王晨楊,閆鐵柱,翟麗梅,等. 密云水庫白河流域基流演變特征[J].生態學報,2022,42(8):3181-3190.
[8]張軍龍. 基于基流分割的流域地下水—地表水相互作用研究[D]. 西安:西北大學,2017.
[9]王曼玉. 潮河流域基流變化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D]. 北京:北京林業大學,2018.
[10]張洪波,陳克宇,俞奇駿,等. 地下水強擾動地區的徑流還原計算方法[J].水力發電學報,2015,34(11):95-105.
[11]楊哲,張行南,夏達忠,等. 基于包氣帶厚度的流域蓄水容量計算及水文模擬[J]. 水力發電學報,2015,34(3):8-13.
[12]夏軍,馬協一,鄒磊,等. 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漢江上游徑流變化影響的定量研究[J].南水北調與水利科技,2017,15(1):1-6.
[13]鐘皓. 漳河上游流域基流變化特征及其歸因分析[D]. 邯鄲:河北工程大學,2021.
[14]呂向林,姬世保,仇亞琴,等. 汾河流域上游基流特征及其影響因素[J].水資源保護,2022,38(2):147-153.
[15]賈建偉,劉昕,王棟. 長江流域天然河川基流量時空演變特征分析[C]//2021學術年會論文集第二分冊.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21:405-413.
[16]孫志偉,梁越,鈕新強.基于數字濾波法的長江上游流域基流時空分布特征[J].長江科學院院報,2023,40(11):23-28,35.
[17]黃珊珊,董前進.長江流域上中下游基流演變規律及與降水量關聯分析[J].水電能源科學,2022,40(7):10-13.
[18]吳佳, 高學杰. 一套格點化的中國區域逐日觀測資料及與其它資料的對比[J].地球物理學報,2013,56(4):1102-1111.
[19]LYNE V D, HOLLICK M. Stochastic Time-Variable Rainfall-Runoff Modeling[C]//In Institute of Engineers Australia National Conference,1979.
[20]何亞男,王雙玉,顧西輝.水文變異下長江流域的生態徑流變化、影響及歸因[J].武漢大學學報(理學版),2023,69(3):313-322.
[21]LI F P, KUSCHE J, CHAO N F, et al. Long-term (1979-present) total water storage anomalies over the global land derived by reconstructing GRACE data[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21, 48(8). DOI:10. 1029/2021GL093492.
[22]LIU Y, LIU R G, CHEN J M. Retrospective retrieval of long-term consistent global leaf area index (1981–2011) from combined AVHRR and MODIS data[J]. Journal Geophysical Research, 2012, 117(G4). DOI:10. 1029/2012JG002084.
[23]CHAPMAN T G , MAXWELL A I. Baseflow Separation -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Methods with Tracer Experiments[C]//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Symposium, Australia,1996.
[24]ECKHARDT K. A comparison of baseflow indices, which were calculated with seven different baseflow separation methods[J]. Journal of Hydrology, 2008, 352(1/2):168-173.
[25]PIGGOTT A R , SYED M, CHUCK S. A revised approach to the UKIH method for the calculation of baseflow / Une approche améliorée de la méthode de l'UKIH pour le calcul de l'écoulement de base[J].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HydrologyBulletin, 2005, 50(5):911-920.
[26]韓鵬,王藝璇,李岱峰. 黃河中游河龍區間河川基流時空變化及其對水土保持響應[J]. 應用基礎與工程科學學報,2020(3):505-521.
[27]趙棟. 黃土高原典型流域基流分割及其演變驅動因素分析[D].鄭州:鄭州大學,2021.
[28]周嘉欣,丁永建,吳錦奎,等. 基流分割方法在疏勒河上游流域的應用對比分析[J]. 冰川凍土,2019,41(6):1456-1466.
[29]張一多. 基流分割在蟒河上游流域洪水預報中的應用[D].鄭州:華北水利水電大學,2021.
[30]樊晶晶,劉純,穆征,等. 不同基流分割方法在秦嶺山區-黃土高原過渡帶的對比應用及其演化規律研究[J].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2,43(3):1-10,27.
[31]夏露,楊晶,馬耘秀,等.植被恢復和氣候變化對汾河源區徑流及其組分的影響[J].生態學報,2024,44(11):4597-4608.
[32]盛菲,劉政,劉士余,等.彭沖澗小流域基流變化特征及其歸因分析[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2022,44(6):1569-1581.
[33]趙梳坍.巖溶區流域徑流變化特性及其量化分離研究[D].南寧:廣西大學,2022.
[34]李蘇.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流域徑流的影響研究[D].邯鄲:河北工程大學,2021.
[35]KENDALL M G. Rank Correlation Methods [J].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0, 25(1):86-91.
[36]RODERICK M L , ROTSTAYN L D , FARQUHAR G D , et al. On the attribution of changing pan evaporation[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7, 34(17). DOI:10. 1029/2007GL031166.
[37]NAEEM S, ZHANG Y Q, TIAN J, et al. Quantifying the impacts of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and climate variations on vegetation productivity changes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15[J]. Remote Sensing, 2020, 12(7). DOI:10. 3390/rs1207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