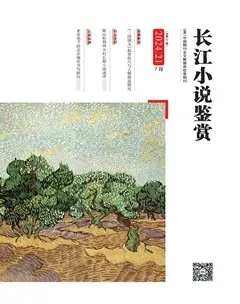符號敘事學視閾下海明威小說的電影改編研究
[摘 要] 美國當代著名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小說具有鮮明的影像化特征。其諸多作品被改編成電影,走上銀幕世界。本文從語言符號與影像符號的敘事差異、敘事符號的跨媒介應用及意識流手法的影像符號表達三個層面就海明威小說的電影改編進行符號敘事學探討,有利于深化對文學與電影敘事規律的研究。
[關鍵詞] 符號敘事 海明威 電影改編
[中圖分類號] I10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1-0105-04
美國當代著名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的小說具有鮮明的影像化特征,并被稱為電影化的作家[1]。鑒于海明威的世界文壇影響力,其諸多作品被改編成電影,走上銀幕世界。海明威本人也曾積極參與到自己部分作品的電影藝術改編過程中,并提出了許多建議。但是,并非所有其改編后的影片都獲得了成功。就海明威小說的電影改編進行相關研究成果較為顯著,但大都圍繞改編本身需要考慮的要素開展,就敘事活動的本質并未觸及過深的問題。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電影作品,敘事的基本元素是符號。就從文本敘事到影像敘事的轉換進行探討,敘事符號便成為重點關注的研究對象。本文擬從語言符號與影像符號的敘事差異、敘事符號的跨媒介應用及意識流手法的影像符號表達三個層面就海明威小說的電影改編進行符號敘事學研究,以深入探索文學與電影兩大敘事藝術之間的互動關系,及探究符號敘事的內在規律。
一、語言符號與影像符號的敘事差異
文學作品與電影作品的敘事差異,從根本上說是敘事符號之間的差異。文學作品的敘事元素為語言符號,集中呈現了人類的經驗與情感。電影作品的敘事元素則是影像符號,具體涵蓋繪畫、圖像、語言、音樂、色彩等多種形式,是抽象語言符號的具象化。因此,無論是文學還是電影,其敘事的根本元素均為符號。符號是意義的載體。同語言符號相比,影像符號種類更加豐富,內容更加多元。世界有多精彩,電影就可以被呈現得有多精彩。文學作品所呈現的精彩世界,需要依靠讀者豐富的想象力去實現,而電影作品本身,就是人類豐富的想象力對抽象概念符號的實踐結果。意義的呈現對于文學創作者而言,需要一定的語言符號使用技巧及寫作修辭手法。這對讀者來說,盡管在閱讀上增加了難度,但仍然可以借助文字表層的語義功能來實現整體上不同程度的理解。電影符號則因為運用鏡頭語言與蒙太奇剪輯技術,結合符號的復雜類別,無異于將觀眾再次置身于現實世界中,需要他們自身將人工敘事所描繪的場景在各自大腦中被重新進行認知加工,以實現概念化的識解目的,從而達到對電影敘事內容的精準掌握。作為人文藝術領域的兩大敘事形式的應用主體,文學創作者與電影藝術家既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符號集合的使用者,又是具有個性化意義的創新符號的制造者。
海明威小說的語言特征鮮明,句式簡短,這主要得益于其早期的報社記者工作經歷。因為新聞報道語言是通訊性和概念性的,而文學語言則是表現性和情感性的。換句話說,新聞報道語言的功能是向讀者傳遞關于某種事實或事件的信息,而文學語言旨在讀者的內心深處喚起某種特殊的情感或經驗[2]。以《老人與海》為例,該作品語言凝練、含蓄,富有象征意義,且心理描寫較多。然而,對于從語言符號到影像符號的轉換而言,敘事的效果則差異顯著。對于語言符號而言,不存在任何不可以被表達或難以表達的內容,而只存在是否易于被讀者理解這一事實。而將語言符號所表達的內容、所傳達的意義及所描繪的對象完全對應地用影像符號進行呈現,則是極具有難度的事情。在電影工業技術手段尚不成熟的歷史時期,如何讓動物說話,讓兒童角色被演繹得生動形象,讓神仙鬼怪等脫離現實的畫面真實可信,均是早期電影藝術家們所面臨的重大難題。就《老人與海》的電影改編而言,比如老漁民圣地亞哥與大魚在海中搏斗的過程,以及魚兒在海面跳躍等場景,甚至小男孩兒馬洛林的扮演者是否可以很好詮釋這一角色等方面,均顯現了文字符號到影像符號轉化過程中的微妙之處。小說《老人與海》共有三個電影改編版本,分別于1958年、1990年和1999年拍攝。在三部影片中,海明威本人親自參與了1958年版《老人與海》電影的拍攝工作。作為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及優秀的藝術家,海明威本人深知小說《老人與海》敘事節奏緩慢,語言符號的焦點主要在于圣地亞哥的思想與感情,很難拍成一部激動人心的電影作品,尤其小說中那條大魚,需要用道具來做成,效果可想而知。1990年版本的電影《老人與海》則相較原著增加了人物角色,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原著的節奏與風格。改編最為成功的反而是1999年由俄羅斯導演亞歷山大·彼得洛夫執導的動畫短片。該短片獲得第7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動畫短片榮譽。無論是小男孩馬洛林的演技問題、大魚的表演問題等,均在藝術家的筆下進行了精彩的呈現。海明威在其小說中所呈現的意境與語言魅力,完全通過這種在玻璃板上所進行的油彩繪畫進行了完美表達。整個畫作歷時兩年半之久,可以說是電影藝術家們的傾心之作。
二、敘事符號的跨媒介應用
海明威小說的語言敘事風格,以其“冰山原則”著稱于世。簡潔的文字、鮮明的形象、豐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是構成“冰山原則”的基本要素[3]。文學作品的敘事元素為文字符號,集中呈現了人類的經驗與情感。電影作品的敘事元素則是繪畫、圖像、語言、音樂等多種符號,是文字符號的具象化。因此,無論是文學還是電影,其敘事的根本元素均為符號。符號是意義的載體。同文字符號相比,電影符號種類更加豐富,內容更加多元。世界有多精彩,電影就可以被呈現得有多精彩。文學作品所呈現的精彩世界,需要依靠讀者豐富的想象力去實現,而電影作品本身,就是人類豐富的想象力對抽象概念符號的實踐結果。意義的呈現對于文學創作者而言,需要一定的語言符號使用技巧及寫作修辭手法。這對讀者來說,盡管在閱讀上增加了難度,但仍然可以借助文字表層的語義功能來實現整體上不同程度的理解。電影符號則因為運用鏡頭語言與蒙太奇剪輯技術,結合符號的復雜類別,無異于將觀眾再次置身于現實世界中,需要他們自身將人工敘事所描繪的場景在各自大腦中被重新進行認知加工,以實現概念化的識解目的,從而達到對電影敘事內容的精準掌握。作為人文藝術領域的兩大敘事形式的應用主體,文學創作者與電影藝術家既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符號集合的使用者,又是具有個性化意義的創新符號的制造者。美國作家海明威的長篇小說《永別了,武器》曾兩次被改編成電影,第一次拍攝完成于1932年,并于1934年獲得第6屆奧斯卡提名;第二次是在1957年拍攝完成[4]。就敘事主題而言,小說《永別了,武器》主要是表達反戰思想及描寫戰爭中的愛情。該小說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大利戰場為背景,以主人公亨利中尉與英國護士凱瑟琳的愛情故事為主線,重點描寫了亨利如何先后“告別”了“戰爭”和“愛情”,或者更確切地說“戰爭”如何毀滅了“愛情”,從而深刻地揭露了戰爭毀滅生命、摧殘人性的本質[5]。從語言風格上看,其突出地體現了“冰山原則”的運用,選用簡單易懂的生活日常用語,含蓄地表達深刻的情感。海明威本人也在談及他的寫作風格時說:“我有時覺得我的風格,與其說是直接的,倒不如說是暗示的。讀者往往得開動想象力,才能抓住我們思想的最微妙的部分。”[6]例如,在小說第一章的結尾處,有這樣一句描寫:“冬季一開始,雨便下個不停,而霍亂也跟著雨來了。瘟疫得到了控制,結果部隊里只死了七千人。”在上述句子中,“一……便……”這個句式體現了海明威的另一個寫作風格,那就是“采用有節奏的句子結構,重復、排比、反比等,好像是音樂旋律,旨在召喚一種心理印象。”“結果”一詞的運用含蓄深刻,意味豐富,讓讀者不禁陷入對戰爭與生命關系的深刻思考。而對于改編后的電影來說,亨利與凱瑟琳之間的愛情故事占據了敘事的主要內容。相對于電影敘事的鏡頭語言,其小說的個性化語言特征很難得到體現。因此,如果是從故事內容的表達與轉化而言,電影鏡頭語言是否能夠做到、如何做到以及應不應該照搬原著來力求做到,這些本就存在于從小說到電影改編過程中所面臨的技術性難題,尚且還有可處理的余地,但是,對于一位以文字本身的風格獨特性而著稱的作家來說,其電影改編后一定會使其原有文字韻味受到極大影響。人物對話部分的語言還可以照搬使用,盡量保有原作特色,但描寫性語言則會無法在電影中再現。除非以旁白形式呈現,但這樣會對電影整體的藝術效果產生一定影響。在《永別了,武器》結尾,亨利在凱瑟琳死后,將護士們趕出了病房,但卻“關了門、滅了燈,也沒有什么好處。那簡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別”。簡潔的語言,通過對行動的描寫,來表達內心的無奈與悲涼。但是,這種情感,很難通過影像語言以表演的方式傳遞給觀眾。因為,從影像符號到可被直觀理解的思想與情感符號,尚需要中間更復雜認知環節的協助,而語言符號,則可直達內心深處。因此,對于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而言,敘事符號存在不可轉換的可能性。正如在文本翻譯的過程中所必然遇到的“不可譯”情況一樣,中國古代詩歌在被翻譯成外國語言后,其詩歌本身所具有的韻律及音樂節奏幾乎所剩無幾。也就是說,在小說到電影的改編過程中,故事性內容是否可以被鏡頭語言這種新敘事媒介再次呈現,有賴于新技術的創新使用,而文體風格特征則會隨著語言符號在電影藝術中作用的弱化而變淡,甚至消失。
三、意識流手法的影像符號表達
對于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而言,意識流寫作手法因為關注人物的心理描寫與內心感受,在以鏡頭語言符號為敘事手段的電影中很難體現。具有精湛演技的演員可以運用自己豐富的表情、眼神等變化來詮釋人物角色的心理活動,但僅限于前后對比差異明顯的心理狀況。也就是說,通過眼神、表情符號甚至行為動作等肢體語言可以表達內心情感的某種變化,或是簡單的心理內容,但是卻很難或者無法去表述復雜以及長時間的內心想法。除非仍然選擇用畫外音、旁白等形式進行技術加持。作為一位“精通現代敘事藝術”的文體大師,海明威在其短篇小說《乞力馬扎羅的雪》中,運用了大量的意識流和內心獨白技巧,來表達喪失活動能力的主人公哈利面臨死亡威脅時的內心豐富的思想活動[7]。小說《乞力馬扎羅的雪》分別于1952年和2005年進行了電影版的改編。在1952年版的改編電影中,主人公哈利的結局有了很大的改動,他并沒有死去,而是被飛機救走。這樣一個圓滿的結局似乎能夠讓觀眾回避原作小說中讀者不得不面臨的死亡終局。但是,如果僅僅是復制了小說中的部分相關情節,而將其結局進行了逆轉式的改寫,這必然是對海明威小說原作主題的一種淡化與削弱。那么,被削弱了主題的電影,其思想深度是否還和海明威這樣一位世界級文豪的文學地位相匹配,是否還能代表海明威的藝術水平? 是不是電影版的《乞力馬扎羅的雪》只能在版權方面才可以與其原著產生關聯呢?
對于小說中意識流與內心獨白手法所產生的敘事問題,電影中是如何進行解決處理的呢?《乞力馬扎羅的雪》描繪了一個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的悲劇,通過真實的意識流展現了主人公的迷惘、沉淪、掙扎以及一步步走向毀滅的全過程。影片以完整情節劇的形式出現,也就是說影片已經人為地割裂掉原著中的活潑意識流動,也就是說意識流被主觀去掉,并搭建起獨特的框體敘事結構[8]。那么,存在的問題就是,在進行電影改編之前,是否需要思考小說中為什么要用內心獨白和意識流手法,并將思考的結果作為改編電影需要進行考量的重要元素。美國心理學之父、機能主義心理學派創始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于1890年在其重要著作《心理學原理》一書中提出意識流這一概念,后被應用于文學領域。法國意識流文學先驅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將其應用于著作《追憶似水年華》中。普魯斯特運用“冰山”理論就意識流進行了闡釋,他把意識行為看成是海中“冰山”,即處在海平面以下、看不清楚的那一部分冰山,也就是意識流小說要表現的是朦朧不清的無意識[9]。在小說《乞力馬扎羅的雪》中,主人公哈利因為在非洲染病即將不治身亡,在其瀕臨死亡之際,大腦中除了生理性的困頓外,進而產生的精神上的極度壓抑,令其反復出現時空錯亂的回憶性畫面。意識流手法恰到好處地描述了人類在面臨死亡之際所呈現的一種規律性反應。而將這種反應進行細膩而真實的描繪,對于探討死亡主題,進而解釋人生與命運的波折與坎坷,無異于是極為適合的。但是,如果在影片中基于技術性的轉換難題而將這一困頓與混亂的思想活動進行回避,轉而訴諸于安排合理的時間線與完善的故事情節,則將失去對原著小說所載主題意義的表達及其內在的悲劇性。而沒有了主題的深刻性,改編后的電影必然失去了海明威的特色風格,進而流于平庸。以此可以看出,意識流手法的影像符號轉換,始終是小說電影改編所要面臨的難題。
四、結語
總之,小說的電影改編活動,涉及諸多因素之間的聯系與比較。海明威小說的電影改編歷經坎坷,為文學界與電影藝術界均留下了豐富的思考空間。作為后工業化時代的藝術發展過程中所需探索的目標,將海明威小說的電影改編納入符號敘事學視閾下進行分析與闡釋,并在敘事語言符號的轉換、跨媒介應用及心理敘事符號的創新方面開展探討,有利于深化對文學與電影敘事規律的研究,進而可進一步揭示符號的敘事原理。
參考文獻
[1] 愛·茂萊,聞谷.歐內斯特·海明威小說中的電影化結構和改編問題[J].世界電影,1984(2).
[2] 范革新.海明威·斯泰因·塞尚——探海明威語言藝術的形成[J].外國文學,1997(3).
[3] 張曉花.海明威“冰山原則”下的小說創作風格[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1).
[4] 韋朝暉.論《永別了,武器》電影改編的創新性[J].電影評介,2017(13).
[5] 孫致禮,周曄.交織在敘述語言中的戰爭與愛情——海明威《永別了,武器》重譯有感[J].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9(2).
[6] (美)海明威著,林疑今譯.永別了,武器[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
[7] 孫華祥.從《乞力馬扎羅的雪》看海明威的文體風格[J].外國文學研究,1999(1).
[8] 孫玉林.小說改編電影:《乞力馬扎羅的雪》[J].電影文學,2015(22).
[9] 魏曉紅.意識流、內心獨白與小說人物心理描寫[J].小說評論,2009(S1).
(特約編輯 范 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