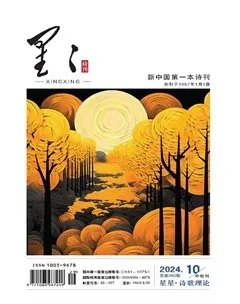百年中國新詩的編年史圖景
自古以來,與中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繁盛相呼應(yīng)的,是綿延不絕的選本編纂傳統(tǒng)。從孔子刪《詩》這個意義上來講,刪定的《詩經(jīng)》即為選本,足以垂范后世。選本促成文學(xué)傳播的展開與作家作品的經(jīng)典化歷程,這對于當(dāng)代的文學(xué)選本來說仍然適用。新文學(xué)誕生后不久,中國的新文學(xué)選本也隨之問世。在功能、體例、特點等方面,新文學(xué)選本與古代文學(xué)選本有一脈相承之處,但也發(fā)展出新的類型、產(chǎn)生新的特質(zhì)。文學(xué)年選是進入現(xiàn)代才出現(xiàn)的選本類型,其突出特點是對文學(xué)發(fā)展的逐年把握與同一時間段不同文學(xué)地理空間的審視,從而實現(xiàn)文學(xué)編年史的建構(gòu),而新詩年選又是文學(xué)年選中最早出現(xiàn)的分支,百年年選展現(xiàn)的是中國新詩百年來的變化與發(fā)展。
新詩年選的誕生及其背景
1917年2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八首白話詩,展示了中國新詩與新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實績。1920年1月,第一部新詩選本問世了,這就是新詩社編輯部編的《新詩集(第一編)》。此后隨著新詩創(chuàng)作進入初步的繁盛期,大量詩作問世,詩集也陸續(xù)出版,新詩選本編選的條件更為成熟。1922年8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北社編選的《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這是中國新詩史上最早的年度詩選,也是中國現(xiàn)代第一部文學(xué)年選。
《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以其選詩嚴謹、點評精當(dāng)而在當(dāng)時就得到朱自清、阿英等人的贊賞,深受讀者歡迎,到1929年4月已出至第五版。當(dāng)代學(xué)者對這部選本也十分重視,相關(guān)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主要是圍繞其編選、點評和詩歌史意識而展開,而關(guān)于這部選本本身作為“年選”的特點與意義還缺少探討。
《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的編者“北社同人”在該書《弁言》開篇即說:“北社是個讀書團體,是個鑒賞文藝的團體,毫無取乎發(fā)泄。我們廣集新詩固不無采風(fēng)之意,而為受用實占一半。賞鑒之余,隨其所好而為批評,也是很尋常的。”他們并沒有解釋這本年選創(chuàng)意的來源,但以年為單位,顯然是年鑒的思路,同時《一九一九年詩壇略紀》一文又具有年鑒“年度大事記”的意味。
由此來看,《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作為年度詩選的出現(xiàn)并非偶然,應(yīng)該與當(dāng)時年選出版的時代背景有關(guān),而早期的年選與年鑒又往往是混同的,年選應(yīng)當(dāng)是從年鑒發(fā)展而來。一般認為,年鑒源于古代的歷書,16世紀形成,現(xiàn)代意義上的年鑒于19世紀由歐洲傳入中國。1867年創(chuàng)辦于美國的《世界年鑒》,1868年創(chuàng)辦于英國的《惠特克年鑒》都在世界上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中國古代就有編年體史書《春秋》,方志編纂也十分興盛,形成了與西方不同的傳統(tǒng)。“年鑒”一詞,作為文獻名稱最早出現(xiàn)于宋代。1909年奉天圖書館出版的《新譯世界統(tǒng)計年鑒》,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以“年鑒”為名、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年鑒。到20世紀初,文藝年鑒/年選逐步規(guī)范化,同時對中國文藝界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正是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問世的,但是,作為一部中國新文學(xué)年選,它并不是對西方同類著作的機械照搬,而是進行了具有本土化意味的開創(chuàng):
一是“選”的理念。《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打破了《新詩集(第一編)》等早期選本“寫實”“寫景”“寫意”“寫情”的四分法,代之“以‘詩人’為中心的編選體例”,實際將“抒情”作為詩歌的內(nèi)在特質(zhì),于是“有關(guān)‘詩’的構(gòu)想隨之轉(zhuǎn)換,從對‘更多經(jīng)驗’的向往到‘純?nèi)问闱椤略姟蜗蟊阍诂F(xiàn)代‘詩’觀念中得到了某種‘純化’”。
二是評語。這部選本得到后來研究者的肯定,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認為它是將中國古代評點方式與現(xiàn)代文學(xué)觀念相結(jié)合的典范。姜濤在《“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fā)生》中對這些評語進行了分類:第一類是“隨意寫下的閱讀感受,或是印象式的風(fēng)格把握,或是對詩的主題、背景作簡要評述,在評價上沒有鮮明的傾向性,目的都在為讀者提供‘閱讀’的門徑”;第二類是“側(cè)重于‘新詩’特殊品質(zhì)的解說,推重具體、清新等新的美學(xué)可能”;第三類是“在與古典詩歌或外來資源的比較中,尋求‘新詩’的價值定位”。評語以中國古典傳統(tǒng)為參照,是要“幫助讀者辨識新詩的價值”,同時借用傳統(tǒng)以維護“新詩歷史合法性”。
三是建構(gòu)出一部早期新詩史。早期新詩選本中胡適的詩作入選最多,《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也不例外,但它更是明確地以胡適串起一部中國新詩史:1.評語中的詩歌史意識,將胡適定為中國新詩的首倡者;2.《一九一九年詩壇略紀》對新詩歷史與發(fā)展的追溯,分為兩條線索:一條線索是以遠古歌謠作為白話詩的源頭,延伸到1916年最早作白話詩的胡適,再到1917年沈尹默《月夜》成為“第一首散文詩而備具新詩的美德”,最后是1919年周作人的《小河》,“新詩乃正式成立”;另一條線索是新詩的傳播,從《新青年》首發(fā)新詩,到《新潮》《每周評論》,再到五四運動后新詩“風(fēng)行于海內(nèi)外的報章雜志”。可見年選選擇1919年這個時間點,實際上是把它視為新詩創(chuàng)立的標(biāo)志。
年度選本編纂的四次熱潮
1933年8月10日,《中國文藝年鑒(第一回)》由現(xiàn)代書局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藝年鑒,也是第一部綜合性的文學(xué)年選。但由于編者作為“現(xiàn)代派”,對自身大加吹捧而貶低他者,因而招致左翼陣營的猛烈抨擊。魯迅對此予以辛辣的嘲諷:“那篇《鳥瞰》把與現(xiàn)代書局出版物有關(guān)的人都寫得很好,其他的人則多被抹殺。而且還假冒別人寫文章來吹捧自己。”
茅盾也發(fā)文批評,在他看來,該年鑒稱1932年的中國文壇“衰落”是“根本錯誤的”,以《現(xiàn)代》雜志創(chuàng)刊為“文壇恢復(fù)”的紀元也是毫無道理的,對文藝的性質(zhì)、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失當(dāng),資料搜集與整理粗疏不全。中國詩歌會的蒲風(fēng)則將批評的火力集中于詩歌部分。《鳥瞰》把詩壇分成了三派:象征詩派、新月詩派和新興階級詩派,給予的評價也依次遞減,在象征詩派中最看重戴望舒,認為施蟄存以“意象抒情詩”而獨具特色。可見編者是以戴望舒與施蟄存為1932年度詩壇的代表的。但在蒲風(fēng)看來,編者無視革命詩歌的蓬勃發(fā)展,現(xiàn)代派的趣味太過濃厚,年鑒中大部分都是自己圈子里的詩人,如戴望舒五篇、施蟄存三篇、李金發(fā)兩篇,“簡直可以說是現(xiàn)代書局的現(xiàn)代月刊的詩選了”。以郭沫若為羅曼詩人的代表,年鑒選了一首《牧歌》,但是“較有時代意識的一篇都不中選”。在蒲風(fēng)看來,年鑒中所選詩作境界狹小、意象陳舊、脫離時代,形式上的追求充滿了小資產(chǎn)階級的趣味;新興詩人的作品也未曾選入,這都是對大眾的欺騙。現(xiàn)代書局版的《中國文藝年鑒》只出了一本,此后北新書局出版了楊晉豪所編的1934、1935、1936年度《中國文藝年鑒》。楊晉豪顯然注意到先前年鑒的問題,極為關(guān)注文學(xué)與時代、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他對年度文學(xué)主潮的把握和概括是十分精準(zhǔn)的,如《1934年中國文藝年鑒》注意到“戰(zhàn)爭小說的常有發(fā)表”“幽默閑適的風(fēng)行一時”“小品文字的極度興盛”;《1935年中國文藝年鑒》則指出“生活傳記的蓬勃一時”“報告文學(xué)的滋生”“反帝情緒的高漲”等;《1936年度中國文藝年鑒》則有“新現(xiàn)實主義的傾向”“國防主題的把握”“戲劇的高潮”“詩歌的特盛”等。選錄的詩人有卞之琳、李金發(fā)、林徽因、臧克家、戴望舒、路易士、金克木、蒲風(fēng)、亞丁、田間、姚蓬子等,兼容并包。總體上看,1930年代的這幾部文藝年鑒,既參與當(dāng)時的文藝論爭,同時也是當(dāng)時文藝論爭的產(chǎn)物。“七七事變”爆發(fā)后,文學(xué)年鑒被迫終止,但文學(xué)年選卻仍有出版,如誼社編選的《第一年》《第二年》,展示了1938年、1939年涌現(xiàn)的抗戰(zhàn)題材作品。此后文學(xué)年選也陷于停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文學(xué)年選重新啟動,最突出的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發(fā)起并于1956—1959年出版的四部選本:《詩選》(1953.9—1955.12)、《詩選》(1956)、《詩選》(1957)和《詩選》(1958)。這四部年選都是當(dāng)時出版的年選叢書中的一種,展現(xiàn)了新中國文藝建設(shè)取得的偉大成就。陳宗俊在《“十七年”詩歌隊伍的分化與重組》中認為,四部年選體現(xiàn)出五個方面的特點:一是解放區(qū)詩人更受重視和肯定;二是青年詩人、工農(nóng)兵詩人成為主力;三是少數(shù)民族詩人被納入;四是“五四”詩人的消隱;五是一批“超級作者”的存在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這些方面,其實在四部詩選的序言中也得到了揭示。四篇序言的作者分別是袁水拍、臧克家(1956、1957年選本序言)、徐遲。袁水拍強調(diào)“典型形象”的創(chuàng)造,而要創(chuàng)造這樣的形象,詩人就必須使自己高尚起來,“詩人只能是一個革命者,一個共產(chǎn)主義的戰(zhàn)士”,這是當(dāng)時文藝界面臨的首要任務(wù)。臧克家從他維護的“五四”精神出發(fā),注意到“詩的意境不完美”的突出問題,提出郭沫若正是“抓住了‘五四’的時代精神,寫出了那些輝煌的詩篇”。徐遲在民歌運動的背景下展開,宣稱“新詩的發(fā)展,已經(jīng)有了明確的方針,這便是在民歌和古典詩歌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的方針”。凡此種種,都顯示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經(jīng)過改造、洗禮與重組,詩壇的秩序已基本上確立。
新時期以來年度詩選再度恢復(fù),首先就是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編的《1980年新詩年編》(1981年出版),其次是《詩刊》社1982年編選的《1979—1980詩選》。此外還有呂進、毛翰主編的《中國詩歌年鑒》(始于1993卷)、安徽文藝出版社自1985年編選的年度《全國詩歌報刊集萃》等。《1981年詩選》的編選者對年度詩選的功能與特點也有自覺的認識:“它應(yīng)是新詩史中的一個橫斷面,盡可能反映出新詩創(chuàng)作在這一年的概貌,有一定的史料性;同時力求成為可資作者借鑒和足堪讀者欣賞的一個較好的讀本。”年度選本由此需要確立這樣的編選標(biāo)準(zhǔn):外部標(biāo)準(zhǔn)是“1.盡可能反映出這一年內(nèi)我們社會生活的重大方面,如農(nóng)村新貌、城市改革等;2.盡可能反映出新詩創(chuàng)作在這一年的實際成就和普遍趨勢,如各種形式、體裁、風(fēng)格等量的統(tǒng)計;3.盡可能反映出有別于往年的特點,如新人和‘新作’”;內(nèi)部標(biāo)準(zhǔn)則是“好詩”。
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年度編選由于文學(xué)被邊緣化、難以適應(yīng)市場經(jīng)濟大潮的沖擊等原因而被中斷。
新世紀年選與中國詩歌的跨世紀發(fā)展
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斷的詩歌年選又一次得到接續(xù),并在新世紀之初展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興盛態(tài)勢。1999年1月,長江文藝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新詩年選,即“中國年度文學(xué)作品精選叢書”中的《1997年中國詩歌精選》。此后各類年選也紛紛出現(xiàn),如楊克主編的《中國新詩年鑒》、遼寧人民出版社的“太陽鳥文學(xué)年選”、漓江出版社的“漓江年選”、春風(fēng)文藝出版社推出的“21世紀中國文學(xué)大系”、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花城年選”、《星星》詩刊社編選的“中國年度詩歌精選”“中國年度散文詩精選”等,一時蔚為大觀。
世紀之交的文學(xué)年選,看上去是以往年度選本浪潮的回歸,但里面其實有不少的差異。一個重要差別體現(xiàn)在前者更講究經(jīng)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贏”,在運作上呈現(xiàn)出新的特點。如漓江詩歌年選一開始就是漓江出版社與《詩刊》社“合作出版”的,“合作”一詞意味著以往的編選格局與方式被打破,出版方、編選方是雙向選擇的關(guān)系,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資源優(yōu)化配置、攜手合作,致力于圖書品牌的打造。
與新世紀詩歌的多元化一樣,新世紀的詩歌年選也是氣象萬千、多元呈現(xiàn),但從縱向的時間軸看,各家年度選本關(guān)注的問題是比較接近的:
1997—2000年度選本:世紀末詩歌的多元化格局;
2001年度選本:新世紀詩歌展望;70后開始崛起;網(wǎng)絡(luò)開始對詩歌生態(tài)產(chǎn)生影響;
2002—2003年度選本:新詩仍在平穩(wěn)發(fā)展;公開刊物與民刊出現(xiàn)合流,網(wǎng)絡(luò)平臺進一步興盛;港臺詩歌受到關(guān)注;對敘事泛濫的警覺;
2004—2007年度選本:新詩出現(xiàn)回暖、升溫;網(wǎng)絡(luò)詩歌迅猛發(fā)展;80后、女性詩歌、文化地理、底層寫作成為熱門話題;
2008年度選本:地震詩潮與寫作倫理的討論;90后嶄露頭角;
2009年度選本:網(wǎng)絡(luò)詩歌影響擴大,公開刊物、民刊、網(wǎng)絡(luò)的界限打破;
2010年度選本:新世紀詩歌十年總結(jié);
2011—2014年度選本:詩歌向抒情回歸;00后受到關(guān)注;
2015年度選本:余秀華事件,詩歌事件再度成為公共話題;
2016—2018年度選本:新詩百年回顧與未來展望。
2019—2020年度選本:新世紀詩歌二十年總結(jié)。
雖然年選具有編年史建構(gòu)的特點,但各選本在同一年關(guān)注的話題未必全然相同,即使是同一問題,各選本的觀點與立場也會有所區(qū)別。下面以幾個話題為例進行分析:
(一)新詩年度總結(jié)。例如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局之年,《2002—2003中國詩歌年選》的編者王光明認為,期待新世紀新一年到來時就遇到全新的詩歌是不現(xiàn)實的,新世紀初的詩歌,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詩歌探索的延續(xù):仍然在城市化、世俗化的語境中走向邊緣化;仍然是一種轉(zhuǎn)型的、反省的、過渡性的寫作,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仍然具有疏離‘重大題材’與公共主題的傾向,以個人意識、感受力的解放和趣味的豐富性見長,而不以思想的廣闊、境界的深遠引人注目。這是一個有好詩人、好作品卻缺乏大詩人和偉大作品的年頭”,但這也許是詩歌在自身應(yīng)有的位置上展現(xiàn)真實自我的機緣。
不少新詩年選還有序言或后記,這樣的文章形式靈活、風(fēng)格多樣,或是年度綜述,或是專題研討,還有理論批評闡述、作品舉例細讀等,正如梁平在主編《中國2013年度詩歌精選》時所指出的,“年度梳理的意義在于,我們可以在年度創(chuàng)作中發(fā)現(xiàn)它的‘意外’和‘新鮮’”,刺激和挑戰(zhàn)詩人的慣性寫作,從而警醒詩人 。該文指出,60后、70后詩人仍是詩歌現(xiàn)場主力,城市書寫的興起、詩壇的活躍、批評的介入等,都是對中國新詩年度狀況的總結(jié),宏觀而精準(zhǔn)。
(二)新詩百年回顧。選本在對年度狀況進行微觀探察時,也注重宏觀把握,但也存在一定的困難:一方面,各家對新詩百年的時間點存有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年度選本是對當(dāng)年度詩歌的梳理,即使是“百年”,對于年度詩選來說也只是一個年度、一個時間點而已,而新詩百年卻是對新詩史的總體性回顧,所以要開掘這個交匯點的意義并不容易。
事實確實如此。張清華是以胡適寫作《蝴蝶》的1916年算起,他在2015年度的詩歌中能發(fā)現(xiàn)佳作,但他也感到“從一百年的尺度看,寫得好的詩歌就不能以這樣的一種常態(tài)尺度來衡量。我們所能夠著眼的,便應(yīng)該是那些更具有體積、硬度以及陌生感和實驗性的文本,而這恰恰是一本年選詩集所難以體現(xiàn)的”。
當(dāng)然,百年新詩的時間節(jié)點是可以與年度編選結(jié)合起來的。《2017中國新詩年鑒》專門把第一卷設(shè)為“向百年新詩致敬”專輯。漓江詩歌年選在1999年進入第二十個年頭,特意將選本二十年融入新詩百年:這個選本“所涉及的這二十年,是百年中國新詩發(fā)展的一個新階段”,即第三次高潮。漓江年選由此極大地提升了年度選本的意義。
(三)新世紀詩歌十年、二十年總結(jié)。陳思和用“先鋒”與“常態(tài)”概括新文學(xué)的發(fā)展?fàn)顟B(tài)。他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文學(xué)處于“常態(tài)”,至2010年仍然如此,但文學(xué)此時“真正完成了文學(xué)與生活的新關(guān)系,那就是在邊緣立場上進行自身的完善和發(fā)展”。
這樣一個總體判斷同樣適用于新詩,燎原就是用“常規(guī)化”來概括這個詩歌時代。不少選家也是如此看待新世紀十年的新詩。韓作榮在2009年選用“被遮蔽的寫作”來概括當(dāng)時的詩界狀態(tài);宗仁發(fā)認為十年來的詩歌“越來越呈現(xiàn)出多面性、雙重性和矛盾性的特征”,同時長詩的創(chuàng)作顯示出值得注意的特色。
到2020年,對二十年來的新世紀詩歌又需要有一個回望與總結(jié)。《文學(xué)報》特邀評論家何言宏主持“文化工作坊”欄目,張清華做了題為《“新世紀詩歌二十年”的幾個關(guān)鍵詞》的主題報告。他提出新詩的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五四”的“詩體大解放”;第二次是“新時期”的“朦朧詩”時代;第三次解放“是一個大眾文化時代,大眾傳媒時代的顯形”。張清華概括了這二十年新詩的特點:1.“極端寫作”的彰顯和先鋒寫作的終結(jié);2.“文學(xué)地理的細化”;3.“寫作的碎片化、材料化或者未完成性”。可以看出,“第三次解放”的說法為新世紀詩歌作了定位,值得重視。
此外,年選活動日益豐富與多元化,紙質(zhì)出版之外,網(wǎng)站、微博、微信公眾號、App等構(gòu)成的電子網(wǎng)絡(luò)空間更是成為詩歌編選的重要平臺。詩歌選本也不再限于單一的紙本印刷物,而是融紙本、音頻、視頻、圖像等于一體的立體文化產(chǎn)品。詩歌編選形式更為多樣,除了傳統(tǒng)的讀詩選詩,還與朗誦會(詩會)、評獎頒獎、發(fā)布會、詩歌節(jié)等諸種活動打包,成為一場文化盛宴。如《星星》詩刊社舉辦“星星年度詩歌獎”“星星大學(xué)生詩歌夏令營”“星星年度詩歌精選”,漓江出版社舉辦“年選系列”圖書出版二十周年研討會、設(shè)立“漓江年選文學(xué)獎”等,都具有相當(dāng)大的影響力。這些活動不僅進一步推動了新詩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也起到了優(yōu)中選優(yōu)、促成經(jīng)典化的重要作用,年度選本也被打造成為知名的文化品牌。
因此,作為有著較長歷史、在20世紀末又重新興起的年度詩選,其本身發(fā)展的歷史也是中國新詩發(fā)展的一個縮影,有重要的意義,也存在自身的問題。但是它們對于中國新詩的創(chuàng)作、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以編年史的形式展現(xiàn)了中國新詩的百年歷程,需要加以充分關(guān)注。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中國文學(xué)‘選本學(xué)’研究”(項目批準(zhǔn)號:23&ZD28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