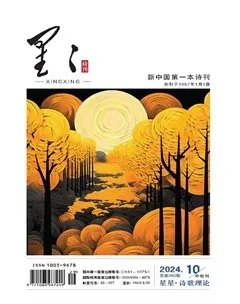民間·音樂·當代性
有人說,或許詩歌死了。那個校園里夾著雪萊詩集,在白楊樹下背誦拜倫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在去中心化的年代,人們熱衷于地鐵里的網絡小說;而沽名者故作驚人之語,或灑口水,或添穢語,以博揚名立萬。
但又或許,詩歌還沒死。北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堅持開設詩歌課程,因為“只有詩歌能讓我們的舌頭得救”;余秀華的詩集賣出了驚人的二十多萬冊;“讀首詩再睡覺”公眾號,溫暖的讀詩聲音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2011年,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拿下諾貝爾文學獎……
詩歌不死。鮑勃·迪倫在2016年拿下了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在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中創造了新的詩歌形式”。一時眾聲喧嘩,市聲鼎沸,不少人大嘆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純文學”不再。這種質疑的聲音今天依舊存在,然而,我不這么認為。在我看來,詩歌與公共生活聯結的可能,那就是民間、音樂、當代性。
一 詩需要與民間相聯結
詩歌與公共生活聯結的可能就是將詩歌與民間相聯結,與最廣大的土壤相聯結。
在1990年代的詩歌論爭中,“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兩派爆發了激烈的論爭。兩者都言之成理,但我們不妨超越這兩者之間的二元對立,走向“知識分子”與“民間”的辯證統一:“民間寫作”需要“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從而提升超越性,“知識分子”何嘗不需要“民間”來接地氣?在詩歌寫作日益走向學院化、技術化的今天,多一些“民間”的氣息,詩歌方能取得更為深厚的倫理力量。在最偉大的詩人杜甫那里,“知識分子”和“民間”從來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學者劉奎也指出:“詩人應走出書齋或公寓,面向中國內陸,面向廣大的鄉鎮和農村,觀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心理變化和感覺結構的變化等。這個時代要求詩歌不僅要面向自身的審美形式進行創新,也要面向大地和民眾,詩歌應重啟‘興觀群怨’的詩教功能。”
這啟示我們,在新時代,詩人需要多一些泥土氣息,從而令自己的寫作更為開闊。在這個意義上,王單單的《花鹿坪手記》,王計兵的《趕時間的人》,陳年喜的《炸裂志》,都是值得閱讀的詩集。他們的寫作并不是“半空中跳舞”的凌空蹈虛之詞,而是“貼著粗糙的地面運行”(維特根斯坦語)的真誠之作。可以說,他們的寫作植入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鄉村泥土和都市水泥,走出了一條先鋒之路。
當然,“民間”的立場并不意味著詩人需要放棄語言的錘煉,更不意味著需要放逐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詩人、散文家布羅茨基說過:“我想說的是作為人類語言的最高級形式,詩不僅是表述人類經驗的最簡潔的方式,而且它還為任何語言活動尤其是書面語言提供最高的標準。”誠哉斯言,詩歌的手藝是樸實的,與民間的手藝人有可比之處,那就是類似于木匠、鐵匠、鐘表匠等匠人的手藝所具有結實、渾樸、牢靠的品質。當然,這種結實的語言是需要飽嘗漢語之甜與生存之苦才能達到的,而不是把自己關進象牙塔之中得到的。與此同時,詩語的錘煉當然不止于語言,而應朝向精神的標高,朝向“人文關懷”與“審美救贖”的美學眼光與詩學追求。誠如昌耀所言,“我投向雪朝而口誦潔白之所蘊含”。
二 “詩”需要與“歌”相聯結
在鮑勃·迪倫獲得諾獎之后,曾有不少聲音質疑鮑勃·迪倫作為歌手的文學嚴肅性。但從作品來看,譜成歌曲傳唱,更提升了他的文學表現力。他的詩與歌合一,精煉、優美、飽滿,富含韻律,酸甜合度,像一籃新摘的煙臺瑪瑙櫻桃,像富含水分的綠樹。更何況追溯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唐詩、宋詞、元曲都是要唱的。阿城先生說:“唐詩與世俗其實緊密相連,就像現在的卡拉OK,通俗歌詞,生氣勃勃。”宋人筆記也說:“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這個“歌”字極其要緊,請想想,鄰里鄉親,少男少女,一起唱起柳詞,豈不妙哉。元曲更是通俗,句句押韻,深入人心。直追更古,《詩經》也是歌——詩與歌,本血脈相連,扎根在生活的泥土里,就在蝸牛的對門。它是感動人的,如顧隨所說的“興發感動”。荷爾德林寫道:“人/充滿勞績/但還是/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詩歌的源流本來便是豐富的生活。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
是的,詩在“歌詠”中流傳。古典詩詞之所以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離不開音樂性的存在。從小時候開始,筆者就覺得那些“聲依永,律和聲”的詩詞特別能讓人記住。整齊的聲律有著和諧的美感。“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一首五言絕句,平仄合度,四句中有三句押韻,對一個孩子來說,這種音樂性有著特殊的魔力。到了大學,學習了“四聲八病”等知識后,筆者的體會更深了。“大珠小珠落玉盤”,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聲律的微妙變化沉淀著復雜細致的感情,更沉淀著中華文明的文化底蘊。在吟誦時,每個字詞都有它獨特的質感與重量,每個韻腳都像一壺沉醉了古今的酒。今人鄧麗君,也有一張專輯《淡淡幽情》,其將唐詩宋詞唱成一曲曲款款深情的流行歌曲,卓絕獨拔的字句如三月細雨般滲透人心——中秋之時,總會響起她的《但愿人長久》,那深婉綿邈的聲音中浮現了蘇軾的詩心;而獨處之時,獨自聽她的《獨上西樓》,那空靈蘊藉的歌唱更是飽含著李后主細膩深沉的靈魂……漫步在她的“詩與歌”中,古典的真情與雅韻如五月流泉般汩汩而出,沿著唐宋的大河一直流淌到心間。
那些我們口口相傳的現代詩,也十分注重音樂性。譬如吟誦一首戴望舒的《雨巷》,悠長的韻腳流淌著輾轉纏綿的情致與婉約清揚的聲韻之美,拼音里流轉著千里江南;再譬如朗誦一首郭沫若的《鳳凰涅槃》,結尾那“我們歡唱,我們翱翔。我們翱翔,我們歡唱……只有歡唱!只有歡唱!歡唱!歡唱!歡唱”所體現的慷慨激昂、大風飛揚的氣概,留給讀者深刻的印象。1980年代詩歌中膾炙人口的詩句莫不具有很強的音樂性,比如這樣的句子:“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顧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北島);“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海子)。
這些名句,以其動人的韻律膾炙人口,在知識界與民間流傳。這告訴我們,新詩需要與“歌”相聯結。余光中的《鄉愁四韻》也是這樣的。它被羅大佑譜成曲,歌吟神州。“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酒一樣的長江水/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這樣回環往復、沉郁頓挫的詩句,正是要在反復的吟唱中方能體現其雋永詩味,方能體現其韻律之美,方能表現其脈脈深情。當然,如李章斌《“韻”之離散:關于當代中國詩歌韻律的一種觀察》一文所言,1990年代以來的當代詩歌存在“韻律”“聲音”之個體化、多元化的趨勢,以及由此帶來的讀者接受的難題。這與社會文化的多元化、讀者-作者同質性文化群體的崩散有關系。而這從世界范圍來看,卻是一個普遍的趨勢。但是,李章斌也提示我們:或許可以實現一種最低限度的“韻律學”,在一個“重”詩時代里讓詩歌變得稍許“輕”一些。
什么是一種最低限度的“韻律學”?或者說,什么是一種在多元化的當代社會中依舊可能的“韻律學”?在筆者看來,那就是讓“詩”的音樂性再強一點,乃至具有成為一首“歌”的可能。周云蓬所演唱的《九月》,唱出了海子的寥廓與蒼茫;程璧所演唱的《我喜歡一切不徹底的事物》《我想和你虛度時光》,也還原了原詩的精致。鮑勃·迪倫在20世紀60年代所告訴我們的,并沒有在21世紀失效:當代詩如果要與我們的公共生活有更為深刻的聯結,不能失去“歌”的維度。因為“詩”與“歌”如昌耀所言,永遠是金黃暮色中的月亮寶石,具有安頓人心的力量。
三 詩需要當代性
除了“民間”與“音樂性”,詩歌如果要與公共生活有著更緊密的聯結,需要具有當代性。那么,在我們這個21世紀,當代詩的寫作如何取得當代性呢?
首先,筆者以為這需要我們把握“新詩”之“新”,把傳統與現代更好地結合起來。在當下,傳統復興,但不免會帶來與現實脫節,乃至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弊病。而在新詩的“古典新詮”中,常見的問題就是將偉大的文學傳統塑造為一種神話,而忽略了古典與當代的關聯。在這種想象中,田園充滿了古典的詩情畫意,鄉村成為一種王維式的烏托邦,我們在其中感受不到任何時代的脈動與城市的氣息。這是當代詩寫作需要超越的話語裝置。我們需要超越平面化的村莊想象,書寫那些不可簡化的鄉野故事與都市心事。
傳統的活力在現代的語境中得以激活。我們在思考“傳統”的時候,必須要以一種清醒的“現代”意識加以審視,這是一個嚴肅的詩學任務。我們在書寫傳統時,需要擺脫那種自動生成詩意的想象路徑——頹廢而彌漫著煙水的逸樂六朝,與李白對飲的盛唐氣象,豁達天真的北宋東坡……這些文化符號背后的“現代性”何在?與我們當下的社會關聯何在?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問題。
回顧新詩的歷史脈絡,這在廢名的《談新詩》那里就已經有所申說。廢名認為,舊詩在于以詩的形式寫散文的內容,新詩在于以散文的形式寫詩的內容,“舊詩的內容是散文的,其詩的價值正因為它是散文的。新詩的內容則要是詩的,若同舊詩一樣是散文的內容,徒徒用白話來寫,名之曰新詩,反不成其為詩”。也就是說,《嘗試集》中的新詩雖是散文內容,但里頭確實有真正的詩的精神。新詩的要義在于靈感受當下的情景觸發,寫出一種靈魂的詩。其“當下性”與“直接性”是非常重要的。借用奚密的觀點,廢名的《街頭》之所以區別于李商隱的《樂游原》,正在于在“汽車”“PO”“郵筒”“號
首先,筆者以為這需要我們把握“新詩”之“新”,把傳統與現代更好地結合起來。在當下,傳統復興,但不免會帶來與現實脫節,乃至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弊病。而在新詩的“古典新詮”中,常見的問題就是將偉大的文學傳統塑造為一種神話,而忽略了古典與當代的關聯。在這種想象中,田園充滿了古典的詩情畫意,鄉村成為一種王維式的烏托邦,我們在其中感受不到任何時代的脈動與城市的氣息。這是當代詩寫作需要超越的話語裝置。我們需要超越平面化的村莊想象,書寫那些不可簡化的鄉野故事與都市心事。
傳統的活力在現代的語境中得以激活。我們在思考“傳統”的時候,必須要以一種清醒的“現代”意識加以審視,這是一個嚴肅的詩學任務。我們在書寫傳統時,需要擺脫那種自動生成詩意的想象路徑——頹廢而彌漫著煙水的逸樂六朝,與李白對飲的盛唐氣象,豁達天真的北宋東坡……這些文化符號背后的“現代性”何在?與我們當下的社會關聯何在?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問題。
回顧新詩的歷史脈絡,這在廢名的《談新詩》那里就已經有所申說。廢名認為,舊詩在于以詩的形式寫散文的內容,新詩在于以散文的形式寫詩的內容,“舊詩的內容是散文的,其詩的價值正因為它是散文的。新詩的內容則要是詩的,若同舊詩一樣是散文的內容,徒徒用白話來寫,名之曰新詩,反不成其為詩”。也就是說,《嘗試集》中的新詩雖是散文內容,但里頭確實有真正的詩的精神。新詩的要義在于靈感受當下的情景觸發,寫出一種靈魂的詩。其“當下性”與“直接性”是非常重要的。借用奚密的觀點,廢名的《街頭》之所以區別于李商隱的《樂游原》,正在于在“汽車”“PO”“郵筒”“號碼”這些現代都市體驗中所感受到的“人類的寂寞”。這需要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并不是第二個黃庭堅,而是屬于我們自己的當代人。當然,傳統也自有力量。當我們凝視幽暗的時候,歷代的星辰也向我們傳來足以擦亮晦暗的光芒。
其次,這需要我們從“語言中心主義”的神話中突圍,把語言的錘煉與當代生活的書寫更好地結合起來。在反思古典神話的同時,也需要反思當下詩學的“語言”神話:即處理“詞”與“物”的關系之中,呈現出精致化、個人化而遠離中國現實的癥候。詩人們以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的姿態,以膨脹的自我想象著一個個虛幻的、鏡花水月式的烏托邦。自足的語言營造出了一個個幻象。因此,朱朱同樣犀利地指出,處于邊緣位置的詩人“必須收起魯濱遜的傲慢”,也就是告別那種夸大“自我”的意志。
這和近期詩論家的討論是相近的:語言的技術主義若流于末端,則難以獲得生活的實感。姜濤在《從“蝴蝶”“天狗”說到當代詩的“籠子”》等文章中認為,張棗等先鋒詩人的寫作,陷入了柄谷行人所說的“現代文學”的“內面自我”之窠臼。先鋒詩人筆下的所謂“無辜自我”與“丑惡現實”的二元對立結構,其觀察現實的姿態其實是一種“看風景”的姿態,趨于令文本關進語言的“籠子”里。李章斌在《走出語言自造的神話》等文章中延伸了姜濤的觀點。他指出,受張棗的“元詩”論影響,當代詩在處理“詞”與“物”的關系時,不免呈現出“語言神話”與“自我中心主義”的癥候。而這會讓文本面臨“內卷化”,逐漸耗盡語言的勢能。因此,詩人要從“刺客”走向“人群”。
最后,這需要我們對當下的社會現實有更為深入的把握。關于“底層”的詩歌書寫時常容易出現這種癥候:作者站在知識分子的角度,以高高在上的啟蒙姿態,并非將底層打工人作為主體來寫,將底層客體化,導致過分地去渲染底層生活的黑暗,沒有寫出底層打工人豐厚的心靈。曾幾何時,藝術家們也通過賣弄固化的刻板印象來迎合一種東方主義的思維。在他們筆下,巨變的中國現實中那些對美、對自由、對愛的追求是失語的。人們仿佛只在呻吟,而沒有希望、夢想。在這種敘述中,詩歌的“超越性”就喪失了,那種“日常的沉醉與抒情”的想象也付之闕如了。然而,詩歌的任務正在于在書寫塵世的塵土的同時,把我們從庸常中超拔出來。
不賣弄苦難的詩歌應當走向何方?在我看來,面對現實之重時,詩歌應當如鳥兒一樣——舉重若輕。誠如朱朱所言,處于邊緣位置的詩人,需要像“沙鷗”一樣,成為一無所負的海鷗,“自在的滑翔”。這是對自由夢想的詩學做出的一個美妙的比喻。在他其他的詩句中也有類似的表述,“成群的大雁穿越過往的歲月,/回到一個不屬于任何年代的季節,起舞”。
李海鵬指出,這種通過對鳥類的比喻來凸顯詩學倫理的寫作,是當代詩中一個常見的譜系。面對“邊緣”的危機,在歐陽江河和陳東東那里,詩歌是從葉芝學來的“天鵝”——高貴的歌吟,一種超驗式的語言本體論的神話;在西渡那里,詩歌則是玉淵潭公園中的“野鴨”,一種即便“邊緣”,依舊能面向公共空間的、充滿倫理溫度的姿態。從領受“天鵝”到領養“野鴨”,詩歌逐漸在地,但依舊能夠飛翔。到朱朱那里,這種“野鴨”的姿態進一步拓展為一種“沙鷗”和“大雁”的想象。他告訴我們,詩歌需要做到的是,一種立足邊緣荒島,但依舊仰望公共星空的超越性。“就像有一架天文望遠鏡猛然將獵戶星推入心扉。”如是,詩歌成長為了一種真正雄健而輕盈的鳥,如前人所言:
“致命的仍是突圍。那最高的是/鳥。在下面就意味著仰起頭顱。”——張棗
“詩人們的真正傳記就像鳥類的傳記一樣。”——約瑟夫·布羅茨基
或許,試圖突圍的當代詩確實需要向鳥類學習。生活固然泥沙俱下,污泥濁水,但痛苦深處還有歡樂與希望,罪惡之下仍有真正的潔白。這需要我們像鳥兒一樣,以飛翔的力量給予詩歌高遠的超越性。
結 語
2023年5月,一些富有批評勇氣的詩人與詩評家,如一行、王東東、張偉棟等人展開了一場以“當代詩歌的困境與危機”為主題的專題研討。在會上,有學者認為當代詩已經陷入了“絕境”。譬如一行以“當代詩的絕境與危難”為題的發言認為:“當代詩的絕境”的形成,不僅來自當下詩歌體制的壓抑和保守化,而且與1990年代以來中國詩學理論缺乏創造性更新關系密切。討論眾聲喧嘩,也引起了許多爭鳴。在筆者看來,這種思考很好地提醒了我們當代詩所面臨的困境。
是的,我們的寫作也需要從粗糲的民間中獲取力量,多一點音樂性的表達,多一點當代性的氣息。具體來說,把個體與共同體連接起來,把青春與“青春中國”聯系起來,把日常生活與史詩年代連接起來,是當代詩的題中應有之義。當然,正如霍俊明所言,這必須是以真誠、詩性、語言和修辭的承擔為首要前提,即所謂的“詩性正義”。也就是說,我們歸根結底,既要把詞與生活連接起來,又要把詞與詞的血脈連接起來——用張棗的話來說,也就是“深入彼此,震悚花的血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