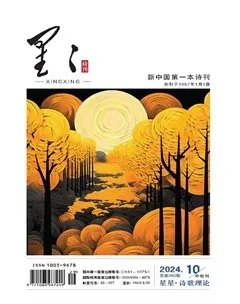“在場詩學”的歷史維度及當代性
張福超:孫老師您好,很高興您應邀此次訪談,您兼具批評家、文學史研究者、詩人、教育工作者等多重身份,不同面向和路徑的創作及研究在您這里是否發生過沖突?可否談談您的批評觀和文學史觀?
孫曉婭:好的,感謝《星星·詩歌理論》,也感謝你為此次訪談所做的準備。你提的這個問題始終伴隨我的學術生涯,在我看來,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并非具有排他性,它們可以呈現出互補互促的有機狀態。如何處理好理論、批評與史料、文本的關系,是充滿樂趣且具有無限可能的學術挑戰。我始終堅守一個觀念:詩歌批評是知識分子詩學理想的實踐方式,是學術肌理的詩意存在形態,是個性化的精神實踐行為,優秀的詩歌批評來源于真誠無偽的寫作姿態,從現象和文本批評中彰顯思想和藝術的多元融合。如果用一個詞概括我的批評觀,那就是在場詩學。不同于海德格爾所說的此在性與文學界通泛而談的在場,在場詩學側重于落地的批評闡釋,指涉見證性、當下性、闡釋性、建設性、引領性甚至是哲學性,是歷史和現實的在場,審美和批判的在場,質疑和創造的在場,介入和延異的在場,警惕和反思的在場,生命和人性的在場,認知和感受的在場,主體精神和社會生活的在場,共存性和獨特性的在場,回頭看與朝前看的在場……在場詩學的核心不停留于“此在”,在具體批評中我們可以從過去的作品中重新評估其當下的意義,從當下的作品中洞見到其歷史和時代的文學價值,也可以通過批評彌補作品的在場性。提出在場詩學旨在強化批評者的主觀能動性和介入性,提升批評效力,對詩歌現象和詩歌創作做出深入靈動且富有前瞻性的判斷,賦予詩歌內在的隱語無限的闡釋機會。
回到你提出的第二層次的問題,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始終互為影響和碰撞,文學史研究要具備歷史眼光和經典化能力,文學批評重在對文學創作和理論的參與性,我在批評中更為側重打通文學性研究的路徑,畢竟批評是基于文學性的批評而非根源或依賴于理論的批評。文學史研究更側重借由翔實的材料黏合歷史書寫的細節性,從浩繁的史料和作家作品中甄別具有經典化元素的文本進行研究,以自然時間為主線呈現文學發展的現象、歷史的偶然性及作家的個性或共性;對作家作品、文學社團、文學思潮經典化的篩選,不僅需要扎實的學術儲備,還要具備從歷史定評、權威定論中突圍出來并對時代做出總結和回應的能力。文學批評的動力機制則強調對研究對象內面的介入——凸顯研究主體的問題意識、審美取向、知識活力以及閱讀趣味,對作家作品具有及物的闡釋能力,從創作現象中提出理論或概念的能力等。二者之間的動態關聯體現為批評的目的不簡單停留于對文學的評價,還可以成為理解和構型文學的媒介,它們之間涌動著不斷變異的張力,彼此促成各自的發展。我將兩者的關聯性融匯于“中國女性詩歌史”這套叢書的撰寫之中,即側重在歷史視野中推進詩歌研究和創作的探索路徑,從文學史發展流脈客觀而全面地審視歷代女詩人在兩性復調的文壇中所處的歷史定位、獨特的創造力和文學貢獻,用詩性的語言消解文學史規范性敘述機制帶來的枯燥或艱澀,拆除程式化的研究范式給廣大讀者帶來的閱讀藩籬,努力做到既發揚詩歌史的完整性、客觀性、豐富性、學術性,又兼具普及性與可讀性。文學史研究為新詩批評提供了一個歷史語境,宏觀或微觀的歷史感也會自動校準文學批評或新詩批評的意義。“中國女性詩歌史”現代卷和當代卷的撰寫,雖然著意于批評的潛能,但這種潛能卻來源于長期的文學史研究,得益于對具體歷史語境的熟知。
另外,新詩批評與文學史研究在互相促進中豐富了在場詩學的歷史維度與學術面向。文學批評可以發掘并牽帶出更多值得深入探析的文學史議題,比如,我撰寫《詩的女神:中國女性詩歌史》(現代卷)過程中,在對20世紀20年代北平女作家、詩人的研究中,就從許廣平研究中發現了魯迅與一些青年詩人及散佚詩集的關聯,進而對《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中的相關注釋做出多處補正。同時,文學史研究可以拓寬詩歌批評的視野,是必不可少的學術積淀,詩歌批評可以磨礪和提升文學敏悟力和品鑒才情。
張福超:在您看來,優秀的詩歌評論應該具備哪些特質?詩歌評論與其他學術文類論文的關聯和異同是什么?
孫曉婭:觀點獨樹、貼合文本,思想有前瞻性或引領性,語言精準,詩學儲備深厚,形成了個性化的話語譜系和批評風格,這幾點,是我欣賞的詩歌評論不可或缺的素質。好的詩歌評論既有穿透文本和現實的力度,亦有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有效的寫作引導力,它可以體現出一個評論家的綜合創造力——審美感受力、理論駕馭力、思考力、判斷力、話語建構力等。評論家既可以從好作品中培養出“第一義”的批評勇氣和批評思想,生成烙印著個人氣息的“第一義”的批評力量,又可以從平凡作品中洞見和呈現出問題、現象及規律,提出思想和創作方面的警示。
張福超:在信息爆炸的新媒介年代,無論是紙質刊物還是網絡媒介,詩歌生產如火如荼,詩歌信息紛繁蕪雜。對您而言,什么樣的詩更具吸引力?好詩的標準是什么?當代詩壇急需什么樣的詩人?您在詩歌批評方面的“信條”是什么?
孫曉婭:那些具有濃厚的生活質感和現實穿透力的詩作對我更具吸引力。我比較看重詩作的“包容力”,諸如詩作是否能穿透日常生活的表象直抵心靈的內核,或超越自我而與他者建立起沉浸式的關聯;諸如雖然是寫給有限的少數人的,但是卻能在更廣泛的空間得到容納與共鳴等。
我們的詩壇不乏深刻地思考現實的“思想家”,然而,我們缺少超越想象、直擊生存真相的詩人,我們缺少富有氣魄與力度的足以戳穿現實和靈魂的虛假面紗的優秀詩作。我始終認為:作為詩人,修煉“怎樣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比精雕寫作的技巧重要得多。詩歌是詩人的生命,這不是盲目夸大詩歌的意義,而是指詩人能夠真實感覺到自己詩歌的聲音與特質就是他生命的聲音與特質,即詩歌找到了它的方向和恰切的語言、表達方式。浸染著創作主體生命感是好詩的前提,在此基礎上,這種生命感還應該秉承馬拉美所強調的“釋放出我們稱之為靈魂的那種飄逸散漫的東西”。詩歌的寫作體現著一種特殊的生命的快樂,好詩足以揭示出生命的秘密、創造快樂、疏解憂傷。
回到批評,我的詩歌批評“信條”就是保留知識分子的良知,秉持在場的詩歌精神,不斷充盈新詩批評的方法,完善當代詩歌批評的理論建設,形成當代漢詩批評話語體系。此外,詩歌本身超乎邏輯思維,那么鮮活而充滿生命力的詩歌批評就應多一些對話性和自由度,側重于詩性的喚醒和探詢。
張福超:您剛剛提及新近出版的學術專著《詩的女神:中國女性詩歌史》(現代卷),據我所知,您今年年底還將出版《漂往遠海:中國女性詩歌史》(當代卷)、《月滿西樓:中國女性詩歌史》(古代卷)。這套叢書引起詩壇廣泛關注,謝冕先生評價,“自有詩歌歷史以來歷史跨度最長、涉及詩人最多、對詩人的評價最熨帖也最深入的一部中國女性詩歌史。不僅是填補了歷史空缺的創新的著作,也是學術基礎深厚扎實的著作”;孫昌武教授認為,“就第一流的學術題目寫出了第一流的著作”;吳思敬教授肯定,“首次為中國女性詩歌構建了獨立的完整的學術譜系”,您可否談一談寫這幾部學術專著的初衷及學術心得?
孫曉婭:我一直關注女性文學和女性詩歌的研究,在很多年前就想撰寫一部中國現當代女性詩歌通史。美國批評家哈澤德·亞當斯曾說過,“在今日的批評活動中,最令人感到興奮的,莫過于女性書寫的重新發現,以及隨之而來對經典作品的過濾與精選”。如果我們想直接聽見女人的聲音,首先必須從女人的文學書寫入手,而詩歌是唯一貫通上古至今的文體。“女詩人”在古代西方并不多見,英文中的“女作家”通常指“女性小說家”,如簡·奧斯汀(Jane Austen)、夏絡蒂·勃朗特與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等人。西方傳統一向視寫詩為“神職”,女人因不具神職人員的資格,一直少有機會展露詩才。而中國不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的中國女作家幾乎千篇一律是女詩人。據《歷代婦女著作考》一書,明清兩代女作家有三千多人,明清結集出版的女詩人詩集至少兩千多本,明末清初這一百年間可以視作女性詩詞創作的一個興起階段,到了清中葉,女性文學發展進入了高潮階段,有數千部的詩歌選集登載了不計其數的女詩人作品。也就是說,從上古至今,中國女詩人及女性詩歌一直占據女性文學的“主流”地位。然而歷史上未見一部關于女性詩歌研究的論著,探入這一盲區,可以算作我撰寫這套叢書的初衷。
目前這套書分為古代卷、現代卷和當代卷,每一卷又可以獨立擴充體量,因未有任何可供參考的范例,過程充滿挑戰:一方面,研究文本浩繁,另一方面,我力爭采用一手資料,為歷史做一些材料方面的爬梳和整理。在具體研究中,我將在場式的詩學批評、歷史的文學研究與性別研究維度融合一體,由詩入史,寫作過程中的收獲和啟發遠超預期:可以近距離地感受這些女詩人幽微隱曲的喜悲思愁,捕捉才女們傳奇動蕩的人生軌跡,欣賞她們不受制于時代和世俗定義的絕代才華、卓然獨立的思想和持續的影響力,這對我而言不僅僅是學術上的精進,更是煥然一新的生命成長。除卻在撰寫中與這些優秀的女詩人產生情感的碰撞,現實中也常常會發生詩性的際遇,今年8月14日,當代卷第一章專題研究的詩人灰娃獲得第七屆“中坤國際詩歌獎”,其授獎詞恰巧由我來宣讀,當銀絲飄逸、側影俊逸的灰娃老師逐字逐句地說出“有些詩我寫得不滿意,以后還想繼續提高”時,我再次感受到學術使命的召喚,九十八歲的灰娃老師為“在場詩學”做出了一個生動的注解——生命與詩歌的在場,過去、此在和未來的在場,持續創新和不斷超越的在場……我是在場的傾聽者、參與者,也是備受感動者,這何嘗不是在場詩學的魅力所在!
張福超:非常敬佩您十年來篤定的初心和扎實的學術儲備,您如何評價“性別”在中國百年文學或文化演繹的不同階段所扮演的角色?
孫曉婭:這個問題僅一次訪談難以回答透徹,簡單說,我渴望通過性別研究拓展詩歌研究新的對象域和研究主線,把它作為新詩研究維度中情感轉向的一次挑戰,隨著研究的深入,我發現性別研究是存在古代性、現代性和當代性的。回溯古代文學,女性在文學史中長期處于失語狀態。“五四”以降,女性文學在小說、散文等文體中均取得杰出的創作實績,詩歌創作反而略遜。陳衡哲、冰心、石評梅、陸晶清、白薇、林徽因、方令孺、陳敬容、鄭敏等詩人,以異于男性的書寫形式,對女性詩歌創作主題做出了拓展與超越,擴大了女性詩歌的視野。然而,現代女性詩歌稀疏的存在并未改寫女性詩歌的邊緣化處境。到了20世紀80年代,舒婷、翟永明、伊蕾、王小妮等新一代“夏娃”的覺醒帶來當代女性詩歌書寫的集體裂變。這些各具性格魅力的女詩人既強調女性感知世界的獨特性,又注意展現男女共有的經驗書寫,更為包容并充滿對話的寫作趨勢代表了當代女性詩歌發展的開放向度。從性別視域考察,當代女詩人對女性經驗的書寫往往采取既不顛覆也不依附男權社會的表達策略,由此形成了與男性經驗并行發展的女性審美意識的書寫模式,這種類型的女性文本大大弱化了“性別對抗”的色彩,呈現出中性的、溫和的詩性言說策略。21世紀女性詩歌創作既是對20世紀女性詩歌書寫的承續,亦有堅定的悖逆、拆解和發展,走向更為多元化、個性化。
我是從牛漢研究、七月詩派研究走上學術道路的,因為逐漸發現性別研究的特殊意義及其突破既有文學史或詩歌史的重要性,學術志趣發生轉變。近些年我集中思考的學術問題可以借今天的采訪略陳一二:其一,兩千多年中國文學史隱藏著怎樣的女性詩寫邏輯;其二,在歷次中國社會文化大轉型中,女詩人是如何參與文化、文學等諸多方面的話語構建和文學書寫的;其三,女性詩歌的書寫與經典化歷程的交疊呈現出怎樣的發展線索,性別意義上的經典是如何在邊緣和中心間搖擺、滑動與漂移的;其四,女性詩歌話語與男性詩歌話語的重疊、沖突是怎樣發生,如何書寫,又以什么樣的姿態被文學史書寫的,等等。
張福超:我注意到您在幾年前就從事詩歌教育方面的課題,比如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視域下民國詩歌史料的整理與研究”結項時被評為“優秀”,可否談談您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推進。
孫曉婭:中國的“詩教”傳統是源遠流長的,古典的“詩教”觀核心在于儒家人格的培養、價值觀的塑造和審美能力的結合。近現代時期,教育卻成為一項與國家民族命運息息相關的公共事業,中國新詩或文學教育在廣義層面上也參與到了近代中國整體文化格局的演變。換而言之,新詩作為一種“知識”進入教育場域,以講義、課堂、報刊、社團為媒介,依托校園文化生態,催生出詩歌的審美新編。新詩是在新舊各種力量的競合中發生的,以教育視野關照中國現代詩歌發生與演變的歷史過程,有助于啟發我們打破線性進化論式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重新認識中國新詩的現代性特征。我做這個項目,根本動因是嘗試突破中國新詩史的框架,將中國現代新詩放置于民國教育場域中進行再研究,同時,打破“詩教”話題的邊界,使其成為透視時代場域的一個共鳴器,旨在發現和提出一些新問題,踐行在場的學術研究。
在精耕細作的研究中,我發現新詩批評是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它就像一個十字路口一樣,匯通起新詩和教育的各個通道,它是一種橋梁,也是一個熔爐。民國時期的新詩批評與新詩教育在本質上是相通的,都是一種情感教育,是一種審美教育,是美育的一部分。研究中,我把不同高校的課程設置、師資建設、“校園內外”“課堂上下”的多種現象和獨特性整理、匯聚和再現出來,以期完整地呈現新詩教育與新詩文體建設是如何被建構的,試圖還原這一動態而豐富的歷史圖景。相關書稿《庠序有詩音:中國新詩教育研究》已經交付給商務印書館,正三校中,計劃2025年1月出版。
張福超:期待能夠早日讀到這部研究民國時期新詩教育的著作,由此我也想聽聽您對當下大學新詩教育的思考,比如,您二十年間始終負責在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的“駐校詩人制度”,近些年,全國高校作家駐校日益風靡,您是否有相關經驗分享?
孫曉婭:相較小說、散文、戲劇,詩歌最難展開教學。詩歌教學除卻詩歌史的講授,更應側重喚醒、啟發和感悟。在這一過程中,感受力是至關重要的。亦如穆木天在《譚詩》中所說,詩是內在生命的反射,詩的世界是潛在意識的世界。敏銳的感受力可幫助詩人發現、發掘生活中細微的潛在意識和內在生命,這是詩與散文、小說、戲劇最大的不同之處。引導學生進行詩歌創作,最便捷的路徑就是從詩歌欣賞入手,新詩教學起于鑒賞,作為教師,首要任務是講清鑒賞的層次,早在1931年,梁宗岱就做過透辟闡釋:“一首好的詩最低限度要讓我們感到作者底匠心,令我們驚佩他底藝術手腕。再上去便要令我們感到這首詩有存在底必要,是有需要而作的,無論是外界底壓迫或激發,或是內心生活底成熟與充溢,換句話說,就是令我們感到它底生命。再上去便是令我們感到它底生命而忘記了——我們可以說埋沒了——作者的匠心。”從初級寫作訓練開始——尋找恰切的語言、表達方式等入手,到感悟詩歌是“心靈作品”——詩歌的韻律節奏對應著心靈的律動,詩歌是對心靈的記錄,詩歌給了心靈一種最為合身的形式,生命的感受在這種可實現的轉換中獲得,這一體悟過程需要教師的引導。教師還應該帶領學生領悟詩歌的神秘魅力,讓學生體會到詩歌創作帶給個體的精微的快樂,激勵他們自覺于語言的表達,自由發揮新詩內在“自由”的精神。嘗試突圍個人的創造力是我在詩歌教學中從未間斷的實踐。
回到你提及的駐校詩人制度,截至目前,首師大培養了有江非、路也、李小洛、李輕松、邰筐、阿毛、王夫剛、徐俊國、宋曉杰、楊方、慕白、馮娜、王單單、張二棍、燈燈、祝立根、林珊、談驍、呂達、侯存豐、龍少共計二十一位優秀的青年詩人,打通了學院內外,將詩人、批評家、學生有機聯絡調動起來,不僅開創了中國的詩人培養機制,也真正聯動起詩歌批評、詩歌教育、詩歌創作的現場,給詩壇提供了很多彌足珍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