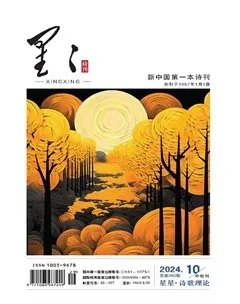孤獨與恐懼的畫布
預 感
[奧]里爾克
我像一面旗幟被空曠包圍,
我感到陣陣來風,我必須承受;
下面的一切還沒有動靜:
門輕關,煙囪無聲;
窗不動,塵土還很重。
我認出風暴而激動如大海。
我舒展開來又卷縮回去,
我掙脫自身,獨自
置身于偉大的風暴中。
(北島 譯)
——選自北島《時間的玫瑰》,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
《預感》一詩寫于1904年,而在1902年,里爾克便對沃爾普斯韋德(Worpswede)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將物視為與人和語言相陌生、相疏離的某種事物”。移居巴黎之后,他對視覺藝術的興趣有增無減,在與雕塑家羅丹和畫家塞尚的交往中,逐漸完成了詩歌藝術實踐的轉型。他意識到雕塑隔絕于世界之外,也獨立于實踐之外,石頭這一“物”(Ding)中含有永恒的神圣性。1907年,里爾克發表了《新詩》,其中的“物詩”集中體現了這一時期他從視覺藝術中獲得的觀看世界的方式。《預感》后來被收入《圖像集》,這本詩集中,里爾克試圖利用“圖像”固定詩歌的結構,并從早期的浪漫主義風格向帶有象征意味的“物詩”轉型。
這首詩代入“旗幟”的視角,以“我”的口吻,寫出了風中旗幟的感受。“我像一面旗幟被空曠包圍”,盡管詩人描繪的是飄揚在空中的旗幟,但被動式的使用和“包圍”一詞,讓原本的“空曠”頓失,而陡增被束縛、不自由之感。“空曠”也被賦予了實體性,變成了可觸摸可感知的有形之物——風。“我感到陣陣來風,我必須承受”,其中“必須”再次強調“我”逃無可逃,加深了第一句詩帶來的不自由感。“承受”的對象不是陣陣來風,而是還未到來的風暴,“我”只能在原地等待未知的審判。詩歌表面寫旗幟,實際上寫面對“預感”的恐懼。“恐懼”是里爾克詩歌經驗中的一個母題,他幼時經歷了父母的爭吵,青少年時期又被父親送入軍事學校,軍校生活給他留下了恐怖的回憶。里爾克曾在書信中說:“巴黎對于我來說是一段與軍事學校類似的經歷。在軍事學校時期,我被一種強大的驚恐所攫取;現在我仿佛處在一種無法言說的混亂之中,再次被那個被稱作生命的東西所驚嚇。”所以,詩中的“我”知道將要發生什么,卻無法躲避,也無法言語,只能靜靜地看向周WTE/rzqR8J9d+dEjodF1Zg==圍:“下面的一切還沒有動靜:/門輕關,煙囪無聲;/窗不動,塵土還很重。”詩歌營造了立體的空間,上方的旗幟和下方的建筑遙相呼應,高與低、動與靜的對比凸顯出風暴來臨前的寧靜,形成張力。“一切還沒有動靜”,不僅描述下方沒有動靜,也暗示下方的事物沒有意識到即將到來的風暴。“預感”在旗幟和下方事物身上再次形成反差,旗幟已經在“忍受”,而門在悠然合攏,煙囪安靜地沉睡,窗戶巋然不動,塵土靜靜地躺在地上。此句詩直接寫物并間接寫人類的活動,門窗、煙囪和塵土因為缺少人類的活動而尤為平靜,連續幾個意象的疊用快速鋪設出具體的場景,像用語言做畫筆在畫布上作畫。
詩歌的第二節在時間上延續到風暴來臨,從“認出”到“置身”,精細地呈現風暴從出現到席卷而過的整個過程。“激動如大海”“舒展開來又卷縮回去”,寫旗幟在風暴中迎接命運,原本的“預感”應驗,恐懼化作了孤獨。“孤獨”是里爾克詩歌的又一重要母題,他曾在《致青年詩人的十封信》中說:“我們需要的只是:寂寞,廣大的內心的寂寞。”他認為“孤獨”是詩人的養分,只有面對孤獨,詩人才可以窺視神性,審視內在的秩序。在另一首同樣被收入《圖像集》的代表作《秋日》中,里爾克寫道:“誰此時沒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誰,此時孤獨,就永遠孤獨,/就醒來,讀書,寫長長的信,/在林蔭路上不停地,/徘徊。落葉紛飛。”詩人用富有畫面感的動詞,將孤獨寫得極美又極悠然。和普遍認為孤獨需要忍耐和承受的觀念不同,里爾克詩中的孤獨也帶有一種自由和安寧。回到《預感》中,“我掙脫自身”“置身于偉大的風暴中”,旗幟最后將自身和風暴融為一體,是孤獨的,也是偉大的。“掙脫”這一動詞在里爾克1902年的詩作《秋》中也有類似的呈現:“而在這些夜晚,沉重的地球/脫離所有星辰墜入孤獨。”與之不同的是,《預感》中的孤獨是從“預感”階段就開始呈現的,在“下面”的人和物對未來無動于衷的時候,有預感的旗幟便是極其孤獨的,當風暴來臨的時候,更是勇敢地享受著孤獨。
20世紀初里爾克對視覺藝術的興趣與研究促使“物詩”風格的形成,“物詩”在重視外部的觀察和描繪的同時,也注重內外部的統一、聯合與均衡。通過視覺上對“物”的精確描述,讓詩歌更多地和日常經驗產生聯系,并凸顯其內在的精神。里爾克在對現實的表現之上,將自身的精神力量注入“物”中,并賦予其“繪畫性的特質”。正如《預感》,既客觀地寫旗幟孤零零地在風中飄揚的圖畫,同時標題也包含著“物”的視角下的主觀感受——一種夾雜著恐懼與期待的情緒,一種懸而未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