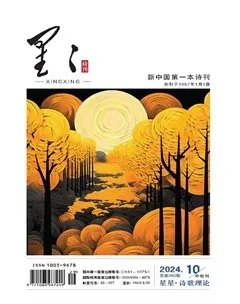海子在1987年的詩學轉變
秋
海 子
用我們橫陳于地的骸骨
在沙灘上寫下:青春。然后背起衰老的父親
時日漫長 方向中斷
動物般的恐懼充塞著我們的詩歌
誰的聲音能抵達秋之子夜 長久喧響
掩蓋我們橫陳于地上的骸骨——
秋已來臨。
沒有絲毫的寬恕和溫情:秋已來臨
——選自海子《海子詩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23頁。
“秋天”是海子詩歌中常見的意象之一。尤其是在1987年,在那一年的秋天,海子接連寫下《秋日山谷》、《秋天》、《秋日黃昏》、《秋》(共兩首,即“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鷹在集合”與“用我們橫陳于地的骸骨”)、《秋日想起春天的痛苦 也想起雷鋒》等多首以“秋天”為主題的抒情短詩。按學界公認的觀點:正是在1987年,海子詩歌由“大地烏托邦”的抒情短詩階段轉向歌頌太陽的現代史詩階段,前后階段詩歌風格的變化也使“秋天”這一意象的具體含義發生了轉變。這種轉變不是突發式的,而具有其內部的發生機制,有著物象上的連接點與意象上的遞進性。或許可以認為,正是由于海子意識到農耕文明及其所代表的傳統精神家園無可挽回的喪失,才使他對秋天的文化蘊含了更為縱深的考量。自此,海子在詩歌中使用“秋天”這一意象時,便從單純地象征“荒涼人世”轉向為表述一種“價值慰藉”。
“秋天”在中國文學中有著漫長的象征史。自宋玉在《九辯》中寫道,“悲哉,秋之為氣也”,便開啟了中國文人悲秋的傳統。文人在面對秋天時,因植被的衰敗、氣候的轉冷、日長的變短等自然環境的變化,而聯想到自身命運的近況,或感時傷世,或仕途沉浮……總之,哀嘆生命的萎縮與命運的跌宕。海子寫秋天,雖繼承了傳統文人所書寫秋天的感傷色彩與蕭瑟氛圍,但避免了哀嘆個人命運的自憐心態。海子所寫的秋天沒有從個別生命體的衰敗入手,而是寫豐收過后荒涼的大地。由此,秋天荒涼破敗的意味則更濃一分,這不是個別村落的黯然,而是整個人世的荒涼,是整個農業文明社會的破敗。“果實沉落桶底/發出悶悶聲響/讓鐮刀平放/豐收的草原”(《秋天》),而在這之后則是,“豐收之后荒涼的大地/人們取走了一年的收成/取走了糧食騎走了馬”(《黑夜的獻詩》)。在海子看來,農業文明的破敗是由工業化造成的。按照農業國的發展路徑,擁有原始的物質積累,實現對土地資源的充分利用之后,下一步驟便是實現工業化。而海子站在精神故鄉的這個維度,在《詩學:一份提綱》中寫道:“由于喪失了土地,這些現代的漂泊無依的靈魂必須尋找一種替代品——那就是欲望,膚淺的欲望。”工業社會中利益與物質之刺激便成了支撐人類精神世界的搖搖欲墜的一節假肢。也是在此意義上,海子的詩歌被視作農業文明的最后一支挽歌,其內核是對工業社會的一種現代性反思,在1987年以降,更是對這反思的再一次反思。海子寫于1987年8月的詩歌《秋》便是此種反思之反思的文字成果。
在海子詩歌類型轉變的1987年,他多次寫到秋天,不再是單純地感傷“荒涼人世”,或是延續一種傳統的價值形態與審美性格,而是通過“秋天”這一主題更為憐憫、更為沉重地審視生命的整個存在形態與人類生存的諸種樣式。海子筆下的“秋”既是物質實體性的,更是象征性的。首行“用我們橫陳于地的骸骨”延續了秋天的荒涼感,又彌漫出生命毀滅的濃郁的悲傷氣氛。“在沙灘上寫下:青春。然后背起衰老的父親”,記述了人類生命的三個重要階段:青年、中年、老年(死亡)。在沙灘上寫字所代表的青春有多么炙熱,速至的衰老與骸骨就有多么恐怖,生命的美好與毀滅形成的劇烈沖突被置于短短的一行詩中。“動物般的恐懼充塞著我們的詩歌”,海子想象人類個體在面對生命的速朽與死亡時,是無比恐懼的,與動物毫無差別。而人要從動物的序列中掙脫出來,只能依賴于“我們的詩歌”。在海子看來,詩歌是農業文明與生命存在消亡過程中唯一能起到關懷作用的慰藉品,詩歌可以緩解時間消逝所帶來的恐懼,也能儲存生命各個生存階段的信息。
“誰的聲音能抵達秋之子夜 長久喧響”,子夜連接著今天與明天,也連接著黑夜與黎明。在生命的無奈循環中,海子自視為子夜中清醒的人,在人類存在消亡之后,在人類精神被欲望侵占之后,他長久歌唱;他替人類發出的悲憫,詩歌中展現的終極關懷,長久鳴響。在另一首《秋》中,海子更加直接地坦白:“秋天深了,王在寫詩。”海子愿為子夜里獨唱的歌者,愿做秋天深處寫詩的王。在他的心中,詩歌是最后的盾牌、最后的陣地、最后的旗幟……這“最后”代表了孤獨,也代表了悲涼。他正是在砥礪自己關注和珍視人類生命與存在的決絕誓言下,“掩蓋我們橫陳于地上的骸骨”,作為最后的收尾,作為最后的慰藉。
海子喜歡在詩歌結構上設置一些對立,在某一對立面的局部使用反復的技法,通過這樣的技藝設置來表現一些思維與觀念的延展過程。作為主題的“秋天”終于出現了,“秋已來臨。/沒有絲毫的寬恕和溫情:秋已來臨”。它在時間序列上早于“秋天深了”,但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對土地的最后一絲憧憬也消散了。秋天或是深秋,再也無法掩蓋人類精神世界走向越來越貧瘠的現狀,同時,也暗示著是時候了,詩人要憑借著詩歌的精神力量,來擺脫對土地的最后一次烏托邦幻想,以走向對人類存在的更為高懸的關懷。那是詩人視野上的仰望,去追尋太陽的光熱,獲得普照性質的神性。“秋已來臨……秋已來臨”,這“來臨”如此急迫地催促著,它也暗示了海子無法逆轉的詩歌風格、思想觀念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