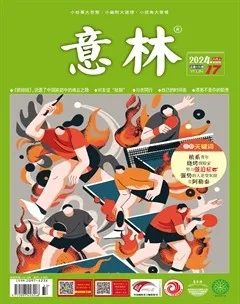我,“985”工科女轉行做廚師
一個人選擇成為廚師的故事本不應該有什么特殊的,但如果加上一系列修飾語——“‘985’名校生”“建筑系轉行”“海外留學”“‘95后’女生”,或許應該再加上“在被男性統治的充滿野蠻、汗水、油煙的后廚里”——這個故事就很難不變得激動人心。今年28歲的崔迪就是這個故事的主角,她來自新疆,是上海兩家融合菜餐廳的主廚。一路走來并不順遂,崔迪到底經歷了什么?
以下是崔迪的自述。
一個女孩子為什么要做廚師
上大學的時候,我看了動畫片《中華小當家》。主角是一個13歲的中華少年,他說想要做出讓人信服的料理,這也是我做菜的初衷。同濟大學一直有“吃在同濟”的說法,每年都有“廚神爭霸”大賽。我覺得很好玩,每年都報名參加,第一年沒進決賽,后兩年都得了冠軍。
第一次參賽之前,我沒怎么做過飯,只能在宿舍里開小灶。那時候燒的菜比較簡單,可樂雞翅、大阪燒……做完就和室友一起吃,如果大家覺得好吃,我也會很開心。當時,我覺得自己也許可以嘗試把廚師當作職業,就去學校附近的餐廳兼職,體驗一下真正的后廚工作是什么樣的。
當初報考同濟大學建筑學院的風景園林設計專業,是因為我在網上看到這個專業的介紹,說它是用人類所知道的生物學、地理學等方面的知識,讓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我以為這個專業就是種種樹,我還挺喜歡動植物的。其實做菜也一樣,去了解食材的特性,對它們進行一些“解剖”和“重置”,最后它們變成美食。大學畢業前夕,我本想升校內的研究生,但沒有拿到名額,便想去法國學廚師。但這個決定被家人阻止了,我爸說,讀了本科再去讀專科不合理,一個女孩子為什么要做廚師?我媽卻說,如果你真的喜歡、能夠堅持做下去也是可以的。
最后,我們都做了妥協,我先去瑞士讀酒店管理的研究生,再找機會學廚藝。

在瑞士讀研,有很長的實習時間。我在米其林網頁上把瑞士的餐廳投了個遍,最后面試上了比利時一家二星餐廳。通過面試的那天晚上,我連洗澡時都在傻笑。
在比利時的日子很純粹,也很封閉。后廚里只有我一個女生,而且是亞洲人。每天起床到上班大概只有15分鐘,每天工作14小時以上。
那時,我經歷了廚師生涯里最難挨的時光。有時候會不小心割傷自己,有時候則因為食物過敏渾身又腫又癢,此外,還要忍受同事的嫌棄和冷暴力。
2020年,我開始了正式的廚師工作。法餐后廚極度講究等級秩序,更別說餐廳里來一個女生。西餐后廚對于體力要求沒有那么高,反而耐心、細致的女生會更有優勢。中餐館后廚對女生來說相對更難。
我記得當時去一家中餐廳面試,負責人把我帶到后廚,把廚房的燃氣灶和抽油煙機打開,整個廚房“呼呼呼”地響,聲音很大。他說:“你來掂一下這口鍋。鍋里需要裝滿水,把它掂平,穩住15秒。”就算對男性來說,也很需要力氣。他想讓我知難而退。
顛勺是中餐后廚的基本功,既靠技術又靠體力。大家下班后,我就加班練習顛勺。
如何審視“學歷浪費”這件事
入行時,我24歲,當時實習的比利時餐廳檔口的負責人才21歲。
24歲對于從廚來說已經很老了。有時候會覺得我繞了好遠的路才走到這里,也有人說我學完建筑再去當廚師是“學歷浪費”。
但仔細想,每一步都沒有浪費。記得剛投遞實習簡歷的時候,那家比利時餐廳官網上主廚介紹中的一句話,深深擊中了我:“我一直以來想成為建筑師,于是我在盤子里搭建我的作品。”
主廚設計的菜品里,也有風景園林設計的思維:biotope(群落生境)、aqua(水)、flora(植物群)、fauna(動物群)。我當時忍不住驚呼:果然,建筑和烹飪是相通的!
風景園林設計專業教會了我設計的思維,我覺得這也是我能這么快成為主廚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廚師來說,怎么設計一道菜是需要自己領悟的,它沒有具體的方法論。廚師需要的,除了審美,還有你對不同風味、不同食材的組合。比如,西餐里面會做很多蔬菜泥,也會做很多脆片,它們搭配在一起,是一種質地的碰撞,脆的東西和很滑的東西混在一起,會產生變化和復雜的口感。雖然風味不一樣,但兩種食材搭配起來必須有共同點。比如,小雞燉蘑菇,雞和蘑菇的共同點是鮮味。但我對食材沒有設限,怎么組合都可以,只要做出來好吃。
現在來看,我好像是幸運的。很多人會來問我轉行的經驗。我的從廚之路其實很坎坷,留學花了30萬元,回國后的第一份廚師工作,月工資只有5500元。后來想去中餐后廚,卻總被勸退。疫情防控期間,餐廳不營業,工資幾乎沒有,每個月還要交房租,我只好先找了一份美食編輯的工作。即便這樣,做了選擇之后,我就不會再去對比。
所以,比起尋找什么是熱門的,跟風報專業,對我來說,了解自己、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情更重要。因為真正的熱愛是不會背叛你的,它會跟著你一直走下去。
為什么有人總覺得做廚師不如做建筑師,其實大家不是很愿意說自己的志向是做一個服務人員。在瑞士讀酒店管理專業時,老師跟我們說,服務也是一門需要智慧的學問。作為廚師,我覺得能通過自己的創造,讓別人覺得好吃,這很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