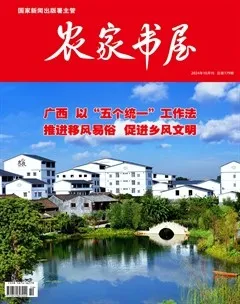《尋秦跡:透過秦俑看秦朝》: 希望更多人和我赴一場千年之約

1989年,我成為秦始皇帝陵兵馬俑坑考古隊的一員,從三號坑開始“蹲坑”,隨后又參加了二號坑的發掘。2009年,一號坑第三次發掘開始,我從三號坑時期的“跟班”成為了領隊,直到2014年轉場秦都咸陽城遺址,時間如白駒過隙,我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從事一線考古發掘歷時25年。
我所從事和熱愛的考古工作,在我心里,是一項享受了“特權”的工作。手下動一鏟,就是跨越千年,坐在探方邊,即享受與古人面對面的約會。這種精神上的富足和自豪,是無可替代的,就像我的同事趙震在《國家寶藏》節目中說的那樣:“我有天底下最好的工作。”
在兵馬俑坑工作的那些年,我每天按要求寫發掘日記,每年按要求寫兩篇以上的論文。這些文字面向的是文博同行,有專業語境的要求,對廣大公眾來說并不通俗易懂,所以更談不上生動有趣。
在很多場合,我都聽到關于秦始皇陵、關于兵馬俑、關于中國歷史的各種神乎其神的“傳奇”“忽悠”,此時我對種種“玄虛”的訛傳不由自主地產生了憤怒。“你為什么要憤怒?隔行如隔山,別人為什么要懂你們專業的知識,又怎么能了解你們專業的收獲?你有沒有將你們的真知識傳播出去?”在一次我和女兒申珅的交談中,她的一席話點醒了我。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說:考古是人民的事業。我希望自己能打破壁壘,跨界、出圈,把我的發現、所思、所感分享給對歷史文化感興趣的人們。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和古人對話,擺脫時空的束縛,感受歷史與文化的博大精深。除了枯燥乏味的學術性的發掘報告之外,我要把發掘的點滴積累下來,多和大家說說我們的發掘是怎么回事。千年之約不單單是考古人與過往面對面的事,也是中華兒女和我們的先人面對面的事,這兩件事都是我的分內事,更應該通過我相互連通起來。
在我開始做考古科普的時候,“無趣”“太專業”“沒意思”“聽不懂”這些詞匯一直縈繞在我耳邊,而自媒體的興起,也讓更多“玄虛”的以訛傳訛接觸到更多的受眾。我越來越能感覺到,準確、有趣、有效地傳播考古文博知識,是一件勢在必行且有點緊迫的事情。
我女兒十分支持我做考古科普,在某種程度上,她也是我的“指導老師”。因為從事博物館展覽策劃和博物館講解的工作經歷,她對公眾渴望知道的內容、喜聞樂見的講解形式都很了解。所以,從內容到形式上,她都在幫我把枯燥的專業知識形象化、趣味化、故事化,我在讀者和網友的留言中,不斷汲取有建設性的建議。
《尋秦跡》是我創作的第三本書,也是申珅和我合作的一本書。在這本書中,我除了繼續給公眾介紹兵馬俑的“三精”——“精心、精彩、精品”之外,也帶領公眾走進考古現場。我試圖用探案推理的方式,透過秦俑探討大秦帝國興衰,探討我們這片土地曾經是怎樣的氣象,發生過哪些大大小小的1c1dc9639062916657bd3473194f58ce事情。我也盡量展開說說考古工作的目的、考古人的工作日常、考古工作的規范等考古學科的知識。而申珅則擔當我與廣大讀者的“橋梁”,把我認為讀者“應該”知道的知識點、可能會覺得枯燥無趣的內容,進行知識延展、趣味解讀,甚至用很多年輕人一聽就懂的類比、“橋段”,來降低理解的難度,拉近古人和我們的距離,讓知識傳播更生動、好玩。
兵馬俑是大秦帝國軍隊、武力的象征。秦國的大一統,不只是秦始皇的雄才偉略,還有無數無名將士的不懈努力,他們前赴后繼,無畏生死,用鮮血締造出這樣一個大秦帝國。他們在為自己贏得軍功的同時,也讓自己的家人獲得了幸福生活,實現了自己的“大理想”,也結束了那個以戰爭命名的“戰國時代”。
武力征伐不代表秦文化,更不代表中華文明。要真正看懂兵馬俑,不能揪住秦始皇指揮千軍萬馬這個點大肆渲染,應該多去了解兵馬俑及兵器所體現的包容性、多元性,這才是秦文化更真實的面貌。人性共通,無論是 2000 多年前戰火紛飛的戰國時代,還是安定幸福的當下,古往今來,和平是人類永恒的主題。止戈為武,戰爭與和平駕馭著人類的歷史、文明滾滾向前。舞戈是為了止戈,這是秦始皇征伐六國的意義,是秦帝國建立的意義,是兵馬俑軍陣的意義。
我希望讀過《尋秦跡》的讀者,能夠通過兵馬俑,感受到滾滾向前的時代巨輪如何牽動著今年的你我,也能夠看到更多生活在那個時代的鮮活個體。只有在歷史深處看到和我們一樣熱氣騰騰地活著的人,我們的歷史才能鮮活,我們才能從歷史深處展望未來。
考古學從考古人走向大眾共享,是新時代的新要求和新景象。與“世界八大奇跡之一”這樣的稱謂相比,我更愿意用“文化遺產”來定義兵馬俑,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華優秀文明資源。我希望我能盡我的綿薄之力,為大家盡量講好這段中國故事,讓更多的人發現這些資源的價值。如果能夠利用這些文明資源,創造新的文化資源,那就再好不過了。
(來源: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