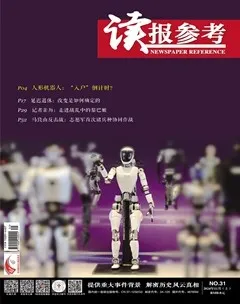從方寸簡牘解碼長江文化
“乙未父下席。己亥歸寧。甲辰父葬。”這是3枚竹簡上古人留下的記錄,黑色的毛筆字透著古樸韻味。
“‘下席’,是什么意思?”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簡帛研究中心主任、古文字與中華文明發展傳承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陳偉講解說,這3枚竹簡于湖北云夢睡虎地77號漢墓中沉睡2000余年之后,經考古發掘重見天日;其講述的是越人父親去世,他回家奔喪、安葬父親的一段日程;“下席”即“去世”。陳偉說,古書有的地方不好懂,有的注釋有問題;而出土的簡牘,在啟示古書解讀等方面展現出重要的學術價值。
“簡牘”,是指用于書寫的竹、木片,和寫在竹、木片上的文獻。與甲骨文、金文相比,簡牘的材料容易獲得,制作和書寫簡便,可編連成冊,承載卷帙浩繁的文獻。中國古代,在紙張普遍使用之前,簡牘是主要書寫載體,流行于戰國、秦漢至魏晉時代。
“自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約30萬枚。”陳偉介紹,不過,由于簡牘易損壞,墨跡易脫落,繩索出土時大都腐朽無存,使得簡牘的整理異常艱難;必須通過釋字、斷讀、綴合、編連等多個環節的縝密考訂和反復推敲,才能在文本復原和內涵解讀上,逐漸貼近古人書寫的真相。
陳偉說:“出土的簡牘中,3個省份數量最多,湖南約15萬枚,甘肅約6.5萬枚,湖北約3萬枚。長江中游可以說是我國簡牘出土最為密集的地區。”
經由一枚枚竹簡,我們可以領略這一“方寸之間”的記錄呈現出的長江文化密碼。陳偉介紹,在20世紀初期較長一段時間內,簡牘的出土地點限于西北一隅。1951-1953年,湖南長沙連續發現幾批楚簡,拉開了長江流域,同時也是我國內地簡牘出土的序幕。時至今日,我國大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均有簡牘出土。位于長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兩省,成為最重要的出土地區。
長江流域出土的簡牘,不僅數量眾多,且時代齊全、內容豐富、保存較好。
按時代先后,簡牘通常分為楚簡(即戰國中晚期楚國的簡冊)、秦簡牘(指戰國晚期秦國和秦代的簡牘)、漢簡牘、魏晉簡牘。陳偉介紹,楚簡、秦簡牘的出土區域均以湖北、湖南為主;漢簡牘、魏晉簡牘出土地點廣泛,但西漢早期的簡牘大多出自湖北。
從內容來看,簡牘分為書籍、文書與律令、遣冊、卜筮禱祠記錄四類。其中,書籍簡發現廣泛,但長江中游出土的品種最多;律令,可看作文書中的特別類型,大多出自湖北境內;卜筮禱祠記錄,是墓主人生前為公私事務或疾病進行占卜并準備禱祠的記載,僅見于楚簡。
從保存情況來看,湖北出土的簡牘中,除了在荊州高臺一口古井中出土了3枚楚簡外,其余主要出自墓葬。陳偉分析,這些簡牘是當時有意識的隨葬,加之地下水位高、水的酸堿度適宜,所以往往保存較好,經綴合、編連等專業處理,文本復原的完整度高,文獻價值也較高。
與湖北不同,湖南出土的簡牘中,只有少量出土自墓葬,大量均出土自水井中。“在古井中大量堆積簡牘,有些可能是有意識的行為。”陳偉分析,兩湖地區出土豐富、精彩的簡牘,與春秋時期以后當地經濟、文化發達有關,且具備適合簡牘保存的埋藏條件。
此外,大量的簡牘是曾經在當時中國普遍存在的文書、律令和書籍,是研究中華文明發展演進的重要史料。
出土簡冊中,包含大批久已失傳的古書。2006年出土自湖北云夢睡虎地77號漢墓的《算術》引人注目。據介紹,《算術》有216枚簡,出土時基本保持編連順序。算題涉及面較寬,包括田畝面積計算、體積計算、谷物兌換等。這是迄今所見保存最好的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算術文獻,對認識秦漢時期的算術科學具有重要價值。同時,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中的早期道家文獻《太一生水》、早期儒家文獻《性自命出》《六德》,湖北荊州王家嘴798號楚墓出土的竹簡樂譜等,“都前所未見,擴充了早期文獻資源”。
律令,是秦漢時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運行的重要制度支撐。但對秦漢律令的總體結構,學界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有學者甚至認為,當時只有一條一條制定的單行律,不存在國家頒布的統一法典。然而,近50年來,秦至西漢早期的律令一再出土,比如,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律、湖北江陵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和《漢律十六章》、湖南益陽兔子山木牘上的律章目錄、湖北荊州胡家草場漢律等。在湖北睡虎地秦簡、湖南里耶秦簡中,還有一些與律令有關的文書檔案。“從中我們可以了解西漢早期律典體系的基本面貌。”陳偉分析,比如總體呈現二分結構、全國統一施行等。
目前,一些先前出土的重要簡牘正在陸續整理、出版,如湖南湘鄉三眼井楚文書簡、湖北云夢睡虎地漢簡、南昌海昏侯墓簡牘等。與此同時,新簡牘還在不斷發現。“隨著簡牘資料的系統整理和解讀,對長江文化和中華文化的研究,必將持續取得新進展。”
(摘自《中國青年報》朱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