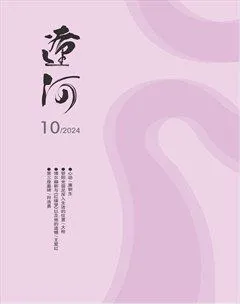初心接力
從京城重點大學畢業的林學碩士廖京州,風塵仆仆地奔赴沂蒙山區的莫家峪村,擔任了村黨支部書記助理。
初來乍到,征塵未洗,他迫不及待地走向了烈士陵園。
手捧花束的他,恭恭敬敬地三鞠躬后,深情地凝望著烈士雕像,眼睛禁不住濕潤了。
這對從未謀面的曾祖父與重孫子,此時此地相遇,注定是一場冥冥之中的接續。
八十多年前,十八歲的曾祖父廖興華在省立師范學校求學時,受工人運動和進步思想的影響,走上革命道路,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受黨組織派遣,他回到沂蒙山區開展地下革命活動。1938年1月,在日軍侵占朐城的前夜,他帶領十幾個青年參加了八路軍,后來擔任八路軍先遣大隊政委,區委書記兼武工隊政委。1941年11月,在反掃蕩斗爭中,為掩護機關和主力部隊轉移,他與敵人展開殊死搏斗,身中數彈,壯烈犧牲。
或許因為廖京州是聽著曾祖父的英雄事跡長大的,從懂事起,每次望見照片上曾祖父打著綁腿,挎著盒子槍,英姿勃發的英雄形象,他總是盯著看了又看,立志要做曾祖父那樣的人。
碩士畢業之初,他憑借著扎實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歷,先后收到幾份入職邀請函,可以留在京城或省城工作,可他卻執意報考選調生,并請求來到曾祖父戰斗過的地方工作。
他來村里報到前,盡管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但面臨的復雜情況,還是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近千人的村子是建檔立卡貧困村,村民大多靠種口糧田維持生活,建檔立卡貧困戶接近常住人口的一半。
村子窮,村兩委辦公的幾間簡易房,房頂蓋的石棉瓦已破爛不堪。他初來乍到,就在村支書騰出的辦公室——一間狹小昏暗的房子里住下了。
晚上,山村一片寂靜。
廖京州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白天在烈士陵園看到的一幕又浮現在眼前。“八路軍是魚,老百姓是水。”刻在曾祖父紀念碑上的這句話,如黃鐘大呂響徹在耳邊,他感到肩上的責任越發沉重。
次日,天不亮,他就起床,換下了皮鞋,穿上了跟村民一樣的解放鞋,開始熟悉村里的工作。
莫家峪村有七個村民組,村民分散居住在五平方公里的深山溝里,入戶走訪、熟悉村情民意,是他入村后的第一課。兩個月下來,他用雙腳把全村丈量了一遍,村里每戶的家庭情況,他都了如指掌。
走在田間地頭,他那被太陽曬得黝黑的臉龐和手臂,與土生土長的村里人沒兩樣。盡管大部分村民不知道他的身世,卻夸他是個好后生。耄耋的老人還把他比作當年的老書記,就是他的曾祖父,時常講起老書記帶領鄉親們打鬼子、保家鄉的事。
站在曾祖父當年帶領戰士鑿打的“八路井”邊,他不由得心潮澎湃,暗暗下定決心,賡續曾祖父未竟的事業,以所學專業知識助力脫貧攻堅,幫助莫家峪摘掉貧困村的帽子。
經過充分調研,他詳細分析了村里的優勢后,遞交了一份《以經濟林建設助力脫貧攻堅的規劃報告》,讓村兩委干部既驚嘆又佩服。
在他的建議下,村里推行合作社加農戶的經營模式,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那些日子,他忙得跟陀螺一樣,帶人外出學習考察,引進優質果樹苗,手把手教村民科學種植。山上缺水,他請來水利專家當顧問,開挖泉眼、修蓄水池、建攔水壩、鋪設管道;還修了盤山路,架線引電上山。后來,他索性吃住在山上,竟半年沒下過山。
幾年過去,村里相繼建成了花椒、油桃、中藥材種植基地,村民人人有活兒干,家家有錢賺,收入大幅提升,莫家峪村按期脫貧摘帽。
看到當年曾祖父不惜流血犧牲,執著追尋的“讓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的夢想終于變成現實,他欣喜地流淚了。
選調生期滿,癡心不改的他又續了一期。等到第二個任期期滿時,縣里要調他到團縣委任職。
誰料,他懇切地跟領導說:“我了解國家的產業政策,熟悉村情民意和產業結構,留下來能更好地發揮作用。”領導同意了他的選擇,他成為鎮黨委委員、副鎮長、村第一書記。
他又一次來到烈士陵園,隔著八十余年的時空,與曾祖父展開心靈對話,對其在危急關頭選擇留下來做掩護,有了更加切身的理解和感悟。
同樣的使命,不同的堅守。如今成為村民“主心骨”的他,正帶領村民在鄉村振興的新征程上闊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