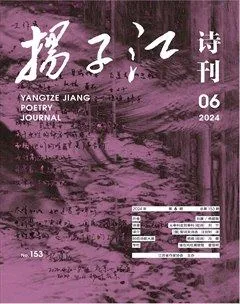一再地,終點往前流去
崖麗娟:自從我開始做詩人訪談就從不同渠道收到詩人朋友們的建議,詩人朱朱你是一定要訪談他的。可見您是一位很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詩人。我們先從一個宏觀問題開始:好詩的標準有哪些?談談對“新詩”的認識,初學者常犯的寫作錯誤應該如何規避?
朱朱:好詩的標準像一個看不見的球心從來沒有變過,變化的是各種不同的球面。“新詩”看似允諾了更多的自由,但也帶來了更多的無所適從,你需要為每一首詩找到一個特殊的、甚至專屬于它的形式感。也許是面對一個黑洞時產生的心理防御,最近十多年來我陷入了某種強迫癥,大多數的詩都保持各段落的行數均等,只有極少數例外。
有一些評論家朋友,譬如江弱水和李章斌,探討了新詩的韻律和音樂性。我有一首短詩《寄北》,在江弱水的建議下,去除了一個并不必需的字之后,通篇暗合了五韻步“素體詩”的漢語形式,這件事讓我很驚訝,它也許說明了:我們可以憑借自己的本能和內在聽覺印證什么,但合于韻律之道未必就意味著是一首好詩。
太多的詩歌以為自己是蚌殼孕育出的珍珠,其實只是泥沙般的情緒釋放或排泄。對于每個寫作的人而言,犯錯的過程是無法省略的,博爾赫斯說他犯過一個寫作者會犯的所有錯誤,至于我,每天都還在犯錯;寫詩不靠肌肉記憶,一個普遍適用的經驗是:對經典的閱讀或他人的建議固然重要,但只有自己真的意識到需要改變的時候,一個人才會做出改變。
崖麗娟:您大學時期就開始詩歌創作,能否介紹上世紀80年代大學校園詩歌活動的情況,還記得在哪里發表的第一首詩嗎?詩歌在哪些方面改變了您?
朱朱:記得當時上海的高校中,最活躍的是復旦和華師大的兩個詩社,地理位置上一東一西,我入學的時候,華東政法學院并沒有詩社,但有一些喜歡寫詩的學生,我和好友談勇一起創辦了一個詩社,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出一本油印的合集。
我們的大學鄰近華師大,日常的交往自然更多一些,我也曾去旁聽過宋琳的詩歌課,當時還沒有真的認識他,在課堂上他用迷人的催眠語調,進行著現代主義的啟蒙。華師大的大門口有一家小酒館,他們的詩社有時會請我們吃飯,吃到沒了酒又沒了錢的份上,有人叫一聲“干爹”,于是酒館老板就笑嘻嘻地出現了,然后,啤酒就成箱地跟來了。
大約三年級時,我和陳東東、宋琳才算真的認識,并且一直交往至今。和陳東東的相識要略早一點,關于寫作他同樣說過一些讓我受益的話,在最近寫給他的贈詩里,我這樣寫道:“我們之間從不是雄辯的氛圍,/耳語般的溪流進到心扉,/有些已是地板下干涸的電池,/有些匯成瀑布,至今聲若雷霆。”
我第一次發表詩應該是在安徽的《詩歌報》上。在大學時自己也油印過幾本小冊子,似乎是一年一本,這習慣在畢業后也持續了不少年;在早期的那些習作里,《揚州郊外的黃昏》的完成度似乎還不錯。
我愿意將上世紀80年代稱之為“最近的故鄉”,也曾對此懷有濃烈的鄉愁,《舊上海》《重新變得陌生的城市》都與之相關,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意識到那個年代值得反思的東西更多。至于詩歌,給予我的其實是一種內在的獨立人格,無論處在哪種現實環境里,我都有恒定的一面。
崖麗娟:您寫詩幾十年間是否感覺疲憊和厭倦,讓您堅持下來的動力和理由是什么?
朱朱:我沒有堅持過什么,寫詩近于本能,幾乎像呼吸那么必需,一天之中,如果不和詩歌發生一點聯系,我會覺得自己虛度了時光,盡管在書桌邊想上一個上午,可能連一個字也寫不出,甚至只是刪除了昨天寫下的一行。詩不是寫出來的,而是你需要和它們生活在一起,經過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的相處,它們才肯向你顯露最真實的模樣。
有時候,我也會厭倦一切,甚至想起這顆星球早晚都要毀滅,意識到這一點,對寫作也不是壞事。
崖麗娟:您的成績有目共睹,評價您的詩歌,組詩《清河縣》是繞不過的作品,在《清河縣》里您寫“人性”,也寫“性”,怎么想起要以此為創作題材的?
朱朱:當時我試圖以此傳達人性的相對性和復雜性。如果一個人有足夠的能力,就可以通過性折射出人性或世界的全部,但這是很難做到的,所以性這個主題始終被不同年代的作者書寫著。
崖麗娟:很多讀者對現代詩的隱喻感覺晦澀難懂,主觀意象太多是否對讀者構成閱讀障礙?作為詩人,您為誰寫作?
朱朱:寫作不是炫技,不是一場關于難度的競賽,但詩本身就是有難度的,關系到速度,穿越事物的速度,也關系到準確,蘊含多義的準確。
我不揣摩、更不低估讀者的智商,有時候,我有意識地為自己設置障礙,以免寫作慣性的衍生,譬如在寫作《旱船》之前,我就決定不用一個明喻。更多的時候,難度意味著為具體的主題找到合適的表現形式,譬如去年的兩首詩,采用通篇提問的句式更吻合《曼德斯塔姆的一首詩》的主題,而在《夏爾巴》那首詩中,我迫使自己采取短促的句式,以對應那種在雪線之上攀緣的心跳感。
我為詩這樣一種既有的傳統而寫作,我希望自己能和同代人一起真正地延續它,在《過靈巖寺》里,我寫過“一再地,終點往前流去”。
崖麗娟:在詩歌不斷被邊緣化的語境下,詩人何為?當代語境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詩歌對現實生活的呈現?
朱朱:也許我孤陋寡聞,不記得人類的歷史上,有誰因為詩人的身份高踞于權力的核心,或者有哪一首詩決定了關鍵時刻的社會走向,邊緣或許意味著更多的精神空間……不過,在今天,也許是詩人們自己萎縮了,退出了,變得沒有能力回應當代的問題,蜷縮在一個抱團取暖的小圈子里。
崖麗娟:我讀過批評家張桃洲教授主編的《尋找話語的森林——朱朱研究集》,有很多批評家都評論過您的詩,詩歌創作與詩歌批評是一種什么關系?您從中收獲了什么?
朱朱:關于我最早的評論,應該就是張桃洲寫的那篇《尋找話語的森林》,當時他還在南京大學擔任教職,我們在一起度過了不少快樂的時光。書中有一些作者我從未謀面,譬如年輕一代中的賴彧煌,他的那篇文章寫得妙趣橫生,可惜他早逝了。
對我來說,獲得來自評論的深切理解,當然是很大的安慰,譬如我讀姜濤的那篇文章時,就在想:精妙的傾聽,智識與感性在他那里并存。還有一些后來寫出來的好文章沒有被收錄進來,譬如麥芒的《無人賦予使命》、李章斌的《成為他人》等。
馬小鹽關于《清河縣》第一部的“環型劇場”論,為我寫作《清河縣》第二部帶來過啟示,這是批評在切實地影響到我的創作。
崖麗娟:身兼詩人、藝術策展人,兩個身份之間的張力構成的是相互啟發、相互促進、相互提升的關系嗎?有沒有沖突?
朱朱:開始時,兩個身份之間的齟齬不少,主要是時間和精力的分配、知識系統的調整、個人習慣的改變等,譬如過去我只能在自己的書房里寫詩,后來,等到我也能在上午時分的旅館里寫詩時,情況就開始好轉了。
現在看來,從事策展,尤其是寫作藝術評論,讓我有機會深入到他人的思維方式之中,幫助我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詩人身上的兩種常見病:半是高士半是怨婦式的自我中心主義、遺老式的文化優越感。
崖麗娟:您先后出版過法文版詩集《青煙》和英文版詩集《野長城》,在中外詩歌交流活動中獲得哪些啟發,創作中會受到潮流的影響嗎?
朱朱:沒有什么潮流等著我去匯合,更多的意味著我得以置身在異域,以一個觀光客的身份觀察著那里的“好天氣”。出版《青煙》的收獲,是我被邀請去了出版社所在的海港拉羅榭爾,回來之后以那里為原型寫出了《小城》這首詩。當時,出版社安排在大西洋沿岸的一些小城鎮做了幾場朗誦,有一座小鎮為我們舉辦了隆重的晚宴,但是鎮長遲到了,他來了之后一個勁地道歉,原來他是為一頭母牛接生去了,在日常的工作中,他交替擔任鎮長和獸醫這兩個角色。
受限于語言能力,我對西方詩歌的了解絕大部分仍然來自中譯本。對于國外的同行,我近年的記憶里倒是有一些零星的片斷:在一次互譯活動上我邂逅了安妮柯·布拉辛哈,荷蘭的一位女詩人,我為她的那首詩激動過,《蒲福風級表中的貝多芬》,起勢平緩,然后旋律一浪高過一浪,結尾臻于一種近乎抽象的虛無。此外,德國的楊·瓦格納應該是一個極其用功的詩人,2019年我們一起受邀參加鹿特丹詩歌節,有一天清晨,在旅館門前,他一邊觀察著草地上的鳥群一邊記著什么,好像畫家在寫生,后來,那些鳥廝打起來了,不知道是否干擾或改變了他的思路。
崖麗娟:您關注90后、00后年輕詩人的創作嗎?如何評價他們?有什么建議?
朱朱:屬于他們的時代正在到來,最近兩三年,我和80后、90后之中的幾位漸漸有了一些日常的交流,雖然讀他們的作品并不多,但他們的修養、趣味和判斷力都顯得可靠,只要有閑暇的時間,我很愿意彼此以朋友的方式一起談論詩歌,分享寫作的進展;在我的同代人那里,這種激情變淡了,話題開始變成無休止的懷舊之類……
時間確實過得很快,我也到了給別人提建議的年齡了,那就“修辭立其誠”吧。
崖麗娟:感謝您百忙之中回答。
朱朱:應該感謝您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