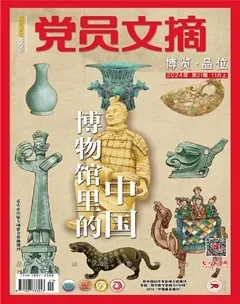我們為什么需要博物館
博物館,在不同人眼里是完全不同的物種。學者去尋找研究材料,學生去吸收萬千知識,文物、歷史和藝術愛好者循著特定的展覽和展品而來……現在,大量新媒體博主又為博物館賦予了“打卡”、引流的新用途。博物館是收藏知識的殿堂和展示文化的客廳,也是教育的工具、城市形象的標識。
n博物館是從何時起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的?2008年我國博物館實行免費開放是一個關鍵節點,從此,博物館破除門檻,成為類似公園的公共場所。而近年來博物館積極轉變形象,文博領域在全社會中熱度陡然攀升,則是另一個重要轉折點。壯麗的建筑、精巧的文物……博物館到底帶給了我們什么?我們為什么需要博物館?
n博物館能治愈精神內耗嗎
n在城市里,博物館是一處相當特別的空間。今天的博物館,爭相成為城市里數一數二的地標建筑,充滿設計感、想象力、本土性,并且必須雄偉、壯觀,同時融合古典與現代設計,具備名留建筑史的極佳條件。
n博物館內部巨大的挑高結構,展廳里由燈光營造的深邃而層次分明的氛圍,無不表達一種神秘、莊重的感受。
n n
n在這樣的環境中,當我們面對博物館的藏品,我們會生出什么樣的獨特感受?
n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程樂松曾如此表述:“我們每個人都是有歷史感的,都覺得我們來自那片觀念的土壤,都來自那個時代。雖然我們甚至不知道文化基因或者心靈架構中間,還有哪一部分來自這些文物的留存,但我們心里清楚地知道,我們在精神和觀念意義上和它們有關系,但又不知道是什么關系——這是最妙的一種感受狀態,因為你可以天馬行空。”這也是很多人喜歡逛博物館的原因——與喜歡科幻的邏輯一樣,博物館是朝向歷史的想象,科幻是朝向未來的想象。
n一間運營良好的博物館,會準備好讓人目不暇接的展品,指引人們前往一個個陌生的世界。對很多人來說,展品所帶來的想象之旅,不僅可以豐富知識,更在于投放注意力。置身博物館,便可以將自己暫時交付出去。
n廈門大學教授張曦說:“在博物館里,人們可以獲得一種眼光,一種超越當下、超越渺小自我、與偉大民族的歷史聯系在一起的眼光。”
n人類總是需要故事。而博物館講述的是真實發生的、與我們有某種關聯的故事,是人類自己的故事,并且往往以巨大的時間尺度,映襯我們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暫,從而提供暫時的休憩。“博物館的功能本就包含教育和休憩,是可以充電的地方。如果在職場上感到困惑或者焦慮,到博物館中尋找知識和智慧,其實是一件挺好的事。博物館就應該和公園一樣,放松一下,喘口氣,不也挺好?”上海大學文化遺產與信息管理學院副院長徐堅說。
n理想博物館
n雖然博物館以物質的收藏為基礎,但時至今日,物質已不是衡量一個博物館的唯一標準,更重要的是闡釋,是講故事和講道理,讓觀眾在與文物短暫的對視中獲得共鳴與啟發。藏品如何陳列,如何闡述,如何延展它的內涵和外延,體現出一個博物館的策展和策劃能力。
n如果沒有良好的策劃思路,沒有對藏品進行具有知識性、啟發性的整理呈現,即便珍寶如山,也難逃鄭振鐸對博物館界提出的犀利批評:古董鋪子、雜貨攤子。古董鋪子只強調單個古董,突出經濟價值,而博物館總是通過一系列藏品的組合和對照,講述物質背后更寬廣的精神世界。
n張曦說,過去,博物館側重于把文物當作“東西”,把“展”理解為一種對象化“展示”,所以許多博物館用框框罩住展品,再呈現在觀眾面前。現在國內很多博物館的認識已經發生了改變,比如,有些展覽開始將文物當作一段歷史、一種生活方式的載體,鑲嵌在具體語境中。還有的博物館做了很好的3D體驗,讓觀眾參與到文物背后的歷史生活中。
n n
n“今年是馬王堆漢墓考古50周年。如果你去逛湖南省博物館的馬王堆文物展,你就會看到,50年前考古學對文物的理解,就是把文物當‘東西’。這種思想反映到展覽布陳上,就體現為按照材質和功能來展示‘物’。”張曦說,隨著認識的不斷加深,湖南省博物館對馬王堆漢墓的陳列,也在條件允許的范圍內有了很大改進。
n故宮博物院曾是國內最為“激進”的博物館之一。故宮自然有它得天獨厚的條件,它有裝滿無數傳奇故事又妙趣橫生的空間——它可以“點亮”宮墻讓模特在紅墻下走時裝秀,也可以在上元之夜將《千里江山圖》的光影投在琉璃屋頂上。它還有約186萬件(套)浩瀚的文物收藏,讓它如今可以每個月不重樣地推出重磅展覽。
n這一系列獨特的嘗試,創造了觀看故宮的獨特視角,有一些是復古和還原,另一些是創新與對話,收獲無數好評。具有行業風向標意義的故宮,也為其他博物館作出示范,故宮都能打開自己,還有什么可擔心的?后來,一系列博物館創新便普及開來。
n博物館是城市專屬嗎
n我們何以成為我們,人何以成為人,博物館就是一本答案之書,你總能夠在那里找到答案——因為智力,因為技術,因為思想文化,因為山川地理,因為偶然……博物館經由對人類物質文明最精華之作的收藏展示,講述著我們所知的人類精神文明的全部歷程。
n然而,這種對人類文明和總體命運的關注,是每個人都具備的嗎?收藏文明的博物館,對每個人而言都重要嗎?
n博物館是典型的城市產物。因為博物館藏品的匯集,本質上是財富和權力集中的結果。中國雖然幾乎每個縣城都有博物館,但地級市以下的博物館發展并不充分。徐堅曾提出“縣級博物館陷阱”之說,指的是博物館試圖向上仿效,但是資源有限,博物館越往下沉,資源局限就越明顯。
n但別忘了,博物館本身是一個十足包容的概念,并非只有那些天價或無價之寶才值得進入展廳。在莊嚴的大型博物館之外,還存在大量中小型的民間博物館、行業博物館乃至社區博物館、村史博物館。在這些不那么雄偉輝煌、高高在上的建筑里,博物館與人們產生著更親切的關系。
n社區博物館和村史計劃一直是徐堅關注的領域,他認為,好的社區博物館一定是扎根社區,為社區居民代言和發聲的。徐堅說:“如果一個社區的退休老人沒事就去博物館里坐坐,被當成活文物,充當博物館志愿者,這樣的社區博物館一定能活下來。如果一個城市里有十幾個、幾十個這樣的社區博物館,不就是一個鮮活的城市博物館群嗎?”
n博物館是記錄和收藏過去的載體,而共同擁有的過去,形成人們的文化和身份,因而博物館也是一種文化認同和文化表達的途徑。每個地方的人都需要自己的博物館,每種身份、行業的人都可以通過博物館收藏走過的歷程,展現身份和文化認同。
n徐堅說,在上海和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里,也有不少社區博物館實踐,很多以村史館的名義出現。在貴州,三線工廠舊址上建立起承載三線一代和三線二代集體記憶的博物館,它們以特定方式加入三線工廠遺產的社會更新之中。“任何地方,任何人群,任何時代都需要博物館,因為文化認同和表達的需求是明確存在的。”他說。
n(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