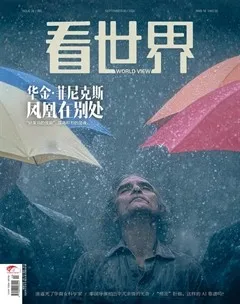這屆年輕人,用婚前協議保衛愛情

龔亞煩了,結婚之前,她的媽媽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讓自己難以招架的“財產提議”:一會兒是“天價彩禮”,一會兒是男方全款買的房產要加女方的名。
在她看來,媽媽的這些提議,會讓自己的婚姻有了一層“交易”屬性。為了避免媽媽的婚姻財產觀影響到她的親密關系,她和未婚夫商量,決定簽署婚前協議。
在她這里,婚前協議不僅僅被視為處理財產分配的法律工具,而是一種維護兩人感情純潔性和公平性的相互承諾,確保他們的關系不被外界財務觀念所侵蝕。
像龔亞這樣在婚姻面前想尋求婚前協議幫忙的女性,越來越多。不少人將婚前協議作為備婚中必不可少的環節,主動與對象及雙方家庭溝通,小到家務分工、寵物歸屬,大到財產公證、忠誠條款等等。
她們就婚前協議的商議和簽署過程,也是女性在親密關系和婚姻家庭里對于主動權的爭取與確認。通過婚前協議,年輕人試圖在感情與生活瑣事之間找到平衡。
“純粹”的關系
龔亞決定和未婚夫共同簽訂婚前協議的初衷,源于與母親在財產問題方面的分歧。
剛大學畢業時,在雙方父母的介紹下,龔亞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兩人年齡相仿,平常也玩得來,逐漸從朋友發展成情侶。由于雙方父母較早地“參與”了這段關系的推進,3年后,兩人也順勢發展為未婚夫妻關系。
從以個體為中心的情侶關系,遞進為連接兩個家庭的婚姻關系,財產的分配與處置,是橫亙其中的一道看得見、摸得著的坎。這道坎曾一時難倒了龔亞。
門當戶對的基礎上,未婚夫的家庭財產條件還略優越些。未婚夫出身溫州生意世家,龔亞的媽媽“不知道從哪兒道聽途說,溫州給彩禮非常高,甚至兩三百萬都有”。
出于“愛女心切”、不能讓女兒在婚姻中“吃虧”的想法,龔亞的媽媽建議女兒:要個百萬彩禮。
面對媽媽時常提出的一些過于實用主義甚至具有交易性質的提議,龔亞匪夷所思。一番追問下才知道,這個故事媽媽只聽了前半部分,故事的后半部分是:女方還了兩倍的嫁妝。
當媽媽再次給出“男方全款購買的婚房應該加上龔亞名字”的提議后,母女倆又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大吵起來。龔亞認為,男方名下的婚房實際由他的父母出資,并不是未婚夫自己的資產,自己不應該向對方提出他無法作出決定的要求。
爭吵無果,龔亞拖著疲憊的身心回到家,坐在沙發上向未婚夫又一次大倒苦水。傾訴中,龔亞向未婚夫提出:“不如我們簽婚前協議。”意料之中地,未婚夫十分贊同這個決定。
在這之前,第一次和媽媽有類似的分歧之后,龔亞就意識到婚前財產問題的復雜性和討論的重要性。此后,她經常在社交媒體平臺了解有關婚前財產、婚前協議的案例和帖子,也會分享給未婚夫一起討論。潛移默化間,婚前協議成為了龔亞與未婚夫處理雙方財產分配的共識。
婚前協議的作用并非體現于計算分毫的精明,反而在于讓婚姻變得更加純粹。

認真討論簽訂婚前協議的細節,以及如何處理各自以及家庭共同財產,意味著他們將一直以來的擔憂和期待放在桌面上,開誠布公地討論。這個過程不僅是對婚前協議條款的商定,更是對兩個家庭幾代人積累財產的合理配置,以及夫妻共同價值觀的探索和確認。
在龔亞他們看來,婚前協議的作用并非體現于計算分毫的精明,反而在于讓婚姻變得更加純粹:“我們兩個人名下很多東西都是爸媽給的,這些其實是屬于各自原生家庭的,婚姻的復雜就來源于兩個家庭的結合。簽署婚前協議并不是說要算得很清楚,而是我們不想因為這些東西影響兩個人的感情,那還不如提前將它說明白了。”
他們將婚前協議看作感情與財產矛盾的隔斷層,希望它能將財產等其他問題隔絕在他們親密關系之外。和媽媽提出他們將簽署婚前協議后,媽媽雖然不滿意,但試圖干預的行為減少了許多。龔亞覺得,或許是媽媽也明白,婚前協議的白紙黑字已經難以讓“外人”插足。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們婚嫁觀念的變化,人們對進入婚姻越來越謹慎。現代婚姻面臨著越來越多的考驗,對婚前協議的態度也是愈加開放和包容。
“只能說,他的負債不用夫妻共同承擔,我就萬幸了。”

婚前協議“失效”了
婚前協議作為一種需要雙方共同協商約定,同時還涉及更廣泛、更復雜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并不意味著簽了就能一勞永逸,或者能夠按照簽署的條款完美執行。
直到決意離婚、咨詢律師后,盧娜才發覺,當初婚前協議中保護自己婚后財產所得的條款是無效的。
結婚前,盧娜偶然發現,男友一直以來的超前消費習慣,已經在她不知道的情況下累積了高達20多萬元的負債。
發現未婚夫負債后的盧娜,心情異常復雜。獨自考慮良久,因為無法割舍這份感情的她,抱著對方婚后能夠改變、一切都能變好的期望,借此契機提出簽署婚前協議。
決定提出婚前協議的那一刻,她已經意識到這是對這段關系的一次挑戰,“覺得有點傷感情”。但男友沒有坦白交代自己負債的情況,讓她感到不安。在長談中,盧娜坦誠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和期待,希望通過婚前協議,約束對方超前消費的習慣和行為。
男友一開始并不情愿,或是自知理虧,兩人并未僵持太長時間,男友便答應了盧娜簽訂婚前協議的決定。
盧娜托律師朋友拿到了婚前協議的模板,并在模板的基礎上,與男友簡單商量了條款后簽署。如今回想,她意識到這份協議并沒有太多有關財產歸屬權的實質性內容,條款也不嚴謹,比起法律意義上的“婚前協議”,這更像是一份“情感協議”,因為“財產這部分內容并沒有很細致地談”。
婚后,前夫的不良消費習慣以及負債等問題,并未如盧娜預期的那樣迎刃而解,甚至愈演愈烈。盧娜不得不認清現實,提出離婚—這段婚姻,只維持了4年。
條款的其中一項提及,若男方婚后沒有約束行為并改善負債狀況,房產需要寫上盧娜的名字。但直到咨詢離婚律師時,盧娜卻被告知這份婚前協議條款設定得并不嚴謹,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而條款中提及的房產,也已經被前夫用于抵押貸款。
在這種情境下,拿出婚前協議,或許除了傷感情以外就別無其他了。“我覺得我也沒法要求拿到更多了,畢竟他都負債了,財產都要優先給債權人。只能說,他的負債不用夫妻共同承擔,我就萬幸了。”盧娜自嘲道。
離婚后復盤,盧娜認為婚前協議最能夠保障的仍是財產等更為實質性的利益,而當時的自己恰恰并未對此認真對待,也并未咨詢過律師或進行財產公證,以確認協議的嚴謹和效力。
“新型”的浪漫愛情表達方式
牧子在了解婚前協議并且考慮自身情況后,并不打算簽訂婚前協議,主要原因是就其情況而言,婚前協議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目前我和男友名下分別有一房一車,也沒有負債,財產狀況不復雜。這些財產無論是否簽婚前協議或進行財產公證,都會被認定為是婚前財產。”
我和她提到,當下,簽婚前協議在年輕人的婚戀狀況中似乎是一種新趨勢。而牧子也露骨地指出,這或許只是一種“新型”的浪漫愛情表達方式—似乎簽了婚前協議,就意味著兩人“渡過一劫”,此后關系理應將更加穩固,彼此將更加深愛。

在這種觀念下,簽署婚前協議不僅是對個人財產和權益的保護,也是對伴侶的一種承諾和對婚姻負責的表現。它代表著在這份契約簽下各自姓名的雙方,愿意為了共同的未來和幸福采取預防措施,彼此信任并準備共同面對生活中的挑戰。
但此前在民政相關部門的工作經歷告訴她,婚前協議并不如大家想象中那樣“即簽即生效”—在司法實踐中,多數人常常提到的婚前協議中的“凈身出戶”由于難以約定具體數額,因此往往難以被法院認可;忠誠條款實際只有雙方在離婚時自愿遵守并愿意承擔代價時才會生效。
“在我接觸到的一些卷宗里,婚前協議真正能夠保障的還是財產問題。家務分工、寵物歸屬、忠誠條款這些內容,法院更多只是酌情考量,但能被完全認可的還是少數。”牧子認為,若僅抱著“增進感情、維護愛情”的想法簽訂婚前協議,而對具體的制度內容和條款效力缺乏了解,那么最后的結果或許會失望。
同時,如果簡單將婚前協議視作財產問題的“蓋棺定論”,毫無財產管理或防范意識,那么實際上仍是將財產及自身置于風險之中。
“即便簽署了婚前協議,只要有人試圖去操作,能鉆的空子還是很多的,例如轉移財產、不動產抵押等等。所以婚前協議并不是一勞永逸的。”牧子說道。
作為過來人,雖然婚前協議對盧娜而言,并未真正意義上“有用”,但她依然建議年輕人簽訂婚前協議:“對于下一段婚姻,在簽婚前協議的時候,我會提前把最壞的情況考慮進去并咨詢律師。這樣做不代表我要拿它來對付什么東西,我只是在保護我自己而已。”
利用婚前協議的商討,來建設兩人之間的共識橋梁、謀求價值觀契合,甚至決定在進入更嚴肅的婚姻前提前“好聚好散”,這或許是當下年輕人開始熱衷于討論婚前協議的原因。
特約編輯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