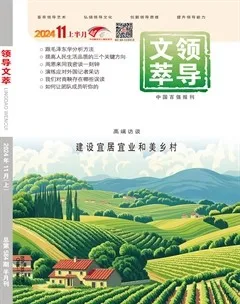比壞與做奴隸的邏輯

近日重讀魯迅先生的《燈下漫筆》,發(fā)現(xiàn)有一種可以叫“比壞”的心理或行為“邏輯”。
魯迅寫到袁世凱想稱帝的那一年,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鈔票大貶,以至不能兌換銀子了。雖然政府命令商家不允許拒收鈔票,但是狡猾的商家總是找各種理由陽奉陰違。在這種情況下,“幸而終于”出現(xiàn)了鈔票換銀子的行市,盡管兌換率是六折幾,魯迅先生還是“非常高興”,趕緊去換了手頭一半的鈔票;孰料竟然又漲到七折,先生“更非常高興”,趁機全部兌了。完事后先生感嘆:現(xiàn)銀“沉甸甸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并做了這樣的比較:“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平時”不答應的事情,“非常時期”就答應了,不但答應了,而且“非常高興”,這是什么邏輯在起作用?我以為是比壞邏輯。魯迅先生的“高興”是因為與最壞的情況(鈔票徹底不能兌換成銀子,甚至徹底變成廢紙)相比,以六折幾或七折兌換已經(jīng)是不幸中之大幸,至少不算最壞。如果不是這樣比壞,而是堅持與“平時”的正常情況比,還能高興得起來嗎?
令人略感突兀的是,魯迅先生在敘述了上述“高興”之事后突然筆鋒一轉:“但我當一包現(xiàn)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為什么會這樣?魯迅寫道: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么東西; 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fā)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后給與他略等于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么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
這使我想起波士頓猶太人死難紀念碑上的一段碑文(作者為新教牧師馬丁·尼莫拉):
當納粹來抓共產(chǎn)黨人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chǎn)黨人。當他們來抓猶太人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來抓貿(mào)易工會主義者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貿(mào)易工會主義者。當他們來抓天主教徒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是新教徒。當他們來抓我時,已無人替我說話了。
一般認為,這段話的意思是:人類是命運共同體,其自由和生命權利都是相互關聯(lián)的而不是孤立的,別人的自由同樣也是你的自由。如果你不保護他人的自由,那么你的自由也終將不保。
但我想這個道理也適用于比壞:當納粹殺了共產(chǎn)黨人時,你的自由與權利就少了一分,雖然你不是共產(chǎn)黨員;當他們殺了猶太人時,你的自由與權利又少了一分,雖然你不是猶太人。如此這般下去,你的自由和權利很快就會蕩然無存。
因此我的結論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壞就是壞,只要是壞,就不能有絲毫容忍,不能因為還沒到最壞就容忍較壞,否則的話,較壞必將很快發(fā)展為最壞。
同樣,任何情況下,像人的自由、尊嚴這樣的價值都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如果任其失去一部分,遲早必將失去全部。如果你認可了自己是奴隸和牛馬,你就會拿奴隸和牛馬的標準要求自己和統(tǒng)治者,只要自己過得像奴隸、像牛馬,而不是“下于奴隸”“牛馬不如”,就心滿意足。換言之,就會陷入比壞邏輯而不可自拔。
但是一旦你以做穩(wěn)奴隸和牛馬為滿足,那么,你遲早必將淪入奴隸不如或牛馬不如的境地;只有當你一開始就拒絕奴隸和牛馬的身份,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一個自由的、有尊嚴的人,以人的標準要求別人,更要求自己,你才能徹底跳出比壞邏輯。
這真是:比壞流行時,茍且無止境。
(摘自《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