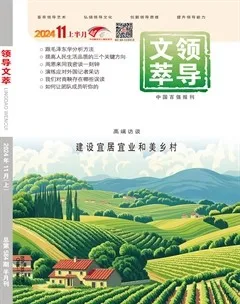演練應對外國記者采訪

在外交界,針對媒體的培訓在發達國家已很普遍。例如,駐英國的許多其他國家大使經常接受這樣的培訓。美國大使告訴我,他每年接受上百次媒體采訪,事前都會做演練。
一
《明鏡周刊》安排來采訪我的是一位女記者,叫蘇珊·科博。科博提交了問題提綱,屬于框架性的,實際采訪應該在這個范圍內,但是記者很少能嚴格按照提綱提問,會有比較大的發揮。
德國媒體行事嚴謹,尊重受訪者,例如,記者撰寫的文稿在發表前能拿給被采訪者看,如果有引用或者概念不準的地方,可以要求調整。這種態度讓受訪者有安全感,避免被誤解。而其他國家的報刊就鮮有這么通融的情況。
記得我在澳大利亞當大使的時候,接受過一家雜志的采訪,記者是位女性,她的家族是從東歐國家移民來的,有很深的負面記憶,以至于她對任何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充滿敵意。我當時缺乏經驗,之前對她的背景沒有做足夠的了解,貿然同意了接受采訪。當我意識到她的敵視和片面態度時,就試圖用大量事例說服她,讓她更全面地了解中國,希望以此影響到她寫文章的基調。原本約定談40分鐘,結果談了近3個小時,我真是苦口婆心,甚至拿出中國的書刊,用上面的照片圖像來說明中國的現狀。而她鐵了心認定中國是“錯誤國家”,顯然是帶著結論來采訪我的,自始至終在質疑中國,對我介紹的情況并不關心。
采訪之后她就不再與大使館聯系,我是在那期雜志發刊后才看到她是怎么寫的。她的文章就像剝洋蔥頭一樣,層層數落中國多么不對,最后剝到蔥心,結論是這個女大使是個“死硬的共產黨人”。她對我花很長時間介紹的中國的情況、政策和原則立場只字未提,只是利用這個采訪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和看法。此后我在選擇接受哪家媒體、哪位記者采訪時,對背景一定要做更加透徹的調查研究,對記者的意圖也要有所判斷。
二
我邀請了外交部歐洲司幾位年輕的外交官,組建起一個小團隊,一起研究如何應對蘇珊·科博的采訪。我們按照科博的問題提綱,設計出10個焦點問題,無非是德國乃至歐洲媒體對中國成見最深的那些,例如“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國軍事威脅”“中國人權”“中國經濟崩潰”之類的,還考慮到了德國人目前最關心的幾個熱點問題。
團隊每個人承擔一個題目,分頭收集資料,根據中國的政策和立場,擬寫應答要點。
第一輪演練,我把團隊分成提問和應答兩方,我做觀察員。結果發現,提問完全達到實戰水平,足夠尖刻和深入,應答則多是照著例行口徑念,雖然很周正,但顯得被動,也缺乏說服力。當我把兩撥人對調位置之后,應答仍然顯得吃力,而且經不住追問。也許存在對具體情況掌握不夠充分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查找資料、補充知識。當然也不完全是知識的問題,在記者尖銳提問的壓力之下,人的思考能力容易受到一定的制約,包括我自己,很容易被問題牽著走,陷入辯解。
第一輪演練的結果不理想,我抓緊熟悉材料,做了充分準備之后,進行了第二輪演練,由我直接作答,讓團隊的每個成員模仿西方記者隨意提問。這些年輕人很快進入角色,不依不饒,步步緊逼,越問越狠。而我雖然講了很多,態度也足夠堅定,但仍感覺被動,是被問題牽著走,態度也是對抗性的,達不到說服人的目的。如果現場的采訪是這個狀況,效果不會太好,就不如不做了。我有些沮喪,請大家先回去,自己留在會議室里靜靜地想了好久:為什么會這樣?中國明明做的是對的、是成功的,為什么在說理的時候總是爭取不到主動?從哪里解扣?
分析起來看,我對每個尖銳和批評性的問題都有答案,但就是擺脫不了被動辯解的處境。我反問自己,為什么要像在審判臺上一樣,接受西方媒體的詰問?更糟糕的是,越解釋,越容易被追問,說出的話掛一漏萬,結果很容易在糾纏不清中失去自己的立足點。
經過反復的自我審視,我終于認識到,問題出在自己的思考方式上,用大白話講就是太老實了,我一直在跟著提問者的思路走。比如,當對方質疑中國增加國防費預算、批評中國軍備帶來威脅時,我便去解釋增加國防費的用途,包括改善官兵的生活條件和更新裝備,等等。而對方就會進一步追問國防費的構成,或者直接提出關于先進武器配備等方面的問題。且不說我是否掌握這方面的全部信息和知識,就是專家,也容易在這樣的問答中陷入被對方窮追不舍的境地。而且采訪不是做報告,沒有足夠的時間引述大量事實和數據來完成對一些專業問題的說明。這樣的答問難有好的效果。
我終于想明白,必須破解對方設問的套路。對方提問的立足點是有問題的,是從否定中國的角度出發,如果我不能從根本上否定對方的出發點,就不可能與對方站到一個平等的位置上去對話。就好比有人設定了一個錯誤的公式讓你去推導,如何得出正確的結果?
思維的轉變使我悟出了其中的門道,認識上的提升讓難題迎刃而解。我請團隊成員回來,再次進行演練。這一輪我不再是坐在“被告席”上了,而是從一開始就爭取到主動的地位,無論他們的問題多么尖刻,我都可以擺脫被動,甚至用反問的方式掌握主動。比如,當問到中國為什么要造航母,是否對世界構成威脅時,我不再費力地解釋中國制造航母的過往、目的和用途,而是反問,為什么英國、美國的航母不是威脅?這樣就可以釜底抽薪地讓記者走下“道德高地”,這樣的回應可以讓歐洲讀者意識到他們的雙重標準和偏見是多么不合理。
后來的演練進展就很順利了,我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能找到新的切入點,確立主動地位。
三
2011年8月17日,我在外交部南樓一間中式會客廳接受了蘇珊·科博的采訪。我當時很放松,有那種胸有成竹的感覺。整個采訪內容基本在估計到的范圍之內,科博在提問中表現出來的批評態度也在意料當中,我總能比較自然地找到變被動為主動的方法。她一直試圖批評和詰問中國,而我的回應貫穿始終的一個潛臺詞就是:你們對中國有偏見。
采訪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我和科博都態度平和,我在開始的時候就征求了她的意見,可否用“蘇珊”來稱呼她,這樣彼此都不感覺生分。她的職業素養很好,雖然不斷遭到我的反擊,但從未面露不快,反而顯得很享受這種激烈的對話。
到最后,她幾乎窮盡了所有問題,突然提出了一個我沒有估計到也從未遇到過的問題:“那您覺得,今天的西方可以向中國學習什么?”這個提問本身是很有內涵的,也是委婉地說明她接受了我的回應,承認了中國有自己的道理和成功之處。我沒有想過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當然,準備不到的問題永遠會有。我猶豫了一下,說:“謙虛吧,中國人常說,‘三人行,必有我師’。”
(摘自《我的對面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