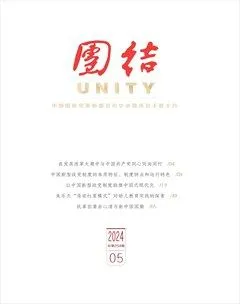向世界講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故事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廣泛宣介中國主張、中國智慧、中國方案。”2021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1]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作為政黨政治的新形態、新發展、新范式,既根植中國土壤、彰顯中國智慧,又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政治文明優秀成果。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論述,確立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世界政黨制度體系中的獨特地位,既是對世界政黨制度模式的創新發展,也是對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的重大貢獻。[2]國際傳播工作是黨和國家的戰略性工作,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我國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向世界講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故事,加強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海外傳播工作,是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爭奪國際話語權的重要內容,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一、向世界講好中國政黨故事的重大意義
(一)提升中國政黨形象和國家形象
美國政治學家博爾丁(K. E. Boulding)最早將國家形象定義為自身及他者對國家的認知集合,[3]此后以認知來理解國家形象的概念被世界大多數人普遍接受。一般認為,國家形象指“個體對于特定國家的認知表征”,而由于普通個體的認知不可能是全面細致的,只可能是一種高度概括或簡化,因此對大多數公眾而言,國家形象是一種由穩定的刻板印象與流變的對各種信息的認知和具體態度組成的綜合性印象。這種綜合性印象也可以分解為文化、政治等不同維度加以考察和測量。[4]對于一個國家如此,對于一個政黨亦如是。海外社會對中國政黨制度的認知,直接關系到對中國的國家形象以及包括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和各參政黨在內的政黨形象的塑造。就像一提起美國就想到民主黨與共和黨,一提起英國就想到保守黨和工黨,一提起蘇聯就想到布爾什維克黨,對一國政黨制度的認知與理解關乎對該國政治文明與民主治理維度上的形象塑造。
根據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對外傳播研究中心2020年發布的《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9》可知,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非西方發展中國家,海外公眾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普遍認知中,對中國歷史文化和經濟發展形象的正面認知要遠高于對中國政治治理形象上的正面認知;其中海外受訪者對中國執政黨的印象主要集中在“全面從嚴治黨”和“具有很強的組織動員能力”,選擇比例分別為38%和28%。[5]盡管全球公眾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整體印象在改善,但對中國政治維度的國家形象認知仍存在普遍的空白與偏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實現治國理政的重要手段,亦是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的偉大創新。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民主政治創新的重要亮點,也是理解當代中國治國理政與民主建設的關鍵環節,增強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海外傳播,有助于提升海外社會對中國國家整體政治文明的理解與認可,有助于提升對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理解與認可,從而促進海外中國國家形象與政黨形象的改善,“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增強我國在政治輿論上的國際話語權。
(二)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方案、中國理念認可度
自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奠定了現代政黨制度的基本理論與實踐,并在西方霸權的推動下不斷擴散到世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特別是自蘇聯解體之后,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制度受到嚴重打擊,西方國家在“歷史終結論”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輿論推動下將西式政黨制度塑造成現代民主國家政黨制度的“唯一選擇”,乃至成為全世界各大高校政治學教科書中的教條,在國際輿論中將西式政黨制度等同于現代民主政黨制度。在這樣的教條框架下,世界各國的政黨制度普遍被西方政治學和輿論宣傳根據政黨數量及選舉而劃分為一黨制、一黨優勢制、兩黨制、多黨制等簡單粗暴的分類,并以此作為國家民主程度的價值判斷標準。這一套政黨制度的理念和標準深刻影響了世界各國的制度建構與話語建構,成為所謂的“國際主流”。在這樣的制度霸權與話語霸權下,一方面,很多發展中國家盲目模仿西方政黨制度,卻沒有很好地適應本國國情,從而導致國家治理失效、社會動蕩;另一方面,西式政黨制度的內在弊病和缺陷被長期輕視或掩蓋,并在長期積累下不斷惡化。特別是近年來,西方政黨制度沒能很好地解決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分化、族群分化、價值觀分化的問題,民粹主義思潮崛起,政治極化愈演愈烈。美國、英國等國出現了主流政黨民粹化的傾向;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出現了新的民粹主義政黨崛起。西式政黨制度“制度瓶頸”愈發顯著。
相比之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對西方政黨制度和蘇聯政黨制度的超越和揚棄,創造了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具備顯著的制度優勢。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有效地避免了西式政黨間的相互傾軋、政治極化,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與參政黨各民主黨派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互相監督的親密友黨,不以意識形態劃分你我,充分吸納代表社會各階層群體,共同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是民主集中制的典型代表,是真實有效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全程體現社會各階層代表性,全程參與國家治理、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而不是西方國家在“選舉-休眠”“上臺-下野”間往復循環的“選舉工具式政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政治創新,既結合了中國歷史文化國情,又包含人類現代政治文明共同價值,是中國人為人類政治文明進步提供的中國方案與中國理念,并經過了幾十年的實踐檢驗和經驗總結。加強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海外傳播,有助于打破西方政黨制度的迷思與話語霸權,為各國民主政治改革創新提供了一條不同于西式政黨或蘇式政黨制度的道路選擇。
(三)有力反擊涉華負面言論、消除“污名化”影響
在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國際話語權斗爭愈發激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政治制度的攻擊抹黑愈演愈烈,并以此為其對中國施加各種制裁提供合法性依據。將中國體制描述為“威權主義”或“專制主義”是西方國家最常見的一種“污名化”,比如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劍橋大學政治系教授斯蒂芬·哈珀(Steven Halper)的《北京共識:中國的威權模式如何主導21世紀》,等等。這一類觀點延續了西方自由主義學術傳統以及意識形態中的“二分法”,將世界各國劃分為“威權”和“民主”兩大陣營。[6]此類觀點強調中國政治體制與西方國家的區別,例如不存在西方的“三權分立”、多黨制、普選制等,將中國的現代化稱為“威權現代化”。[7]隨著此類觀點越來越難以預測和解釋中國的客觀現象,一些學者又修正理論出現了所謂的“合法化威權主義”“回應性威權主義”“有民主特征的專制”等來描述中國。[8]在當下西方掌握國際話語霸權的背景下,西方主流的學術理論界、媒體界以及大多數政客仍將中國的政黨制度表述為“一黨專制”“一黨獨大制”等誤導性詞匯,從而否定我國政黨制度的合法性。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普遍缺乏基本了解,多數外國民眾并不知道中國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還有其他政黨,一些西方學術與媒體輿論經常將我國民主黨派歪曲為“花瓶”政黨。[9]面對西方對我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各種抹黑詆毀,我們迫切需要進一步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了解,破除國際上對中國政黨制度的各類偏見污蔑,消除涉華負面言論影響,提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國際話語權。這既是為了維護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合法性,也是為了彰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優越性,同時也是擴大國際政黨交往交流的需要。
二、向世界講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故事面臨的主要困境
(一)后發劣勢與西方話語霸權擠壓
西方中心主義話語占據先發優勢。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概念、政黨制度、政黨理論源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10]西方按照自己的經濟基礎、社會實踐、文化理念和資本主義價值觀形成了系統而完備的所謂現代政黨制度理論體系和實踐,并以此牢牢地掌握著現代政黨制度的國際話語霸權。周恩來曾明確指出,民主黨派作為政黨“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黨的標準來衡量他們。”[11]但是西方的政黨制度理論和話語體系已發展百余年,片面以多黨競爭和輪流執政為評價標準來區分“民主”與“專制”、“現代”與“落后”,使得作為后來者的“參政黨”“多黨合作”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難以被西方話語體系所接受和認同,也造成了海外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誤解、誤讀甚至妖魔化。例如在2018年“新型政黨制度”正式提出后,“先進中國研究中心”在美國《外交官》雜志發表文章《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為外國消費的“多黨制”?》,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為了對外宣傳而對中國的政黨制度進行品牌重塑”。[12]
(二)理論體系與話語權構建滯后
盡管中國的多黨合作制度已經經過了70多年的發展和實踐,但是相關的學術理論和話語權建構相對滯后。學術話語嚴重滯后于政治話語,難以實現政治性和學理性的有機統一,造成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解釋力相對不足。雖然近年來,我國有關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學術理論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中國學者發表在國際刊物的相關英文成果仍然很少,例如在谷歌學術上檢索“中國政黨制度”(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截至2024年6月只能找到三篇中國學者的正面研究成果,一篇是發表在《巴西政治評論》上的關于中國政黨制度中的無黨派人士角色研究,[13]一篇是發表在某理科期刊上的“新時期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理論話語體系構建研究”,[14]還有一篇是發表在《國際社會科學與教育研究雜志》上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中國式民主發展的歷史邏輯”。[15]同時,中國學者關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成果往往以解釋性成果為主,相關的基礎理論研究有待提升,缺乏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概念來解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現狀。而且,批判性和學理性的成果相對較少,不利于世界各國認識和理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
西方的政黨實踐來自于資產階級“國家建黨”,其現代民主政黨評判的核心標準是“公開表達反對和異見”,并以此為衡量合法性的準繩,而中國的政黨制度來自“黨建國家”,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均成立于新中國成立前,并在協商建國中獲得合法性,但是目前大多數國內理論研究以及對外理論宣傳,仍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表達反對和異見”的政治過程闡釋不夠、公開不夠,讓很多人誤以為中國政黨制度在實踐中“只有統一和同意”“沒有反對和異見”。但現實是,任何政治過程中必然存在反對和異見的表達,只是中國政黨制度跟西方政黨制度的處理方式不一樣,在化解分歧、求同存異、凝聚共識上恰恰是中國制度的優勢所在,但由于相關理論建構和話語宣傳的不足,反而成為西方政黨理論和話語攻擊中國政黨制度的主要靶點。
(三)國際傳播方式與手段存在不足
首先,國際傳播存在“量”上的不足,尤其覆蓋面嚴重不足。盡管2018年正式提出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這一概念,2021年發布了各種語言版本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但上述官方傳播的覆蓋面有限,缺乏民間傳播的有效配合。傳播渠道主要仍是中國政府發布會、官方網站、官方媒體,傳播渠道單一。[10]海外的外文媒體和華文媒體經常會有涉及中國政黨的報道信息,但是直接介紹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報道很少,正面宣傳則更少。例如,通過信息檢索發現,截至2024年6月,比較主流的幾大海外華文媒體中,北美《僑報》目前無新型政黨制度相關報道,《世界日報》無相關報道,新加坡《聯合早報》國際版有9篇相關報道且均為正面報道,《新華澳報》有一篇轉載中新社的報道,《星島日報》有一篇原創正面報道,香港《文匯報》集中有4篇正面報道等;而反華中文媒體《大紀元》、《美國之音》中文版、《自由亞洲電臺》中文版均有多篇針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負面報道,“中央社”等臺灣當局媒體也有針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負面報道。并且,上述報道皆是圍繞《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發布這一事件而產生的,并沒有涉及新型政黨制度日常運作或具體實踐的報道。
其次,國際傳播的“質”有待提高。國際傳播與對內宣傳的受眾、目標、要求和標準等方方面面均存在顯著差異,但當前很多宣傳部門及有關干部仍然以“內宣”思維指導外宣工作。官方有關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國際傳播新聞、文字語言、視頻等存在傳播方式生硬、語言行文僵化,主動表達和創新轉化的意識不強,缺乏針對性和靈活性,脫離了國際社會多元化的現實需求。在有關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國際傳播內容上,政治語言過多、理論論述過多、生動案例太少、接地氣的語言太少,導致即便在課堂上、新聞上看到了也難以深刻理解。
再者,民主黨派領導干部參加國際交往活動是直接講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故事的重要平臺和機遇,但現實是目前這一平臺作用發揮不足。民主黨派跟中國共產黨都是講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故事的責任主體。我國八個民主黨派的國際交往活動差異較大。民主黨派干部在參加國際交往活動、會見海外僑胞或外賓時較少以黨派身份參加。多數民主黨派除了高層領導參與國家外事活動與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之外,極少以本黨派名義開展外事接待或出國訪問活動。有些民主黨派的成員大多以來自某些特定領域的專業成員為主,民主黨派活動聚焦于國內事務、地方事務,有的民主黨派成員狹義地理解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沒能認識到參政黨國際交往在國家政權建設與民間公共外交上的重要意義,對參加、開展國際交往活動不積極,國際交流這一重要職能發揮不充分。特別是以民主黨派身份開展政黨外交、公共外交的政治意識有待加強。
三、進一步向世界講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故事的路徑思考
(一)“誰來講”:完善體制機制,以多元主體推動構建新型政黨制度國際傳播話語權
首先要構建完善多元主體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國際傳播體制機制。在加強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國際傳播工作上,要形成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民間和官方共同參與的多元主體的大傳播格局。
在中國共產黨方面,各級中共黨委首先要進一步加強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落實,將多黨合作、互相監督落到實處,帶頭尊重照顧各民主黨派,發揮政治領導作用。要進一步在全黨貫徹落實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的會議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黨委(黨組)要把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納入黨委(黨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各級領導干部要主動做國際傳播工作,主要負責同志既要親自抓,也要親自做”。[16]中國共產黨各級宣傳部門、外事部門、統戰部門等要肩負起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國際傳播工作的領導責任,發揮領導作用,帶頭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國際傳播納入多黨合作、國際交流、外事外宣、僑務工作與海外統戰工作等。主動邀請民主黨派領導干部和代表人士參與有關國際傳播工作、僑務工作、海外統戰工作、國際交流工作的各項活動,為民主黨派現身說法展現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創造條件和機會。要加強中共黨內關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國際傳播的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加強中共黨員干部國際化能力培養。
各民主黨派要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主體責任,發揮自身作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親歷者、參與者、貢獻者的獨特優勢,在輿論上主動發聲,現身說法打破西方輿論所謂的“民主黨派花瓶論”,展現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優越性。各民主黨派要積極主動擔當作為,配合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公共外交,完善自身國際交往與國際宣傳的制度體系、部門配置、人員能力建設,充分發揮自身成員智力資源豐富、專業優勢突出、海外聯系廣泛的優勢,結合自身職能與特點優勢,明確國際交往的目標定位。民主黨派開展政黨外交,其目標定位應以向外國政黨交流參政議政經驗、黨派組織建設經驗、國際問題看法以及兩國政黨制度經驗等,讓外國黨派了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真實情況和優勢特點。民主黨派開展公共外交,其主要目標對象應以海外精英群體和輿論領袖為主,工作定位以專業性較強的講座、研討會、訪談等活動讓海外公眾、社會精英理性客觀認識中國、認識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要加強各民主黨派內部國際傳播人才培養和隊伍培訓,打造本民主黨派的國際傳播活動品牌、代表人物品牌,各民主黨派都要形成一支能力素質過硬的國際傳播人才隊伍。
(二)“講什么”:充實新型政黨制度的內涵外延,以問題為導向構建普適性傳播內容
進一步加強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的建構。要立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立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三方面價值來共同充實新型政黨制度的內涵和外延。首先,要立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實踐發展,講清楚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從中國革命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創立和發展脈絡,突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從“多黨合作建國”到“多黨合作治國”的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其次,要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清楚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價值理念傳承,突出中華文化中“結黨”“黨爭”“和而不同”和“大一統”“天下觀”等的文化價值取向對構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化影響。再者,要立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講清楚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民族性與世界性的有機統一,回應當今世界各國政黨制度發展的普遍性難題癥結和訴求,突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推動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中重要意義和價值追求,發揮國際政黨交流合作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重要作用。
同時,以問題為導向構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具有普適性的話語體系內容。面對國內國外學術界和輿論界的主要質疑,要敢于交鋒交流,迎難而上,直擊痛點問題。
第一要直面西方主流政黨理論和話語體系中關于“表達反對和異見”的核心標準。政黨到底為何而存在?選舉和投票是手段還是目的?如何處理多數與少數的關系?如何衡量政黨的權力?……應明確這些核心問題,給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相比于西方政黨制度更具有競爭力的話語答案。近年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出現了政黨政治民粹化極端化的趨勢,形成“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否決政治”,“表達反對”反而流于形式主義,加劇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因此以“公開表達反對”來衡量政黨的實權和制度的民主化顯然也走上了形式主義的歧途。“表達反對”不應是目標,而是為了凝聚共識,包括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內的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相比于西方制度不是“沒有反對和異見”,而是能更好地協商和處理反對和異見,最終實現凝聚最大共識,既達成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也充分照顧考慮少數。
第二要直面廣大發展中國家政黨政治的最大痛點需求。很多發展中國家在歷史上也有“政黨建國”的經歷,但受到國內外各種因素干擾影響,或強行建立多黨制走上西式政黨惡斗老路,或長期難以解決政黨組織渙散、派系分裂、能力孱弱、成員腐敗等問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核心優勢之一就在于回應“如何以政黨制度帶動國家治理”這一廣大發展中國家政黨制度建構的核心訴求,無論是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治國理政經驗還是各民主黨派的多黨合作、參政議政經驗,都對發展中國家極具吸引力,我們要以此為契機,采取“求同存異”的策略以降低海外民眾陌生感,[17]有針對性地向其他國家提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政黨制度話語經驗。
(三)“怎樣講”:創新傳播方式,營造有利話語環境
即便有好的傳播內容也必須同時具備好的傳播方式和手段,才能達成傳播效果。首先就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傳播方式,讓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與話語入腦入心。除了傳統的有官方主導的發布白皮書、理論文章和政治培訓之外,還要充分利用電視、廣播、互聯網社交媒體、短視頻平臺等全媒體渠道,充分發揮官方與民間、國內與國外各傳播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以新穎接地氣的圖片、文字、短視頻、動畫、音樂等多種藝術形式傳播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概念和實踐成果,制作吸引不同年齡段、不同文化背景和經濟階層受眾的傳播產品。鼓勵國內外的具備相關能力的有關專家學者、社會名流、網紅公眾人物等在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傳媒平臺上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正名、發聲。要統籌領導干部、專家學者、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多方位宣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優勢作用,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2]要加強民主黨派組織和領導干部在媒體、社交網絡、國際交往活動中的展現和發聲,加強黨派及其成員的宣傳工作意識。充分利用好外事部門、僑務部門、政協、人大、高校等各種渠道的跨國人員交流活動平臺,在這些活動平臺中創造海外僑胞、外國友人直接接觸多黨合作實踐和成果的機會。
同時,要主動營造有利于傳播的話語環境。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根植于中國國情、中國文化土壤,要充分理解認識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就離不開中國自身的文化語境。文化語境是一個語言學概念。文本的語境包括物理語境、語言語境、知識語境,這三種語境要素共同構成讀者或闡釋者的認知語境,也稱為文化語境。[18]要實現跨文化傳播,就面臨著語境差異乃至文化語境不對稱的情況。東方和西方存在“高語境”和“低語境”的文化之別,高語境文化中的信息交流多數存在于物質環境或內化于人身上,直接顯性傳遞出的信息很少,而低語境文化中的信息交流主要是顯性的,必須直白且通俗地大量呈現才能被他人所理解。[19]高語境的文化向低語境文化傳播時就會出現嚴重的信息丟失,甚至誤解。中華文化作為高語境文化,其優勢在于博大精深又無所不在的同化吸收能力,從古至今中華文化長于內化吸收外來文化,并由被外來同化者傳播出去,而從來不是西方“傳教士式”的主動文化擴張,從古代東亞國家對漢唐的學習到18世紀歐洲中國熱“東學西漸”皆是如此。鑒于此,尤其要加大“引進來”工作,讓海外人士沉浸式接觸體驗包括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內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沉浸式感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文化習慣和生活方式,以“內化吸收”實現“國際傳播”,以培養當代“利瑪竇”的精神培養一批真正懂中國、知世界的國際人才,將包括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內的中華民族現代政治文明帶出國門、帶向世界。
作者簡介:張家銘,山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
本文系山東省社科聯2023年度人文社會科學課題統一戰線理論與實踐研究專項(項目編號:2023—TZZX—14)及2023年度山東省社科規劃打造山東對外開放新高地研究專項(項目編號:23CKFJ24)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 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N].人民日報,2021-06-02(1).
[2]石泰峰.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 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J].求是,2024(17).
[3]K.E.Boulding.The Image: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120-121.
[4]馬得勇,陸屹洲.國家形象形成的心理分析[J].國際政治科學,2022,7(1):114-148
[5]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9[R].2020.09.16.
[6]張家銘.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國際傳播[J].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2(4):103-107.
[7]Ortmann S,Thompson M R.China’s obsession with Singapore:learning authoritarian modernity[J].The Pacific Review,2014,27(3):433-455.
[8]Halper S.The Beijing consensus: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in our time[M].Basic Books,2012;Heurlin C.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Ang Y Y.Aut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eijing’s Behind-the-Scenes reforms[J].Foreign Aff.,2018,97:39.
[9]Liao X,Tsai W H.Clientelistic State Corporatism:The United Front Model of“Pairing-Up”in the Xi Jinping Era [J].China Review,2019,19(1):31-56;Lawrence S V,Martin M F.Understanding China’s political system[J].CRS Report for Congress,2013;Eduardo Baptista. Explainer:Communist Party is not China’s only political party—there are eight others[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21-06-11.
[10]臧秀玲.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國際話語權的基本內涵與提升路徑[J].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4):122-131.
[1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83.
[12] Julia B.& Nathanael C.China’s“New Type of Party System”:A“Multiparty”System for Foreign Consumption?[J/OL].The Diplomat. August 17,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8/chinas-new-typeof-party-system-a-multiparty-system-for-foreignconsumption/
[13]Zhou D.The Non-affiliates in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how to Play a Role?[J].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s Públicas,2023,13(1).
[14]Wu Y.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s Science,2023,6(2).
[15]Bai Y.The Historical Logic Between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Democra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Research,2022,5(12):106-111.
[16]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 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N].人民日報,2021-06-02(1).
[17]黃天柱.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自信的“源”與“道”——一個基于政治學的分析框架[J].統一戰線學研究,2024(1):1-25.
[18]陳開舉.文化語境、釋義障礙與闡釋效度[J].中國社會科學,2023(2):184-203.
[19]徐敬宏,袁宇航,鞏見坤.中國國際傳播實踐的話語困境與路徑創新——基于文化語境的思考[J].中國編輯,2022(7):10-16.
(編輯:邱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