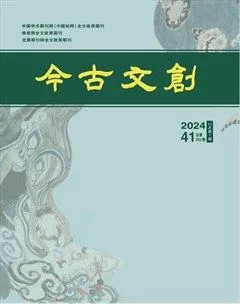《手中紙 , 心中愛》中的言語焦慮與身份認同
【摘要】本文解讀《手中紙,心中愛》中主人公杰克的成長過程中言語焦慮的獲得與消解,以及身份重構。兒童時期遭受的種族歧視使杰克討厭自己的華裔身份,并拒絕說中文,在美國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他鄙視中國文化并遭遇了自我認知的迷失。在被母愛所感動后,杰克最終理解了母親,理解了她所代表的中國文化。他與過去的經歷和解,開始重新學習中文,重構了自己的華裔美國人身份。
【關鍵詞】劉宇昆;《手中紙,心中愛》;語言焦慮;身份認同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41-002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06
一、引言
劉宇昆被認為是當代最為杰出的美籍華裔作家之一,他的成就見證了“21世紀華裔科幻作家的崛起”[1]15。他的短篇小說《手中紙,心中愛》出版于2012年,在美國受到廣泛關注,并斬獲了星云獎、雨果獎和世界奇幻獎三大獎項。《手中紙,心中愛》描述了出生在美國華裔家庭的男孩杰克在成長過程中獲得的言語焦慮及其對自我身份的追尋,這是一份有關失落﹑融合和再發現的記憶。
相較于國外學界對劉宇昆的廣泛關注,國內的相關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劉宇昆的翻譯成就上,而對劉宇昆小說的研究寥寥無幾,且大多聚焦于“中國神話”“技術倫理”“后人類主體性”及“族裔身份”等主題。
“身份”是美國華裔文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而語言是身份建構中的重要環節。主體通過對語言的選擇表達個體對一種文化的認同或抵抗,通過話語行為追求認同并定位文化身份。《手中紙,心中愛》圍繞語言與身份認同的關系,描述了一個華裔男孩成長過程中語言的遷延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身份的變遷過程,揭示了語言在文化身份建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本文以劉宇昆的《手中紙,心中愛》為藍本,分析了華裔美國男孩杰克言語焦慮的獲得與消解及其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在美國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由于文化沖突和種族歧視,杰克開始憎恨自己的華人身份,陷入身份困境,同時獲得了言語焦慮。最終,在母親的幫助下,他與種族歧視的經歷和解,重新學習中文,并接受自己作為美國華裔的雙重身份。
二、言語焦慮與種族歧視
語言焦慮,指的是“個體在語言課堂或任何使用語言的情境中所經歷的恐懼”[2]159。語言使用者在進行語言表達時感受到憂慮、排斥,或者懼怕。傳承語焦慮是常見的語言焦慮之一,指的是使用者在學習和使用傳承語的過程中產生的焦慮。良好的傳承語能力“有益于形成健全的民族認同,培養良好的家庭關系,是來自移民家庭的青少年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3]43,而傳承語焦慮的產生顯然不利于這一能力的發展。就傳承語焦慮產生的影響因素看來,華裔傳承語學習者的語言焦慮“明顯受到華裔身份認同的影響”[3]44。
在《手中紙,心中愛》中,主人公杰克言語焦慮的產生與他的雙重文化與種族身份密不可分。與作為第一代移民的父母相比,那些在美國出生和長大的年輕人更容易陷入身份認同的困境。他們生活在美國,并接受美國的教育,更傾向于認同美國文化。然而,在美國的文化價值體系中,他們卻往往不被認可。作為一個華裔美國混血兒,主人公杰克的情況則更為復雜。根據美國主流社會認定種族身份的“從下原則”和“一滴血規則”,混血兒的種族身份依據父母雙方中地位較低一方的種族身份而定。因此,即使父親是美國白人,擁有部分白人血統的杰克仍和母親一樣被視為中國人。杰克被排斥在兩種文化社會之外,被視為“局外人”[4]132——他與純粹的中國移民家庭有著一定的距離,又被拒絕平等地加入美國白人社會。在社區和學校生活中,杰克總會遭到直接或間接的歧視。混血身份使他被認為“偏離正常”[4]132,因此成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從而陷入難以掙脫的身份困境。
種族歧視是杰克陷入身份困境的顯著表征,它最直觀地體現在言語暴力上。杰克的母親是來自香港的郵購新娘,面對陌生的語言和環境,她選擇延續中國文化傳統,包括堅持講中文,并教孩子說中文,還給孩子折各種神奇的折紙玩具。當杰克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并不排斥母親用中文和他交流,并且會說中文。他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覺得母親的折紙術十分“特別”[5]179,對紙老虎等玩具十分珍視。然而,杰克十歲的時候,聽見了新鄰居對他充滿惡意的評價——“混血兒都怪怪的,像是發育不全。瞧他那張白人面孔配上一雙黃種人的黑眼睛,簡直就是小怪物”[5]181。此外,她們還質疑他不會講英語,并認為他應該有個中文名字。父親有事外出,而母親不懂英文,年幼的杰克一個人獨自面對了這場語言暴力,他第一次直觀地感受到自己是受排斥的“他者”。在這場對峙中,英語作為主流文化的語言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漢語則是缺席的、被壓制的。英語及其所代表的白人文化是優越的,而漢語及其所代表的中國文化處于劣勢地位,這種觀念由此在杰克心中埋下種子,是杰克言語焦慮獲得的誘因。
與鄰居家的男孩馬克的沖突使得杰克的言語焦慮由隱性變為顯性。在杰克向馬克介紹母親折的紙老虎玩具時,他先是說了中文“小老虎”,之后停頓了,接著用英文重新說了一遍。杰克說完中文后下意識的停頓是他言語焦慮的表現之一。此外,語言的差異性也造成了杰克對西方文化和美國社會更深刻的“他者”感受,這是一種“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感受”[6]106。馬克對杰克分享玩具的友好行為并未給予正面反饋,反而嘲笑杰克的折紙老虎是垃圾,并把它撕碎了。被撕破的紙老虎實際上象征著中國文化在美國文化主導的社會中的脆弱性。更令杰克手足無措的是,馬克還羞辱了他的母親——“沒準兒你老爸買你媽的時候都沒花這么多錢”[5]182。言語攻擊毀壞了母親在杰克心中的崇高形象,母親樹立的中國文化信念隨之崩塌。
這場沖突還延續到了校園中,杰克遭到了馬克和其他同學的排擠。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霸凌侵入了杰克的家庭生活和學校生活,杰克無處可避。由此,杰克陷入身份困境,他對自己的華裔身份失去了信心,開始為自己不是一個純正的美國人而感到羞愧[5]182,他決定拋棄從母親那里學到的所有中國傳統,屈從于美國主流文化。此外,他的言語焦慮也進一步升級,開始拒絕用中文與母親交流。
三、言語焦慮與文化認同
主人公杰克的語言偏好從中文向英文的轉變表明語言身份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它“不是一種給定的、由出生地或父母自動授予的成員身份,也不是語言特征、文化制品或具有明確釋義的群體習俗的積累”[7]3,而是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呈現出一種流動變化的特質。隨著時間的推移,個人的成長經歷、情感認知的變化不斷地改變和塑造著一個人的語言身份。在白人文化主導的社會中,杰克所經受的文化焦慮與認同危機使得他對中文產生了劇烈的情感變化,他開始對中文表現出強烈的排斥心理。拋棄中文是杰克拋棄中國文化身份,擁抱美國文化邁出的第一步,也是他嘗試擺脫言語焦慮的努力。他不再說中文,也不再遷就母親糟糕的英語水平,多次要求母親說英文——“英語!說英語!”“我很好!不要你管!我只要你給我說英語!”[5]183他要求母親不再做中國菜,并強迫母親說英語,拒絕用中文和母親交流:
如果媽媽和我說中文,我就拒絕回答。久而久之,她只好和我說英語了。但是她蹩腳的口音和離譜的文法讓我覺得很丟人。她出錯,我就挑錯。終于,她不在我面前說英語了。[5]184
拒絕使用漢語造成了杰克與母親之間的語言隔閡,阻礙了兩人的交流,使得母子倆關系僵化。
語言的轉變同時也意味著文化身份的轉變。“語言對身份認同的構建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將人們對世界的經驗抽象化,使得語言人形成了對自我和他者的概念”[8]22。對英語的偏好及對漢語的排斥恰恰展現了杰克文化身份的轉變。一旦成為英語文化的擁護者,杰克就從種族歧視的受害者轉變為施暴者,他鄙視母親并憎恨她的華人身份。在與母親的戰斗中,杰克代表了強大的美國文化,而他的母親代表了中國文化。就像他被馬克羞辱一樣,杰克也羞辱了他的母親。他不可避免地以東方主義的態度對待他的母親和中國文化。對于杰克來說,母親的折紙魔術只是來自遙遠東方國家的幻想,而他真正理解和認可的是他現實生活無處不在的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因此,一旦他意識到母親帶給他的華裔身份使他在美國主流社會中處于劣勢地位,杰克理就所當然地疏遠了母親,甚至輕視她,轉而尋求白人社會的認可。這表明美國社會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已經內化到杰克的思想中。他既因為華裔的身份而受到白人的歧視,卻又鄙視他的中國母親。這是造成他身份困境的原因之一。
杰克對美國式家庭的追求使得家庭氛圍很快發生了轉變,食物變成了美式餐點,杰克和美國青年一樣玩電子游戲,學法語,努力地追求“美國式的幸福生活”[5]184。“在日常生活中,決定與誰交往,遵循哪種生活方式,說哪種語言等等,可能意味著要在不同的文化之間做出選擇。這些決定可能最終會對自我概念產生影響”[9]259。在杰克看來,美國式的生活方式能讓他更好地融入美國社會,享受美好的生活,而中國文化只會令他飽受歧視,帶來恥辱的感受。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杰克拒絕說中文并抗拒一切和中國有關的事物,并將美國社會對華人的歧視內化為自我歧視。換句話說,“種族歧視使他自我憎恨”[9]793。他渴望拋棄生活中所有與中國相關的東西,并把自己遭受的歧視歸咎于他的華人母親,從而達到擺脫恥辱感受的目的。這種做法雖然使他擺脫了言語焦慮,他不必再為自己說中文而感到羞愧,但從本質上來說,無論杰克多么努力地使自己像個白人,他也無法擺脫自己的華裔身份。他放縱自己陷入自我憎恨的情緒中,無法準確地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
四、言語焦慮與身份重建
杰克的身份重建得益于理解母親并重新建立與中國文化的聯系。杰克與母親在語言上的沖突使兩人日漸疏離,杰克對母親的態度甚至可以稱得上冷漠。他嫌棄母親擁抱和親吻的動作夸張而丟人;他將母親做給他的折紙動物全部壓扁扔進閣樓;母親的英文水平日益提高,但他仍拒絕和母親交流;母親病重垂危,杰克卻一心想著自己的求職計劃,不等陪伴母親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已經急匆匆飛往加州。杰克的冷漠源于他不理解母親,也不愿放低姿態了解處于弱勢的文化群體。在主流文化的沖擊下,他選擇了逃避母親,并直截了當地切斷自己與中國文化的聯系。這種簡單粗暴的自我隔離持續到母親去世仍未獲得轉變。然而,不論如何,母親的一言一行還是在杰克的心里埋下了一粒種子,靜待破土而出的契機。
母親去世,杰克的父親決定出售房屋,杰克在整理房間時再次見到了小時候被撕碎的折紙老虎。小老虎已經被母親用紙膠帶粘好了,當杰克觸碰它的時候,它恢復了活力。神奇的折紙老虎讓他回憶起童年時期與母親溫馨相處的點點滴滴,杰克想起母親病床前的殷殷囑托,以及她反復提起的“愛”字。然而母親已同他的童年記憶一般離他遠去了,只留下與日俱增的愧疚與遺憾。當杰克意外發現折紙老虎的背后是母親寫給他的信時,他想起母親讓他每逢清明要記得思念母親的請求。杰克立刻確認了當日正好是母親提到的清明節,他的內心十分激動,并對讀懂信中的內容產生了強烈的渴望,然而杰克不認識漢字,他只能用記憶中模糊的中國話一遍遍向中國游客求助,為了讓中國游客理解得更清楚,他還用英文重復一遍。這一舉動是他身份重建的關鍵一步。
在向中國游客求助的過程中,中文占據了主場,而英文充當了理解中文的輔助手段,杰克不再將中國文化視為可恥,而是重新接受中文進入自己的生活,并且主動地尋求對母親所代表的另一種文化的理解。在一個中國女人的幫助下,杰克從信中了解到母親過去的痛苦經歷:母親從河北到香港投靠親人,卻被人販子賣到富裕家庭做仆人,最終通過郵購新娘的方式來到美國。面對不同的語言和陌生的生活環境,她過著孤獨的生活。杰克與她及祖父母相似的臉龐給了她安慰。她教杰克說中文,并為他折紙動物,這讓她在異國他鄉有了歸屬感。她對杰克充滿深深的愛和期待,而被杰克疏遠使她十分悲傷。文字傳情,這封信使杰克理解了母親,他明白了母親為什么執著于教他說中文,他請求為他讀信的中國女人教他寫“愛”字,在他的一遍遍臨摹中,母親多年的愛終于得到了回應。杰克不再排斥說中文,也不再憎恨自己的華裔身份。在“愛”里,他與自己的成長經歷和解,從而擺脫了身份困境。
在清明節這個充滿中國傳統的、具有悼念親人的意義的節日,杰克用中文求助一個中國女人為他讀信,并學習中文的“愛”,哀悼母親并乞求原諒,這象征著杰克對母親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也表明杰克言語焦慮的完全治愈。過去,他拒絕說中文,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完全的美國人。現在,在母親的愛的驅使下,他開始學習中文,不再拒絕自己的華裔身份。他走出了身份困境,重構了自己作為美籍華人的身份。
五、結語
劉宇昆的《手中紙,心中愛》聚焦于華裔杰克的成長經歷,展現了他言語焦慮的產生與消解及身份重構。兒童時期遭受的種族歧視經歷使杰克討厭自己的華裔身份并拒絕說中文,在美國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他鄙視中國文化并在自我認知上產生了混亂。被母愛所感動,杰克最終理解了母親,理解了她所代表的中國文化。他與過去的經歷和解,開始重新學習中文,從而走出了身份認同困境,重構了自己的華裔美國人身份。
參考文獻:
[1]Han Song.Chinese Science Fiction:A Response to Modernization[J].Science Fiction Studies,2013,40,(1): 15-21.
[2]Gardner,Robert C.and Peter D.MacIntyre.On the Measurement of Affective Variabl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J].Language Learning,1993,43(2):157-194.
[3]蕭旸.民族認同與傳承語焦慮[J].語言戰略研究, 2017,(3):38-55.
[4]陳華.美國文學中的混血人形象評述[J].外國文學研究,2000,(4):128-133.
[5]Liu,Ken.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M]. New York:Saga Press,2016.
[6]劉俊.“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尋——美國華文文學的一種解讀[J].南京大學學報,2003,(5):102-110.
[7]Zentella,Ana Celia.Growing up Bilingual: Puerto Rican Children in New York[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7.
[8]王浩宇.民族交融視域下的語言使用與身份認同[J].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9,(4):16-22.
[9]Noels,K.A.,Pon,G.,and Clement,R.Language, Identity,and Adjustment:The Role of Linguistic Self-Confidence in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J].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6,15(3):246-264.
[10]Hang,Yuan.An Analysi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Paper Menagerie[J].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2020,10(9):790-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