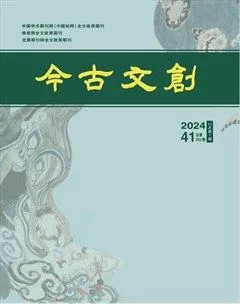明代中后期基層賦役改革的橫向互動
【摘要】明代中后期湖南基層賦役制度弊竇叢生,官民達成共識后,合力推動了一場賦役改革。在湖南茶陵州、攸縣及善化縣的賦役改革過程中,借助官員流動和官紳交往網絡等媒介,鄰省南昌縣的賦役改革有益經驗成為茶陵州的重要制度資源,而茶陵州改革過程中的重要創制《便民正規》復被鄰縣攸縣所借鑒。在攸縣清丈中,地方官員通過合理利用官紳交往網絡,使跨省界田清覆難題迎刃而解。基于湖南的例證可知,明代中后期的基層賦役改革不僅具有明顯的自下而上的特點,還呈現出跨區域橫向互動的特點。賦役改革經驗的跨區域傳播是這一橫向互動的核心內容,而官員的跨區域流動和官紳之間良性的交往網絡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關鍵詞】賦役改革;橫向互動;官紳交往網絡;明代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41-007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21
明代賦役制度研究自梁方仲發表《一條鞭法》以來,學界已展開卓有成效的研究,相關成果極為豐碩。①以往研究大致循兩條路徑推進,其一為側重對制度規定層面的分析與闡述,多取傳統制度史與全國性視角;其二為側重對制度實踐層面及其所引致之社會變遷的分析,多取社會史與區域性視角。②與此前歷代自上而下的賦役改革不同,明代中后期的賦役改革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對此,學界已有辨明。③其實,明代中后期的賦役改革不僅存在一個自下而上的縱向互動過程,還存在一個不同地區之間的改革互相影3jGHKqvpHTDkuoyjrw838pBhRwtlrY+RAlXf8ktnqK4=響的橫向互動過程。對此,學界卻多未論及。有鑒于此,本文擬通過仔細剖析明代嘉萬年間湖南長沙府的賦役改革實踐,初步總結明代中后期湖南基層賦役改革中的橫向互動模式及其特點,以期進一步豐富對明代賦役制度史的研究。
一、賦役改革經驗的跨區域傳播
在明代,長沙府位于湘江中下游流域,東界江西袁州府,西、南、北則分別與湖廣辰州府、衡州府、岳州府接壤。長沙府下轄茶陵州、長沙縣、善化縣、湘潭縣、攸縣等一州十一縣。其中攸縣在長沙府南三百六十里,東界江西安福縣,北界醴陵縣,西界衡山縣,南界茶陵州。[1]1266-1268茶陵州則在攸縣之南,東與江西相鄰。攸縣、茶陵州地處羅霄山脈中,境內多為山地丘陵,很多居民自稱明清時期從江西遷來,當地方言與江西較為接近。④
明朝定鼎之后,明廷以魚鱗圖冊及黃冊互為經緯,并創立里甲、糧長等制度,在全國范圍內重建賦役制度。但經過百余年的演變,到明代正德、嘉靖年間,湖南長沙府茶陵州及攸縣的賦役制度已弊竇叢生,或則詭寄田地而飛灑稅糧,或則征收無度而逋賦嚴重,或則徭役簽派之權操諸官吏里胥而賣富差貧。嘉靖年間,劉應峰談到攸縣清丈時即指出:“今天下田賦浮詭之弊萌滋久矣,故豪宗右姓之所磐石率多無稅之田,而沉痛茹苦空輸無田之稅者倍在畸門窶子輩焉,積歲累世,固根深穴,雖強察吏莫之詰也”[2]467-468。又如《茶陵州志》載:“(茶陵州)均徭……舊例以一七甲、二八甲、三九甲、四十甲、五六甲一年一審,分別上中下銀力二差,中間賣富差貧者多”[3]211,“舊志當年里長審定官丁,輪流撥差,十戶九逃”[3]212。長沙府茶陵州、攸縣賦役制度的敗壞使得民不堪命,于是苦于賦役繁亂的民眾產生了強烈的改革訴求。與此同時,茶陵州、攸縣的州縣地方官出于為民紓難及個人政績的考量也有著較為強烈的改革沖動。到嘉靖年間,隨著官民逐漸達成共識,一場官民合力推動的賦役制度改革在長沙府茶陵州及攸縣拉開序幕。
嘉靖三十三、三十四年間,茶陵州知州劉高針對茶陵州田賦浮詭之弊議舉核田,希望通過核田來清理田賦。然因舉措不當,“約田程功,一切驅以苛峻”[2]468,致使“群役惴惴受事,如赴湯火”,“事未就而訟牒起”[2]468。由于遭到吏民抵制,劉高的改革最終失敗。劉高的改革雖然沒有取得成功,但為隨后的改革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嘉靖四十四年,黃成樂就任茶陵知州,黃氏有感于茶陵賦役制度的敗壞,于隆慶一、二年間再次推行改革。鑒于劉高改革的失敗,黃成樂采取了比較審慎的態度。他積極爭取地方士紳的支持,接納地方士紳劉應峰參與改革。劉應峰曾于嘉靖三十五至三十七年出任江西南昌縣知縣,在任內推行賦役改革,成效顯著。據章潢《新修南昌府志》卷十六載:
劉應峰,字紹衡,茶陵人。由進士宰南昌,邑當會省,事難綜核。公以鎮靜處之,一不為勞。均丁糧以簽差役,省工食以覈機兵,開十限以定追徵,均鋪行以蘇偏累,革民船以省差擾,政績為一時之最。[4]314-315
劉應峰后來因政績卓越被擢為吏部主事,歷江西參議疏乞終養。此時已回到家鄉茶陵,成為一位究心理學,著述自娛的鄉紳。在黃成樂的虛心邀請下,劉應峰再度涉足自己曾取得傲人成績的賦役改革領域,將自己豐富的賦役改革經驗獻諸桑梓。在黃成樂與劉應峰等的合力謀劃下,最終于隆慶年間議立《便民正規》。《正規》“仿江右一條鞭法,凡本州一應錢糧、均瑤、公費等項,歲當輸于官者均派于概州丁糧”[2]504,“征銀入庫,隨時支用”[3]214。由于得到劉應峰等擁有豐富賦役改革經驗的士紳的協助及地方民眾的支持,黃成樂的一條鞭法改革得以較為順利地推行。
茶陵州借鑒江西的改革經驗成功完成一條鞭法改革,直接推動了攸縣的一條鞭法改革。茶陵州的一條鞭法改革取得成功之后,鄰縣攸縣民眾“鳴諸上臺,求仿行焉”[2]504,表達出強烈的改革訴求。于是攸縣知縣徐希明順應民意,引入茶陵知州與地方鄉紳合議的《便民正規》,開始一條鞭法改革。
徐希明在《平賦役序》中詳細記載了攸縣推行一條鞭法改革的情形。據徐希明記載,攸縣民眾見茶陵州議立《政規》 ⑤后順利推行賦役改革,乃請求仿照茶陵州進行賦役改革。這時適逢湖南撫臺下達賦役改革公文,徐希明遂召集地方士民在公所商議賦役改革事宜,最終達成三點共識:一是額辦、派辦和京辦等項目維持原數;二是比照原頒會冊與茶陵政規,如果原頒會冊所載關乎攸縣風教、解運、民瘼等公費較少,則相應增加;三是與攸縣官府有關的公費,就算茶陵政規有所改革,也全部依據湖南原頒會冊,不敢予以增加,以免讓人覺得官府進行一條鞭法改革是為了謀取私利。[2]504
據上所述,攸縣的一條鞭法改革有三點頗值得注意:第一,徐希明在“公所” ⑥召集地方士民商議賦役改革事宜,由此可見地方官員不敢輕視地方權勢對賦役改革的影響。第二,改革過程中,地方官員注重結合鄰州已有的成功改革經驗及地方士民的訴求,折衷損益,而不是原封不動地執行上級政府所頒布的政策條文。第三,改革者通過將賦役改革項目劃分為不同部分,即與地方官府有關的公費全部依照湖南原頒會冊,與民間事務有關的公費則借鑒茶陵的改革經驗予以增減,實際上是劃分了地方官府與地方士民之間的權力邊界。由此可見,攸縣一條鞭法改革是攸縣官府、上級政府和地方士民三方勢力合力推動,折衷損益的結果。
由于攸縣知縣徐希明悉心謀劃,積極爭取地方士民的支持,其一條鞭法改革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徐希明也因此獲得后人很高的評價,《攸縣志》稱其“萬歷中由舉人知攸縣,蒞任數年,丈田清賦,貧者無無田之糧;清江西界田,豪民無無糧之田”[2]257。
在茶陵州及攸縣的賦役改革過程中,鄰省南昌縣賦役改革的成功經驗通過退休官員劉應峰這一重要媒介而成為茶陵州改革的重要資源,進而茶陵州改革過程中的重要創制《便民正規》又被鄰縣攸縣所借鑒。可見,當基層賦役改革的經驗經由官員的流動和官紳社交網絡在地區間傳播時,賦役改革的跨區域橫向互動便自然而然地發生了。
明代中后期湖南基層賦役改革過程中,賦役改革經驗跨區域傳播的案例尚有不少,下面試再舉兩例。
據上文可知,徐希明在攸縣知縣任內,借鑒毗鄰茶陵州的賦役改革經驗,在攸縣成功實現一條鞭法改革和田畝清丈。徐希明卸任后,董志毅接任攸縣知縣。董志毅后來又赴湘潭縣任知縣,并在湘潭縣任內推動湘潭縣一條鞭法改革。據李騰芳《征丁議》記載:董志毅赴湘潭縣后,清查丈糧冊,想改變賦役征派的辦法,讓每五石糧兼出一丁之銀,從而廢棄舊的征派辦法,以為這樣可以用私惠取悅于沒有田的人。但是湘潭縣的民眾不肯遵行新的賦役征派辦法,最終導致新的方案被束之高閣幾近五十年之久。[5]599
董志毅將其在攸縣任職期間所獲得的賦役改革經驗用于推動湘潭縣賦役改革是不難想見的。
萬歷二十八年,善化縣知縣陳弘乘在推動善化縣驛傳改革時也借鑒了湘陰的改革經驗。對此,陳弘乘的《善化官馬議》記之甚詳:
“今日之最為民累者無如馬遞一節……合無比照湘陰事例,除長善兩縣量存馬數匹為縣馬,余總合兩縣之馬,通付付臨湘驛走遞為官馬,不惟馬數多而易于應差,且馬屬于官而乘騎者亦知所顧恤矣。”[5]592
二、官紳交往網絡與攸縣清丈
丁糧、徭役及公費等項的攤派,是湖廣省原頒章程及茶陵《便民正規》主要關注的領域,而田畝清丈尚未涉及。賦役攤派領域的改革固然可以做到既有負擔下的相對公平,但難以解決稅賦虛浮造成的民不堪命,可謂治標不治本。因此,徐希明在推行賦役攤派一條鞭法改革的同時,于萬歷三年進一步主持了田畝清丈,以期從更為根本的層面上解決攸縣的賦役問題。
明代嘉萬年間,攸縣的豪宗右族兼并土地,當值的糧遞在征收押解田賦的過程中也上下舞弊。[5]619徐希明就任之初,詢問民事,為虛糧所苦的民眾每天紛集于庭下[2]468,徐希明乃決定清理攸縣的虛糧。開始,徐希明想根據原有冊籍逐都清查,但很快意識到田契之內的虛糧可以查到,但田契之外的虛糧無法查到;留存有戶口版籍的虛糧可以查到,但是沒有戶口版籍的虛糧無從查到[5]619,要從根本上清理虛糧問題只有清丈一途。其時,恰逢都民洪邦里等連名具告,懇請清丈田畝,徐希明乃借機召集攸縣士民商議田畝清丈事宜。邑中士紳多表示贊同清丈,然亦有反對者,徐希明“獨毅然抗論,謂能身冒議端,毋令重吾民困也”[2]468,核田之舉由此敲定。
萬歷三年十一月,徐希明率領民眾在城隍廟發誓,隨后開展清丈活動。清丈的時候,每個都推選十名公正的人來監督清丈行為,再推舉兩個人負總責,與地報、知識人等一起對清丈用的繩罩進行編號,以防止民眾作假。[5]619徐希明也時常親往監視,以確保田畝清丈的順利進行。[2]468攸縣田畝清丈之事歷時七個月,丈畢,將逐都田地細數登記刊印之,家給一冊。[5]619在清丈過程中,徐希明還順利清覆了攸縣與江西安福縣之間的界田。
在攸縣與安福縣交界處,居住著楊氏大家族。楊氏買了攸縣民眾的田地而逃避田稅,攸縣部分民眾亦趁機隱逸自己的賦稅,并詭稱是楊氏所逸。此前攸縣官府誤以為賦稅全部為楊氏所逸,于是讓攸縣民眾代為輸納。[6]235。楊氏所逸之稅皆由攸民代輸,必然加重攸民的負擔,最終造成“(攸縣)四十八都之糧名存而實亡者積百五十石,當年糧遞因之破產流移者不啻十之四五”[2]467的嚴重后果。本來,橫跨兩省的界田清覆因牽涉不同政區管理者的協作,更牽扯到地區間的稅賦利益博弈,往往不易處理,所謂“以吳楚勢懸隔,無能焉”[6]235。但是,徐希明善于利用官員與地方士紳之間的交往網絡,借助當地頗有影響的士紳之力,使清覆界田一事迎刃而解。
安福楊氏有一位姻親叫劉元卿,乃當世名儒。劉元卿因忤張居正,科舉之路被阻,于是居鄉講學。但他不忘經世之志,對于“邑大便利,無不為當事言之,動中款會”[6]1551。因此,劉元卿頗得地方長官敬重,以致“縣大夫至者,皆就而問政可否、緩急之宜”[6]1551。在此次清丈中,徐希明在命令約正張思乃“檄諭諸楊”的同時,鑒于劉元卿在安福楊氏中的影響力,寫信給劉元卿,希望他出面勸誡楊氏配合界田的清理。劉元卿接到徐希明的委托后,乃“與清泉(即楊氏族人)戶曉家喻”[2]467之。在姻親劉元卿的勸誡和知縣徐希明的諭令之下,楊氏在族人楊子孝的帶領下,冒暑雨履畝清覆。最終“凡攸之田,悉屬丈明,登冊以報”[2]467,共得所逸之稅四十七石,楊氏表示愿為輸納。⑦安福楊氏將逃逸的賦稅上報后,徐希明當即宣布楊氏歸附正義,因為他們的倡導而成就了攸縣清丈的美事,并贈送“尚義”的門匾給楊子孝,以表彰他的首功。[5]611。界田清覆之后,徐希明擔心楊氏后人可能再次逃避輸納賦稅的義務,于是算明賦稅額度,拔田給四十八都,讓該都各甲分種,以其收獲充繳賦稅,永遠不許買賣,并樹立碑石,以垂不朽。[2]467
由于徐希明舉措得當,攸縣清丈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首先,此次丈田清理出大量的逸稅田畝與人丁,從而使官府所掌握的財賦來源大增。據徐希明《固本樓記》載,攸縣原有田地三十五萬畝,清丈后增至七十五萬余畝。[2]471清雍正五年(1727),攸縣知縣陳文言也提到明季徐希明丈田后,攸縣田畝數定為七千二百九頃零。[5]620由此可見,徐希明確實清查出比原額更多的逸稅田畝和丁數。其次,由于清丈后稅基擴大,且秉持“田有沃瘠不等而科糧均以一則,俾滑胥積算不得操贏縮于其間”[2]468的原則,在稅賦總額不變的情況下,攸民的稅賦負擔明顯減輕且更趨公平,所謂“及考其成籍,糧無溢額,邑人獲減損者十之七八,而間有一二稍增益者,亦寂無譁語”[2]467是也。
攸縣核田之舉,也獲得了當地紳民的認可。縉紳庶民無不歡呼雀躍,認為清丈之后確立的新賦稅征收辦法非常方便,于是謀求立碑來記錄徐希明的功德。[2]468攸縣庠生龍尚寶、劉騰生、譚階及陳制⑧請求茶陵州的劉應峰撰寫文章來記錄這件事。徐氏也因其丈田清賦之功,得以榮列“名宦”,名垂青史。
攸縣的界田清覆橫跨湘贛兩省,更牽涉到地區間的稅賦利益,本不易解決,攸縣知縣徐希明通過合理利用其與劉元卿等地方士紳之間的交往網絡,使這一棘手問題迎刃而解。由此可見,官紳之間良性的交往網絡不僅可以促進賦役改革經驗的傳播,還可以在跨區域的糾紛調解中起到潤滑劑的作用。
三、結論
有明一代,賦役改革幾乎貫穿始終,而以中后期之一條鞭法改革及萬歷清丈為高潮。明代嘉萬年間,湖南長沙府茶陵州及攸縣與國內很多地方一樣稅糧虛浮、徭役繁重,再加上胥吏里甲舞弊、豪強劣紳侵凌,逋賦逃役時見,民不堪命。因此,官民雙方都萌生了強烈的改革賦役制度的沖動。嘉靖年間,茶陵州知州劉高導夫先路,隆慶、萬歷時,茶陵州知州黃成樂、攸縣知縣徐希明追踵前賢,最終在紳民的支持下實現了賦役改革目標。通過仔細剖析明代嘉萬年間湖南茶陵州及攸縣的一條鞭法改革及田畝清丈,我們大致能得到如下幾點認識:
首先,學界關于明代賦役制度史的研究已表明,明代中后期的賦役改革表現出明顯的“自下而上”的特點。通過對明代中后期湖南長沙府的賦役改革實踐的分析可知,明代中后期的賦役改革不僅表現出明顯的自下而上的特點,還呈現出跨區域橫向互動的特點。賦役改革經驗的跨區域傳播構成了這種橫向互動的核心內容,而官員的跨區域流動和官紳交往網絡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其次,以往的研究多強調基層行政中官紳勾結而導致徇私枉法,欺壓良善的一面,而較少關注官紳之間的良性互動對基層行政的推動作用。來自攸縣田畝清丈的案例表明,良性的官紳交往網絡在處理某些地方行政時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對于官紳之間的互動似不可一概而論。
最后,在基層賦役改革中,地方官員往往是倡導者和直接領導者,他們根據已有改革經驗、上級政策和地方實際折衷損益,探索適合地方實情的改革方案,表現出較大的自主性。與此同時,地方社會尤其以士紳吏役為代表的地方權勢的改革訴求與人心向背往往能左右改革的走向與成敗。因此,官民之間是否存在通暢高效的協商機制就顯得格外重要。可以說,成功的基層賦役改革往往是官民共同推動的結果。
注釋:
①參見梁方仲《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等,相關研究數量眾多,不一一列舉,可參閱賴惠敏《明代賦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顧》,載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出版組1993年版。
②前一路徑可以梁方仲、唐文基為其代表,后一路徑可以劉志偉、鄭振滿為其代表。梁氏在《明代一條鞭法年表(初稿)》中指出,其所著《一條鞭法》《明代江西一條鞭法推行之經過》《釋一條鞭法》及《明代一條鞭法的論戰》“多半側重在制度方面的分析和闡釋”“至于歷史方面,除在第二篇及第四篇的一部分外,都無暇多說”。《明代一條鞭法年表(初稿)》雖側重歷史方面,但終究與劉志偉、鄭振滿等試圖從社會史和區域史的視角來研究明代戶籍賦役制度改革旨趣各異。唐文基關于明代賦役制度的研究參見氏著《明代賦役制度史》。劉志偉、鄭振滿關于明代賦役制度的研究分見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及鄭振滿《明清福建的里甲戶籍與家族組織》(《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③參見萬明《明代賦役改革模式及其特點初探(上)——從海瑞的縣級改革談起》 (《河北學刊》2016年第3期)及《明代賦役改革模式及其特點初探(下)——從海瑞的縣級改革談起》(《河北學刊》2016年第4期)。萬明在其論文中指出明代的賦役改革是自下而上的過程,并試圖從縣、府、省級改革及其官員群體出發對明代賦役改革模式及其特點做出初步探討。
④具體可參見譚其驤《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編》,載《史學年報》1932年第4期;何炳棣《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曹樹基《湖南人由來新考》,載《歷史地理》(第九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⑤即茶陵州知州黃成樂所編定之《便民正規》。
⑥在明代,公所一般是商人或地方人士集會議事的場所。
⑦安福縣致使攸縣四十八都之糧名存而實亡者,積百五十石,楊氏自報逸稅四十七石,剩下的一百零三石,或另有隱匿之情弊,則未可知也。
⑧陳制乃劉應峰姻親,在攸縣一條鞭法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茶陵《便民正規》很有可能是陳制從劉應峰處獲得。
參考文獻:
[1]薛綱,吳廷舉.(嘉靖)湖廣圖經志書[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2]趙襄等.(同治)攸縣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
[3]福昌等.(同治)茶陵州志[M].臺北:成文出版社, 1975.
[4]范淶.(萬歷)新修南昌府志[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5]呂肅高.(乾隆)長沙府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6]劉元卿.劉元卿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作者簡介:
葉再興,男,湖南醴陵人,長沙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明清社會經濟史。
黃子萌,女,湖南武岡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
基金項目:本文為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課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視域下近代中國戶政制度建構研究”(項目編號XSP22YBC06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