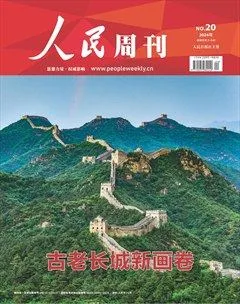公益基金助力長城保護

自1984年“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活動開展以來,我國社會力量參與長城保護工作已經走過40年。40年后,新生代的社會力量是如何發揮優勢,參與到長城保護公益項目中的?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文化保育組項目經理尉舒雅向本刊記者講述了這支年輕團隊的創新嘗試。
長城有其他文化遺產難以企及的特色
記者: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與長城保護是如何結緣的?
尉舒雅: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參與長城保護項目,是在2014年,整整10年前。當時,騰訊地圖想要做一個長城街景的技術探索,所以做了一系列的360°長城街景,團隊開始接觸長城并思考,長城到底是什么。
團隊中的工作人員,對長城的認識并不一致。我來自西北,對長城的印象停留在小時候夯土長城的形態;到北京上學后,見到了八達嶺長城、居庸關長城、慕田峪長城,才知道原來北京的長城是磚石的。項目團隊成員心目中的長城各有樣貌,每個人對長城的認知都天差地別。這些對長城的差異性認知,一定程度上局限于區域的認識。
基于認知的不同,我們開始思考,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種類型的長城?我們也開始探索,長城到底是什么樣的,應當對長城形成一個什么樣的概念,應該怎樣理解長城?2014到2016年,在這樣的思考和探索中,我們結識了很多專家,以及一些社會公益團隊。
經過與諸多專家的交流,我們認識到,長城在建筑材質、形態、用途等方面,都展現出不同的延伸。我們由此發現,長城不是一個點,也不是一段墻或一條線,它可能是一個區域、一個片、一個面積性概念。因此,有一些專家認為,長城是一個系統;也有一些專家認為,長城是一個傳統文化帶。但無論如何,長城都是一個有空間、有面積的概念,這是很多其他文化遺產難以企及的、長城獨有的特色。
2016年,我們和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攜手成立了一個長城保護公益專項基金,專門用于支持長城保護的一系列公益活動和公益項目。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希望向大家科普,到底什么是長城,我們能夠為長城做什么。
將數字化引入長城保護記錄工作
記者: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開展的長城保護工作,與40年前開展的“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社會贊助活動有怎樣的不同?項目團隊是如何使用現代科技手段推陳出新,引導社會公眾參與到長城保護工作中的?
尉舒雅:我們同樣是資助長城的保護修繕,基于保護修繕的具體項目,我們做了很多模式上的探索和創新。比如,箭扣長城南段保護修繕項目開啟了雙甲方合作模式、實施設計師駐場、引入數字化記錄;在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長城保護修繕項目中,我們嘗試了設計施工一體化;在箭扣長城東段保護修繕項目中,我們嘗試了公眾參與路徑的多元探索。
騰訊的優勢是技術和傳播。我們在長城做了兩個數字化項目,一是聯手北京大學開展的數字化記錄,二是由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辦公室、國家文物局指導的“云游長城”小程序。
2018年開工的箭扣長城南段保護修繕項目中,我們引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在152號敵樓及兩側邊墻嘗試做了長城數字化工作,以考古清理指導修繕工程清理,采用了無人機攝影測量、全景攝影和衛星定位等數字化手段,在修繕工程中分別于干預前、清理中、修繕施工中和竣工后等重要階段對試驗段進行數字化記錄,形成由4次攝影測量模型和全景圖像數據組成的試驗段“源場景”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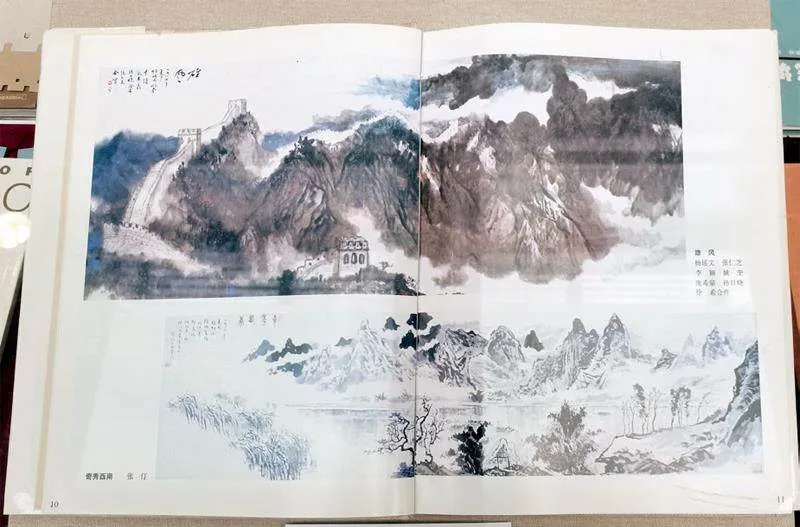
“云游長城”小程序于2022年6月11日上線,是基于天津大學建筑學院采集的整套明長城影像數據、長城小站整套明長城分布GIS數據,由騰訊用戶與研究體驗設計部產品團隊規劃設計,騰訊游戲團隊的游戲技術、騰訊云技術等共同搭建的,開發、測試歷經1年多。“云游長城”利用游戲科技,展示了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長城現場,實現了考古、清理、砌筑等修繕工藝的沉浸式體驗,趣味性地傳播長城文化內涵和保護修繕的科學理念,多角度解讀并展現長城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的創新方式,為推動文物活起來、拓展對外文化交流、提升國際傳播提供寶貴經驗。同時,小程序通過“小紅花”助力公眾的線上行為轉化為公益項目,直接建立公眾與文化遺產保護的聯系,是科技在文保及公益領域實現創新應用的又一標志性范例。
長城保護公益成果亮點紛呈
記者:在過去10年的長城保護宣傳工作中,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還有哪些成果值得分享?
尉舒雅:我們想,既然參與長城保護,是不是應當記錄一些東西讓大家看一看,原來長城保護是可以這樣做的。比如,長城是怎樣修繕的,修繕前后是怎樣的情況,長城與周圍的人是怎樣的關系,等等,我們都會用鏡頭忠實記錄下來。
2017年,我們開展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長城保護修繕項目時,同步開展了修繕記錄項目,經過4年的積累,最終形成了一部記錄喜峰口段長城修繕過程及沿線村民生活故事的電影紀錄片《筑城紀》。影片通過生動的畫面和感人的故事,展示了長城的歷史變遷和修繕的艱辛歷程。我們也希望通過這部紀錄片,讓更多人全面了解長城的歷史與現實。今年,我們和騰訊新聞等多家機構合作開展了長城沿線放映工作,長城腳下的很多村民都在觀看中產生了許多感想并做了分享。
近年來,我們還推出了一系列體驗性、探索性活動,邀請不同身份的人來到長城修繕現場,模擬修繕體驗,讓大家能夠近距離地參與到長城修繕的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