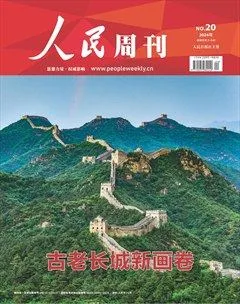畫才和畫情,才能和才華

作者簡介
陳傳席,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美術史論家、美術評論家、博士生導師、人文學者、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人民周刊》新時代美術高峰課題組、中國畫“兩創(chuàng)”課題組專家成員。
本來只想談“畫才”和“畫情”,但這個“才”有才能和才華之別,改為“材”也不行,真正的“畫材”也必有才華,而非僅有才能。一般說來,“才能”這個詞偏于能:能畫畫,能唱歌,能當官……但這個“能”升華后,便成為才華。前面說的“能畫畫,能當官”,不過是一般的能;能畫畫的人,能當官的人,歷代皆有成千上萬,乃至幾十萬、上百萬,但成為大畫家、大政治家者百無一人、萬無一人,蓋其“能”沒有升華為“華”。“華”的本義是開花,古之“華”與“花”也是一個字。《禮記·月令》有云:“始雨水,桃始華。”也有把“華”釋為果實的。劉基《悅茂堂詩·序》云:“春而萌,夏而葉,秋而華。”就是說經(jīng)過春雨的滋潤,桃開花了;經(jīng)過春萌夏葉,秋天有了果實。如是觀之,畫人的才能偏于技,習練而可得。才華偏于藝,非僅技也,讀書、思考、歷練,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人的情操、胸懷、意識、境界經(jīng)過各種知識的滋潤、鍛煉,得到進一步的升華。所謂修養(yǎng),修之養(yǎng)之,除其庸俗,進入高雅,境界則不同一般,“能”方可升為“華”。“能”是基礎,有什么樣的“能”才可升為什么樣的“華”。有畫畫才能的人不會升華為歌唱家的才華,有畫畫之才能可升為畫家的才華。
桃樹經(jīng)過雨水、泥土的滋養(yǎng)開放出桃花,不會開放出杏花,杏樹亦然。光華,有光才有華,但日華、月華不會混亂。但不會說石華,因為石頭不吸收營養(yǎng),不會升華。才華,有才才有華,但有才也有無華的,即才能不經(jīng)升華者。下面講畫才和畫情。
有一個常見的例子,鄭板橋看到竹,“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一般的俗士畫竹,也許就是一棵竹,人觀之,索然無味。但有畫情的人看到竹,也許會“疑為民間疾苦聲”,也許會想起“未出土時先有節(jié),至凌云處仍虛心”。再加上具備的各種修養(yǎng),下筆時,融匯篆、隸、楷、草諸法,學識、修養(yǎng)、思想境界、功力皆在竹中表現(xiàn)出來,畫出來的就不是一棵普通的竹,這就叫內(nèi)涵。清人況周頤云:“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畫情”即“畫意”加“詞心”。
有畫才的人畫出來的畫,若無詞心,即無高雅之情,功力最終也依靠修養(yǎng)而提升。無功力、無修養(yǎng),必無內(nèi)涵,畫不能有情有趣,其實有畫而無意也。
我20歲左右時,看到很多和我年紀不相上下的人,畫出很像樣的畫來,出版了、展覽了,大家都說:“20年后,橫行大江南北者,必此子也。”“將來中國就是他了。”“絕對超過齊白石。”有一位年長的人說了一點點反面意見:“那就看他還讀書不讀書,修養(yǎng)能不能加強……”話未完就遭到大家反駁:“你不要不承認,這個水平、這個基礎,齊白石有嗎?”但30年過去了,這一批少年得志的畫人,不但未能成為齊白石,相反,畫得非常一般,遠遠不如他20歲時的畫。這就是有畫才而無畫情。因為年輕時受過技能的訓練,畫素描人像,神形逼肖,于是畫一幅“領袖在群眾中”“工人攻克難關”,復雜的造型掌握了,毛筆勾畫,色彩點染,氣氛熱烈,確實很好。這是因為他有畫的才能,姑且稱之為畫才,其實只是畫之能者。
但他少年得志,每日畫素描、畫速寫,一周下來,畫的材料可以掛一屋。他沒有時間讀書。因為少年得志,展覽會請他,出版社請他。他忙于事業(yè),且無生計之憂,也不會遭到什么磨難,受到的是尊重而不是侮辱。他有美貌的妻子、華麗的房屋,溫柔鄉(xiāng)里只能消磨人的壯志,艱難困苦才能玉汝于成。他的修養(yǎng)不可能提得太高。久而久之,他只是能畫,有畫之技巧,而無畫情。但他的眼光還在提高,他看了齊白石、黃賓虹等大家之畫,不僅在形,更在筆墨修養(yǎng),他不滿意自己僅有的畫能,當然要提高,想在筆墨上出奇制勝,有情趣有內(nèi)涵,但這靠的是畫情而非才能,無畫情而想畫出情趣來,只能畫虎類犬,畫上不但無情無意,連早年的才華也不見了。
這就是成千上萬的畫人,早有畫之才能而晚不成的原因。天天看到各種畫集、雜志上一堆一堆繪畫垃圾,細觀之,也是很有技巧的,但“才”沒得到升華。不知有多少畫了半輩子畫的人,見到我便問:“陳老師,你看我年輕時素描就這么好,20年前就出版……現(xiàn)在怎么提高呢?”你有畫才,而無畫情,現(xiàn)在已無法提高了。
總之,西方畫以“畫才”為主,中國畫以“畫情”為主,然西人作畫也并非不要畫情,國人作畫也并非不要畫才。有能有才有情,再加上膽識,才能畫出好畫,才能成為大畫家,其中隱秘必須細細體會。
(本文為新時代美術高峰課題組、中國畫“兩創(chuàng)”課題組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