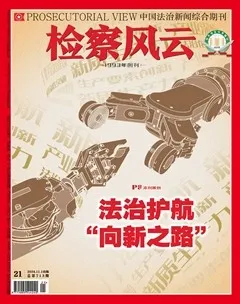我們所能談?wù)摰默F(xiàn)實(shí)


作者費(fèi)迪南德·馮·席拉赫【德】
譯者黃超謨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在德國(guó)作家費(fèi)迪南德·馮·席拉赫的作品《惡行》的開(kāi)篇,赫然寫(xiě)著這樣一句話:“我們所能談?wù)摰默F(xiàn)實(shí),從來(lái)不是現(xiàn)實(shí)本身。”這是物理學(xué)家維爾納·海森堡的名言。不知道席拉赫對(duì)海森堡的一生有著怎樣深入的了解,顯然這句話深深地觸動(dòng)了他。換句話說(shuō),如果我們能夠談?wù)摰默F(xiàn)實(shí),已經(jīng)不再是現(xiàn)實(shí)本身,那么我們眼中的“惡行”,還是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惡行”呢?當(dāng)然不是,比如《惡行》。表面上,這是一系列刑事案件的實(shí)錄,但其實(shí),席拉赫要講的是真實(shí)的人生,且是“人的失敗、罪責(zé)與偉大”。
世事大多錯(cuò)綜復(fù)雜
在成為作家之前,席拉赫是德國(guó)知名的刑事辯護(hù)律師。自1994年入行以來(lái),他曾為700多起案件出庭辯護(hù)。《惡行》記錄的僅僅是其中的38起。在席拉赫看來(lái),世事大多錯(cuò)綜復(fù)雜,僅僅憑借表面現(xiàn)象,誰(shuí)都無(wú)法準(zhǔn)確地把握它的核心。罪責(zé)也是如此。如果拋開(kāi)嫌疑人的身份背景、成長(zhǎng)經(jīng)歷,來(lái)談?wù)撘粯栋讣氖寄瑒t很難找到事實(shí)的真相。于是,在整個(g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席拉赫幾乎是本著“所見(jiàn)即所寫(xiě)”的原則,如實(shí)地將他目睹的人和事寫(xiě)了下來(lái),不帶有絲毫走樣。
盡管如此,我們?nèi)匀徊荒軐ⅰ稅盒小放c尋常的刑偵筆錄、案情分析畫(huà)上等號(hào)。在長(zhǎng)達(dá)30年的職業(yè)生涯中,席拉赫極少背離自己為人處世的原則——既不會(huì)戴著道德審判的有色眼鏡,更不會(huì)一意孤行違背委托人的意愿,以冰冷無(wú)情的目光審視手中的卷宗,為早已完結(jié)的案件添上另一道深深的傷痕。因?yàn)榉蓮膩?lái)不是道德審判。德國(guó)刑法典問(wèn)世至今已有230余年的歷史,在如此完備的法律體系下,偵查、庭審、辯護(hù)、量刑都有相應(yīng)的程序。它們仰賴的是完整的證據(jù)鏈,而不是約定俗成的道德規(guī)范。
偶發(fā)事件正如月球的暗面
具體到《惡行》,不難看出席拉赫的委托人來(lái)自不同的階層:從商界精英到退休醫(yī)生,從家庭主婦到外來(lái)移民,甚至還包括屢教不改的慣犯。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的是38個(gè)案例。它們分別被冠以不同的標(biāo)題(“費(fèi)納”“棚田的茶碗”“大提琴”“埃塞俄比亞男子”),指向38段迥異的人生:出生、成長(zhǎng)、讀書(shū)、工作、婚姻、家庭,以及隨之而來(lái)的漫長(zhǎng)余生。而在諸如此類簡(jiǎn)明扼要的生平概述之后,隱隱藏著某些與日常生活相互悖逆的因素。它們就像月球的暗面,始終潛伏在不為人知的罅隙中,等待在某個(gè)偶然的時(shí)機(jī),以出人意料的姿態(tài)跳出來(lái),左右當(dāng)事人的思想行為,成為惡行的直接誘因。
比如《費(fèi)納》。嫌疑人弗里德海姆·費(fèi)納是一位令人敬仰的醫(yī)生。他的人生本該一帆風(fēng)順,偏偏結(jié)局出人意料。24歲那年,他結(jié)識(shí)了妻子英格麗德。她比他大三歲,性格強(qiáng)勢(shì),陰晴不定。她要求他許下諾言,照顧她一生,永不分離。而在此后的四十八年里,哪怕英格麗德不斷對(duì)他施以冷暴力,費(fèi)納仍然信守承諾,不離不棄。直到72歲那年,忍無(wú)可忍的他才將手中的刀對(duì)準(zhǔn)了妻子。那么,我們應(yīng)該怎樣來(lái)判定他的行為?庭審時(shí),檢察官曾經(jīng)再三質(zhì)疑——費(fèi)納不是別無(wú)選擇,他本來(lái)是可以離婚的。
在長(zhǎng)長(zhǎng)的隧道里絕望地奔跑
但事實(shí)上,離婚才是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今天的我們常常早已忘卻了曾經(jīng)許下的諾言,可費(fèi)納卻是認(rèn)真的。他認(rèn)真地信守了自己的承諾,哪怕這個(gè)承諾“捆綁了他一輩子,甚至讓他成了一名囚犯”。這里,我們看到了席拉赫的悲憫。他很清楚,與其將委托人的行為不加區(qū)分地定義為“罪行”,倒不如稱之為“惡行”。畢竟,這個(gè)世界既沒(méi)有純粹的善,也沒(méi)有純粹的惡。每個(gè)人在各自的成長(zhǎng)過(guò)程中,總是會(huì)在善與惡的夾縫中左右搖擺。而罪犯之所以會(huì)犯下重罪,倒不是因?yàn)樗麄兲煨杂卸嘈皭海撬麄兩硖幍沫h(huán)境,并不提供任何希望。
就像席拉赫所說(shuō),他們“在一條長(zhǎng)長(zhǎng)的隧道里奔跑,看不到別的出路”。《刺猬》即是如此。擁有高智商的卡里姆·阿布·法塔里斯來(lái)自黎巴嫩。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有八個(gè)哥哥。他的叔叔、哥哥都有犯罪前科,都被當(dāng)?shù)貦z察院列為慣犯。而這一次,相似的命運(yùn)終于落到了卡里姆身上。哥哥瓦利德因?yàn)閾尳俦徊丁榱藥退颖芊芍撇茫ɡ锬烦鐾プ髯C,當(dāng)眾出具偽造的不在場(chǎng)證據(jù)。很難說(shuō),瓦利德是不是真正逃脫了法律制裁,但可以肯定的是,卡里姆已經(jīng)和他的叔叔、兄弟一樣,走上了犯罪的不歸路……
拯救每一個(gè)無(wú)辜涉案的人
毋庸置疑,這就是刑罰。在懲處不法行為的同時(shí),法律更會(huì)保護(hù)每一個(gè)無(wú)辜涉案的人。《夏令時(shí)》里,中年男人珀西·博海姆與女大學(xué)生斯蒂芬妮在酒店幽會(huì)。女孩于當(dāng)天15點(diǎn)26分(夏令時(shí))被發(fā)現(xiàn)獨(dú)自死在套間里。調(diào)查中,博海姆稱其早在案發(fā)前一小時(shí)(14點(diǎn)26分,夏令時(shí)),就已經(jīng)離開(kāi)了酒店。但警方從酒店停車(chē)場(chǎng)出口的監(jiān)控視頻中發(fā)現(xiàn),他離開(kāi)的時(shí)間正是15點(diǎn)26分,恰好與女孩的遇害時(shí)間相互吻合。好在,席拉赫沒(méi)有放棄。在經(jīng)過(guò)反復(fù)查證、細(xì)致比對(duì)之后,他終于找到了案件的關(guān)鍵突破口——還是在那段視頻中,超高清攝像頭清晰地記錄下博海姆手表上的時(shí)間為14點(diǎn)26分(夏令時(shí))。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攝像頭的時(shí)間設(shè)置。原來(lái),從安裝的那天起,其設(shè)置便從未調(diào)整過(guò)。案發(fā)時(shí),整個(gè)德國(guó)都在使用夏令時(shí),唯獨(dú)這個(gè)攝像頭還停留在寒冷的冬天(冬令時(shí))。由此,博海姆的冤情終于大白于天下。
說(shuō)到底,這就是刑事辯護(hù)的意義所在。它要求律師必須在前期投入大量時(shí)間、精力,細(xì)致地研究卷宗,在起訴的證據(jù)鏈中找出漏洞,“糾正那些倉(cāng)促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結(jié)論”。畢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更不是兒戲,無(wú)論如何都需要審慎處理、嚴(yán)肅對(duì)待。就像席拉赫所說(shuō):“我們的人生就像在一層薄冰上跳舞,冰下極冷,一旦掉落會(huì)立即喪命。冰層承載不住一些人,他們掉了下去。我最關(guān)心的就是這一時(shí)刻。如果足夠幸運(yùn),這樣的事就不會(huì)發(fā)生,我們可以繼續(xù)跳舞。如果我們足夠幸運(yùn)。”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
新書(shū)速遞

海劍、藍(lán)蓮 著
中國(guó)書(shū)籍出版社
《刑事檢察官之真相》是“刑事檢察官”系列作品的精品之作。作家海劍、藍(lán)蓮?fù)黄谱晕遥泵娆F(xiàn)實(shí),通過(guò)生動(dòng)的情節(jié)構(gòu)思與矛盾沖突設(shè)置,塑造出一個(gè)個(gè)清正廉潔、一心為民的新時(shí)代人民檢察官形象,同時(shí)也將形形色色的反派人物刻畫(huà)得入木三分。
——張平(中國(guó)作協(xié)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