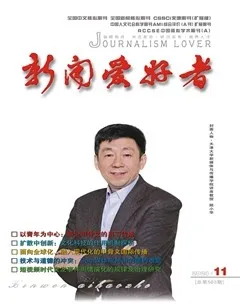技術與道德的沖突:Sora媒體應用中的履約難題
【摘要】現代社會的契約關系預示著Sora與新聞業的必然聯結,其功利取向則帶來Sora媒體應用的技術—道德沖突,造成智能化媒體實踐主客體關系的緊張性。Sora媒體應用道德共識的履約難題,在于智能化媒體實踐的自主性、執業共同體的透明性以及實踐主體的契約精神受到沖擊。強化智能化媒體實踐主體間的契約意識,應將Sora程序作為實踐主體協作者而非工具,克服技術—道德的履約難題。
【關鍵詞】Sora程序;媒體應用;契約精神;履約難題;道德共識
2024年2月,OpenAI推出的視頻生成模型Sora帶來電視內容生產的革命,實現了視頻內容生成的自動化。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在加速媒體實踐智能化轉型的同時,也帶來了真實性濫用、版權邊界模糊等倫理問題。[1]Sora媒體應用是否重蹈技術—道德的沖突,有待新的智能化媒體實踐驗證。
Sora媒體應用有諸多可預見的困難,現代社會的工具化解釋已預示這一趨向的必然性。不同于傳統社會群體間所遵守的休戚與共原則,現代社會“多半只是各群體內在的分解過程之后的殘余和遺跡”[2],僅僅是個體實現人際交往的手段而非目的。在社會解釋的工具主義圖像統攝下,自然人成為確認現代道德的立足點。現代條件下的個體必須通過與他人建立合作關系,以獲得自我實現的可能[3],這為個體間契約關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4]由個體組成的行業群體亦是如此。
生成式人工智能與媒體實踐的聯結遵循契約的邏輯,這種契約的實質是智能化媒體實踐的道德共識。這樣的智能化媒體實踐從可能變成現實,需要通過技術應用的道德考察。道德共識作為技術公司與媒體機構合作的前提,雙方的長久互惠是基礎,但如果雙方出于功利化取向而合作,技術—道德的沖突將導致契約關系中道德共識的名存實亡。
本文考察的問題是:一是Sora可實現媒體應用的技術特征是什么?這是雙方建立契約關系的現實基礎。二是Sora媒體應用何以具有道德共識?這是雙方建立契約關系的道德基礎。三是Sora的技術特征可否瓦解道德共識,如何保證契約關系的有效性?
一、Sora媒體應用的技術特征
作為世界模擬器的視頻生成模型,Sora能夠根據指令生成連貫、真實、穩定的60秒視頻。視覺技術的發展和視覺化的審美轉向使得日常生活趨于圖像化和景觀化[5],視覺時代的到來已成必然。在視覺文化時代,無論是傳統電視機構的新聞節目還是新媒體平臺的短視頻內容,視頻成為消弭“使用溝”不可或缺的存在,這樣的內容制作需要經過由人主導的生產流程。Sora顛覆了傳統的視頻生產模式,使自動化視頻生產成為現實。討論Sora媒體實踐的契約關系,需要先了解這種技術的特征。
(一)經驗性:對歷史之維的深度學習
與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的技術邏輯相同,Sora同樣建立在大量數據訓練之上,對于物理世界的理解與呈現來自于規模效應。[6]Sora通過深度學習完成“量”的積累,最終實現“質”的創造。攜帶了既往經驗的大量數據被用于模型訓練與優化,使Sora生成的“真實世界王國”脫離不了由海量數據建造的“地基”與主體“骨架”。
依靠大量數據訓練而建立的Sora模型,具有在現實基礎上自主生成的能力,這樣的內容生成不同于傳統電視生產流程,但兩者的共通性在于從素材到新聞的形態轉變而非從無到有,這決定了兩者既可獨立生產也可協作分工。電視從業者(以下簡稱記者)可憑借先驗想象力創造先驗圖式,完成對新聞素材的高度綜合。雖然Sora并不擁有先驗圖式,卻可依靠海量的經驗數據形成新聞框架綜合數據。即便Sora無法徹底取代記者的先驗圖式,但其可以作為先驗圖式的輔助性工具。記者可使用Sora完成特定選題的視頻化生成,并將其視作“腳本”用于視頻內容制作的參考。經驗性成為賦予Sora媒體應用可能性的基礎特征。
(二)還原性:對現實之維的自主涌現
Sora深度學習目的在于生成與現實世界別無二致的影像景觀。Sora所使用的擴展視頻生成模型,是一條向著構建通用物理世界模擬器邁進的路徑。依靠Transformer架構與Difussion模型,Sora可摹擬出三維的“真實世界”。基于提示詞與現有數據,Sora可在自然規律的尺度內預測事物發展變化的邏輯。在不違背物理規律與常識的前提下,Sora可生成長時間、多空間的視頻,標志著這款程序初具理解物理世界、構造物理世界模型的能力,實現對于物理世界的自主化“智能涌現”。[7]
不同于現有數據與提示指令的生成,“涌現”表明Sora突破了傳統生成式AI的線性生產邏輯,堪稱“開啟了AI發展的牛頓時代”。[8]在智能化媒體實踐中,Sora的高逼真度與高靈活度,為視頻制作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尤其對于帶有娛樂、科普、教育等性質的軟事實新聞而言,無疑是量身定制。Sora通過自動生成與用戶喜好相匹配的視頻內容,提升內容生成效率與質量,促進媒體機構邊際效益的最大化。[9]
(三)機械性:對物理世界的僵硬理解
從技術細節看,Sora無法準確表示因果關系,局部合理與整體荒謬的沖突,造成其臨界狀態的缺失。Sora使用的Transformer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操縱自然語言,卻無法精準表達物理定律,反映出其作為基于概率世界模型的局限性。[10]這種局限性的實質是Sora的機械性,所生成的物理世界無法與真實世界相比。盡管它可以呈現多時空場景及其細節,卻不能成為真正的“世界模擬器”。物質世界的絕對運動與相對靜止的辯證統一,決定了Sora仍是一個無法實現因果關聯的概率模型,它更適合被稱為“視頻世界模擬器”。
基于大腦的神經網絡與相互連接的神經元,人類的思維得以連貫,將“思維序列轉化為語言序列”,記錄個體思想,實現相互交流。[11]媒體實踐強調“語言序列”的嚴謹性,防止信息的誤讀。Sora媒體應用的智能化實踐以視頻為基本語言,依靠技術模型測算概率,導致其生成的視頻最終卻落入機械因果律的窠臼。如果將視頻分幀處理,不難發現Sora生成的流暢畫面漏洞百出,而智能化媒體實踐的道德共識并不允許這種結果出現。
二、Sora媒體應用道德共識的可能性
社會協作建立在共識基礎上,Sora以及新聞從業者聯合而成的應用主體在某些文化認同上具有一致性,基于此形成了部分共識,且由于主體中的個體倫理境遇與道德氣質的不同,又展現出多樣性。[12]Sora媒體應用的道德共識是在專業實踐中逐漸形成的,應用主體道德價值的多樣性既服膺于道德共識,也為道德共識的建立提供保障。
(一)Sora媒體應用的新倫理自然狀態
2024年2月26日,Sora問世后第8天,CCTV發布了文生視頻AI系列動畫《千秋詩頌》,標志著中國主流電視媒體強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電視實踐中的應用。[13]Sora媒體應用需要相應的倫理秩序,這樣的秩序由系列的倫理原則來支撐。但在倫理原則成為新的道德共識前,Sora媒體應用必然經歷一個倫理原則缺失的“倫理的自然狀態”。康德將自然狀態分為“倫理的”與“律法的”,提出人類社會要“聯合成為一個倫理的共同體”。[14]在此之前,智能化媒體實踐,同樣要經歷一個沒有倫理規范的自然狀態。
媒體實踐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通用技術規定著內容生產與傳播的流程。在智能化媒體實踐中,人機關系的不協調造成了無序的倫理自然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新興媒體的實踐應用處于探索階段,傳統的新聞倫理原則無法直接適應新的媒體實踐,無序的實踐秩序造成了媒體與受眾契約關系的緊張性。走出這樣的倫理自然狀態,需要借助專門化的倫理原則規范新媒體介質的實踐活動。Sora媒體應用同樣要經歷這樣的階段,使智能化媒體實踐由不成熟逐漸向成熟過渡,這是Sora媒體應用的道德共識。
(二)道德共識的雙重保障:技術向善與媒體責任
道德共識體現的是共同的個體利益與相近的價值取向,但現代社會的異質性導致的“道德分化”沖擊著道德共識的穩定性。“社群主義”理論主張通過強調個體“人格自足”的虛假性與整體社群的真實性,證明“社群”對于“自我”的重要性,個體為保證社群結構的穩定性必須追求共同美德,此即道德共識。[15]善與責任作為美德倫理的重要概念,是現代社群凝聚道德共識的重要保障。新聞業可被視為分工一致的專業性社群,Sora媒體應用需要將善與責任作為達成道德共識的保障,避免因其盲目應用破壞社群內部的關系和諧。
技術向善為Sora媒體應用的道德共識提供了可能。技術并非擁有理性的有機體,技術向惡還是向善取決于使用者的目的。不同使用者持有不同的技術善惡觀或中立觀,表明技術顯然無法自行達到這樣的要求。技術使用者卻可以使之具備合目的性,即“一個概念在其客體方面的因果性”。[16]OpenAI的宗旨是“創建造福全人類的安全通用人工智能(AGI)”,這也是Sora的合目的性所在。Sora程序的開發同樣基于利他原則,其應用于媒體的道德共識正在于此。媒體實踐的利他性源于媒體機構及其從業者的理性,理性促進了智能化媒體實踐至善的目的。技術向善與媒體實踐動機的道德性耦合,理念的一致性奠定了Sora媒體應用的道德共識。
媒體責任理論為Sora媒體應用的道德共識指明了方向。責任意味著智能化媒體實踐必須遵循行業規范,既包括內部道德規范也包括外在強制規范。媒體道德責任的類型多樣,其中包括指定式責任、自愿式責任與契約式責任。[17]根據這三種媒體責任,可窺見Sora媒體應用道德共識的可能性。
指定式責任強調責任的外在強制性,Sora媒體應用盡管處于倫理的自然狀態,但仍有部分現有的法律、條例可用來規制智能化媒體實踐。在Sora媒體應用中,盡管這些法律條例缺乏針對性,但它們對版權侵權、隱私侵犯等行為的禁止,仍然適用于文生視頻的智能化媒體實踐。由此,Sora媒體應用的道德共識因指定式責任具備了外部保障。
自愿式責任強調自律,這種責任的內涵與媒體責任理論直接相關,因為自由應以對受眾負有責任為前提。Sora媒體應用中實踐主體的自由,必須根據智能化技術特點制定行動準則,通過遵守準則實現媒體實踐主體的自律。通過實踐主體的自律,媒體使用Sora制作視頻便有了指導行動的準則,這是Sora媒體應用道德共識的根基。
契約式責任強調責任制定時不同責任主體間的責任共識,實踐主體需要履行對社會和公眾的承諾。[18]Sora媒體應用不能因技術的便捷性而忽視責任的履行,否則與責任相對應的權力歸屬也將發生流轉。福柯認為權力是一種關系,可以將權力關系看作是處于流動的循環過程。[19]一旦媒體機構利用Sora生成爆款產品而置對受眾的承諾于不顧,媒體的話語權力便會轉移,媒體機構便因此喪失了公共屬性。出于這種考慮,媒體機構需履行與受眾的道德契約,這是Sora媒體應用形成道德共識的前提。
技術向善與媒體責任成為Sora媒體應用道德共識的雙重保障。在擬履約過程中,Sora的技術架構并非專為智能化媒體實踐搭建,倫理觀念的沖突造成Sora媒體應用的履約難題。Sora媒體應用的具體履約事項應首先包括協助新聞從業者完成生產全流程。除實踐層面外,履約事項的重點應在于遵守新聞業的道德共識。因此,履約難題首先表現為Sora媒體應用對傳統新聞生產流程的解構,進而造成對傳統新聞行業共識的沖擊。
三、Sora媒體應用對傳統新聞行業共識的沖擊
Sora媒體應用將重構電視生態與視頻生產流程,在這個過程中,媒體實踐的行業共識面臨新的挑戰。實踐主體在認識到視頻生產規律的基礎上,道德共識出于對自然法則的尊重而形成。在傳統的電視新聞生產中,行業實踐的自主性、執業共同體的透明性以及從業者的契約精神都是典型的道德共識。Sora的媒體應用,與這些共識可能存在內在的沖突。
(一)Sora與新聞業道德共識的沖突:自主性的解構
現代社會,自然人成為確認現代道德的基本立足點,人的自主性成為塑造自身與群體的重要能力。新聞業要提供真實客觀的“摹本的世界”(新聞資訊),必須保持人類記者實踐的自主性地位,這是新聞業賴以生存的重要根基。
Sora媒體應用對媒體實踐的自主性共識造成嚴重沖擊,首先表現為Sora媒體應用對實踐主體的專業知識學習和專業實踐技能提升構成威脅。Sora生成視頻的便捷性,使負責操作的記者編輯只需下達指令,他們積累的經驗性知識被懸置起來,Sora程序的自動學習和實踐主體無法直接積累經驗知識構成沖突。
Sora媒體應用對媒體實踐自主性的沖擊還表現在對實踐主體自主思考能力的沖擊。媒體實踐是一項創造性活動,智能化媒體實踐的創造性導致實踐主體由人轉向智能程序,降低了記者自主思考的機會。Sora的經驗性反映的是海量的數據概括出來的共性經驗,實踐主體利用文本指令或靜態圖像提示Sora生成視頻內容,程序本身無法代替人的思維,致使這類產品缺乏個性化創造的成分。即使記者編輯在文生視頻作品的基礎上完善,依然無法體現其自主思考和實質性貢獻,因為,這樣的完善只是對Sora內容框架的延續。
Sora媒體應用對媒體實踐的根本沖擊在于它消解了記者編輯執業行動的自主性。傳統的媒體實踐從選題策劃到現場拍攝采訪、再到節目的剪輯制作合成,全部體現執業共同體成員的集體智慧。如果記者編輯放棄自主學習與思考,將無法達到預期的實踐效果。在傳統的電視內容生產中,一般的經驗性知識難以為突發新聞現場的記者提供指導,這有賴于他們的自主行動。智能化媒體實踐正在取代記者編輯的自主行動,這違背了媒體實踐的目的。
(二)Sora與媒體實踐共同體道德共識的沖突:透明性的弱化
隨著AI技術對新聞倫理的驅動,透明性正在成為新的倫理標準。[20]這一概念是智能化媒體實踐的結果,倫理共同體應該將其奉為圭臬。媒體實踐中的透明性概念指的是新聞采集、組織、傳播的對外公開。[21]這三道環節分別對應行動者透明性、過程透明性與回應透明性。行動者透明性包括公開媒體所有者信息、媒體使命宣言與倫理準則等。Sora對媒體實踐共同體透明性的弱化首先體現在新聞生產前行動者透明性的弱化。媒體生產流程公開的前提是共同體對受眾的信任,公開也是共同體獲得受眾信任的先決條件,Sora媒體應用可能使媒體實踐的使命、倫理準則的公開落空。因為它們體現著日常生產慣例與從業者的實踐邏輯,而Sora改寫了這樣的慣例與邏輯。當受眾意識到共同體公開的使命宣言、倫理準則與智能化媒體實踐并不相符,透明性反而解構著共同體。
Sora對媒體實踐共同體透明性的弱化,體現在新聞生產過程中透明性的弱化。過程透明性要求共同體保證生產流程公開化,公開意味著接受監督,客觀性與真實性則成為透明性原則在內容生產環節需要觀照到的特質。Sora生成的視頻是對現實情境的模擬,技術的經驗性導致其無法在自然邏輯內創造全新內容,從這類內容中只能窺見歷史之維的腳印,無法與記者記錄的現實之維相比,所生成的內容反而成了鮑德里亞所說的“超真實”形態,只是這樣的“真實”并不符合自然本身。此外,Sora技術的機械性造成生成的內容不符合人對自然界的客觀認知。“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的辯證法思想恰好說明Sora無法還原事件本身,時間的線性化決定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情況重復發生,利用Sora還原事實反而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契約。“程序客觀”無法達成,“結果客觀”更無從談起,透明性原則在Sora的技術邏輯主導下失去了意義。
Sora對媒體實踐共同體透明性的沖擊,體現在媒體回應性的弱化。提供回應渠道意味著共同體注重互動與反饋,受眾回應可作為后續媒體生產實踐的“養料”,為共同體查漏補缺。在Sora媒體應用的倫理自然狀態,視頻內容的生成缺乏對應的倫理規范,在體驗上并不符合受眾的視覺慣習,受眾同樣需要經歷“觀看的”自然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文生視頻勢必造成與受眾的視覺沖突,技術機械性所產生的邏輯漏洞,也使受眾質疑Sora媒體應用的可行性。在線評論便是受眾質疑的主要渠道,執業共同體出于維護所在機構公信力的考慮,可能精選留言乃至關閉評論區。如此,反饋的透明性并非雙方意見與信息的公開,這并非真正的透明。
(三)Sora與媒體實踐主體道德共識的沖突:記者契約精神的消解
在智能化實踐中,媒體實踐主體通過遵守準則,不斷完善自我。遵守準則也是契約精神的體現,塑造的是記者的職業聲譽。準則作為個人執業的主觀原則,是個人行為在主觀上所遵循的程序和規則。[22]Sora媒體應用破壞著這樣的主觀原則,同時也在消解實踐主體的契約精神。
Sora媒體應用對實踐主體契約精神的消解首先表現為記者編輯無法正常履行執業義務,包括不得造假、敲詐勒索等法律義務,與關愛受眾的視頻資訊消費幸福等道德義務。Sora的還原性使其成為一種效率工具,在功績社會視角下無疑是實現自我規訓與自我超越的一條捷徑[23],但也容易導致使用者的怠惰心理。同樣,在應用Sora時,實踐主體易滋生坐享其成的心理,不再遵循“慢工出細活”的行動準則。Sora媒體應用的“溫柔陷阱”使記者編輯喪失執業主動性,對Sora的輕信導致視頻內容出現漏洞,這便違背了法律義務。現階段的Sora難以保證畫面的流暢性,若未經專業審核公開傳播,實踐主體要承擔未能尊重受眾資訊消費幸福的道德義務所帶來的代價。
Sora媒體應用對實踐主體契約精神的消解還表現為記者編輯履行承諾的身體缺席。在日常媒體實踐中,媒體機構為吸引受眾或塑造媒體形象,在資訊傳播中向受眾做出道德允諾,這同樣是記者編輯應該遵守的準則。這樣的承諾是實踐主體為彰顯自身道德性的表征,滿足的是自我實現的高級欲求,兌現允諾有賴于實踐主體的自主性,且應通過其執業行動來兌現,否則承諾便只具備工具價值。Sora媒體應用幾乎包攬了媒體實踐的事項,擠兌了實踐主體兌現承諾的機會。“在場的缺席”使記者編輯的主體性地位降低,媒體承諾轉由機器間接負責兌現。
Sora媒體應用對媒體實踐主體契約精神的消解也表現在對從業者職業形象的沖擊。記者曾被冠以“無冕之王”的稱號,高度的社會評價要求其以誠實、正義等正面形象示人,這是這個職業群體贏取受眾信任的自我展現,是其契約精神的表現之一。智能化媒體實踐削弱了記者編輯的主體性地位,智能生成內容的瑕疵將消解他們的職業形象,Sora一定程度上成為阻隔媒體實踐主體與受眾主體間性的無形界墻。傳統電視內容生產中,優質內容增進了受眾與記者編輯的心靈交流;Sora生成的視頻增加了受眾的視覺體驗,提高了生產效率,但缺少本雅明所說的“靈韻”。[24]受眾與記者的心理距離被拉大,智能化媒體內容淪為“機械復制”之物。媒體機構允諾的良好形象被破壞,契約精神終被消解。
四、結語:AGI浪潮下Sora與媒體執業主體的倫理面向
在通用人工智能所展現出的前所未有的生產力之下,AI與使用者的關系已由平等代替從屬,并以更為深刻的方式塑造著社會意義與價值觀,新的社會規則、關系與文化在AI技術架構中不斷生成與流變。[25]
在Sora媒體應用中,其與媒體道德共識的適配程度,檢驗著智能化媒體實踐中人與技術、人與自然、技術公司與媒體機構建立契約關系的可能性,從功利角度模擬考察Sora媒體應用的履約難題不可避免。但將Sora模擬實踐環境升維至技術與人平等化情境中,上述的考量似乎有些狹隘。AGI浪潮之下,“人是技術的主人”的觀念不斷被消解,技術不再外化于人,人開始成為一種技術存在。[26]我們不妨將Sora看作媒體實踐中的虛擬協作者,在懸置資本、文化等多重現實因素后,純粹考察其與媒體實踐主體的倫理面向,這同樣是對Sora與媒體共識沖突的道德化補遺。
Sora作為虛擬協作者應該與媒體實踐主體擁有相一致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只是對于出自我們的行動與義務法則相一致或者相沖突這種意識的愉快或者不快的易感性”。[27]Sora媒體應用的道德共識可以使實踐主體獲得“意識愉快的易感性”,為實踐主體克服履約中的困難提供動力源泉。如果Sora媒體實踐主體以相似的道德情感作為達成共識的動機,實現“在彼此坦承其隱秘判斷和感受時的完全信賴”[28],Sora媒體實踐主體將難以在同一道德框架下滑落至道德相對主義的窠臼,進而導致道德共識的瓦解。
隨著社會秩序的不斷文明化,契約倫理展現了近現代人類對自身價值的重視,獲得最大幸福成為個體賴以生存的動力,所有的價值與意義皆以個體為原點,即便個體是為了獲得長遠幸福而秉持契約精神,多重利益的博弈使得沖突仍不可避免,Sora媒體應用中的道德共識沖突便是例證。樂觀來看,現代性中崛起的個體擁有更強的尊嚴感與理性,Sora與新聞業因擁有高關注度與影響力,媒體機構需以更為嚴格的標準規范智能化媒體實踐秩序,克服技術—道德難題。
參考文獻:
[1]鄭滿寧.人工智能技術下的新聞業:嬗變、轉向與應對——基于ChatGPT帶來的新思考[J].中國編輯,2023(4):35-40.
[2]舍勒.價值的顛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153.
[3]周輔成.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210.
[4]張鳳陽.契約倫理與誠信缺失[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2(6):33-39.
[5]劉海明,何曉琴.觀看的向度:短視頻景觀下個體視覺消費行為的倫理審視[J].新聞愛好者,2022(7):11-14.
[6]郭全中,張金熠.作為視頻世界模擬器的Sora:通向AGI的重要里程碑[J].新聞愛好者,2024(3):1-18.
[7]喻國明.Sora作為場景媒介:AI演進的強大升維與傳播革命[J].青年記者,2024(3):1-5.
[8]尹燁.如今,Sora已經開始嘗試建構真實世界了……[EB/OL].https://www.yicai.com/news/101995430.html.
[9]史安斌,鄭恩.邁入“融合性真實”:文生視頻技術對新聞傳媒業態的重塑[J].傳媒觀察,2024(4):27-36.
[10]顧險峰.Sora物理悖謬的幾何解釋[EB/OL].https://mp.weixin.qq.com/s/HSZMbiFuNvTmBv26csZFGg.
[11]霍布斯.利維坦[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19.
[12]樊浩.當前我國諸社會群體倫理道德的價值共識與文化沖突:中國倫理和諧狀況報告[J].哲學研究,2010(1):3-12+128.
[13]中廣互聯.總臺:積極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媒體領域的創新應用[EB/OL].https://www.tvoao.com/a/217541.aspx.
[14]康德.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55.
[15]賀來.“道德共識”與現代社會的命運[J].哲學研究,2001(5):24-30.
[16]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判斷力批判[M].張榮,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27.
[17]趙鴻燕.關系的網絡:微觀權力視角下媒體責任探析[J].國際新聞界,2011,33(12):55-59.
[18]趙鴻燕.關系的網絡:微觀權力視角下媒體責任探析[J].國際新聞界,2011,33(12):55-59.
[19]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27-28.
[20]張超.“后臺”前置:新聞透明性的興起、爭議及其“適度”標準[J].國際新聞界,2020,42(8):88-109.
[21]Deuze.M.The web and its journalism:consid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 ttype of News media onine[J],Newmedia&society,2003(6):203-230.
[22]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道德形而上學[M].張榮,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33.
[23]韓炳哲.倦怠社會[M].王一力,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74.
[24]王才勇.靈韻,人群與現代性批判:本雅明的現代性經驗[J].社會科學,2012(8):127-133.
[25]常江,羅雅琴.人工智能如何“生成”信息失序:原理、危機與反思[J].信息技術與管理應用,2023,2(3):65-75.
[26]張萌.從規訓到控制:算法社會的技術幽靈與底層戰術[J].國際新聞界,2022,44(1):156-173.
[27]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道德形而上學[M].張榮,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411.
[28]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道德形而上學[M].張榮,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483.
作者簡介:劉海明,重慶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重慶 401331);程博,重慶大學新聞學院2023級碩士生(重慶 401331)。
編校:趙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