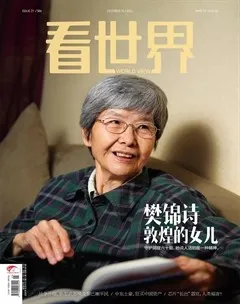純愛退場,“渣男渣女”集合

國產愛情劇正在拋棄愛情。或者說,正在剖解“愛情”這個詞。
近期開播、宣稱“向所有純愛戰士致歉”的都市愛情劇《半熟男女》里,沒有任何一個角色在感情里絕對忠誠。熙熙攘攘的城市迷宮里,他們互相躲藏、試探和拉扯,各懷鬼胎。看似自由的男歡女愛,背后都藏著各取所需的心機,或是一念之間的背叛,幾乎“全員惡人”。
以劇中男性角色瞿一芃為例,他與幾個月前另一部國產劇《玫瑰的故事》里的方協文一起,成為了年度“渣男”代表。二者人設也類似:自卑且自負,敏感多疑,在感情里極端且不真誠。
這部劇將一個終極論點拋在了臺面上:如果削弱道德占比,僅隨心所欲地去愛,愛情的模樣還可能是美好的嗎?道德是維系一段感情的必要因素,還是阻礙?
“渣男”“渣女”的煉成
作家金宇澄曾在接受《十三邀》訪談時,對“渣男”這種詞匯表達了不解和批評:“人本身是非常復雜的東西。這么復雜的人性變化,用這么低能的一句話去涵蓋它,真的是太幼稚,太可憐了。”
節目播出后,金宇澄毫無意外地招致了討伐。甚至有一種批評聲是:沒準金宇澄自己就是或曾是“渣男”,才會為這種“道德敗壞”的身份“洗白”。


其實只需關注語句的表面意思本身即可。這位年過七旬的作家之所以認為此類概括讓人顯得“可憐”,是因為在本可以具有充分緩沖地帶的道德情感境遇里,一個人主動選擇了單一的受害者立場。
若概括《半熟男女》里幾位主角的行為,幾乎人人都是“渣男”“渣女”:腳踏兩只船、互相出軌、移情別戀、為攀富貴玩弄感情者……從道德角度論,人人都是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
而“渣男”“渣女”“海王”“海后”這樣的詞匯,自其發明初期到大面積傳播,其承載的功能更多是便于概括和情緒發泄。在親密關系里,當人們感覺自己受到了傷害,自我保護和反擊是一種本能,其中就包括情緒發泄與道德審判。
看不見的臺面之下,人人都在提防遇到“渣男渣女”,但我們自身是否也可能在某個瞬間變得“渣”?我們是否也會“本能”地用人性的復雜性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劇中,“腳踏兩只船”的何知南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行為不妥。她內心的另一個人格在試圖喚醒她:“被兩個人喜歡沒有錯,但你享受就渣了。”但世俗里的何知南也會對自己承認:“被兩個人爭奪,讓我感覺被在乎了。”
人很容易用“渴望被愛”來解釋自己背德的行為,這似乎是用一種心理或情感的脆弱來做掩飾。劇中千方百計想要攀上富家女的小鎮青年瞿一芃,從他的視角,自己出軌、撒謊,都是因為自己在這個名利場社會里不被尊重。他渴望被人“看得起”,渴望被愛—難道,也是一種錯嗎?
一些行為的初衷也許并不是傷害他人,但又的的確確給他人帶去了傷害,在這種兩難情境下,人真的可以毫不猶豫地作出利于他人的選擇嗎?如果對我們自己的心誠實,是否必然會在感情里滑向道德低谷?
也許需要承認的是,當人們遇到愛—無論那是假象還是真實,被激發出來的也許不是勇氣和力量之類的東西,反而是內心深處的脆弱面和攻擊性,還有貪婪、欲望和趨利避害的本能。
例如“普通女孩”何知南渴望被愛,渴望在多多益善的愛里享受獨特性;已婚男人周斌渴望年輕女孩的肉體,渴望掌控弱者的權力感,為此謊言遍天飛;職業女性韓蘇也渴望一段忠誠和穩定的感情,可當發現自己被背叛后,她也會產生報復的欲望。
人們因獨特性而具有吸引力,也因獨特性互相傷害。正如法國浪漫主義作家繆塞說:“男人會欺騙、背叛、泄密、偽善和傲慢無禮;女人都很做作虛偽、不誠實……但是這不完美的兩者結合起來卻是人世間一件神圣而莊嚴的事。”
愛情,它是一個神話。我們可以去演繹,可以去欣賞,但別想著活在神的世界里。
愛情神話
《半熟男女》不是近幾年第一部戳破愛情神話的國產影視劇。
去年,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的電視劇《裝腔啟示錄》(豆瓣8.2分),同樣將敘事焦點對準都市里互相拉扯、試探的男男女女。他們沒有純愛的幻想,但他們會誠實面對自己的私心和欲望。同時,他們對愛情沒有不切實際的期待,能在混沌現實里互相提供支撐和某種力量,就已足夠讓兩個人走到一起。
誘惑、欲望、寂寞等讓“背德”趁虛而入的情緒,在或許原本就不夠堅定的心理堡壘里橫沖直撞,最終指向供我們所有人躲躲藏藏的道德曖昧性。
如果對我們自己的心誠實,是否必然會在感情里滑向道德低谷?
這種“道德曖昧”,與浪漫主義文學史上的道德邊緣化完全站在對立面。前者是由于現實掣肘和世俗心思過多,后者,如《泰坦尼克號》或《廊橋遺夢》里那種超脫世俗的浪漫邂逅,反而是摒除世俗限制、聽從內心激情的感召。
不過,多年后,人們才恍然大悟,《泰坦尼克號》里男女主角的愛情,其實也是背德的婚外情。由是,又一輪逆時代的道德價值批評涌入。
一個有些“反現代性”的事實是—在今天,道德在愛情里的地位似乎更高了。
于是,對人性的其中一個面向做出道德評判變成一件容易的事。網絡平臺上,鋪天蓋地的“勸分”大軍。節日不送禮、回復信息不及時,就足以被審判“該分手”,仿佛親密關系里的人只是商品,可以隨時退換。
但似乎的確,越來越多人默認,只有樂而毫無“喜怒哀”的親密關系才值得自己走進。結婚率整體下降的社會背景為這種道德潔癖做出了呼應:如果不是足夠純粹的、毫無瑕疵的愛情,寧肯不要。
然而,忠誠的命題之下,同樣埋藏著令人失望的可能。近幾年知名度較大的國外家庭題材電影《婚姻故事》和《意外墜樓的審判》,都呈現了“承諾”之下更長遠的隱患。有情人終成眷屬之后,還可能面對更棘手、更難以脫身的人生命題。
愛情只需要發生,它屬于兩個人相望的一瞬間。長期的感情、婚姻,則需要經營,需要用心和用腦,也需要物質支撐。
從這個角度看,愛情并不是難事。兩難的是人們對它的定義和期待。這并不是要求我們放低自己的道德標準,恰恰相反,我們的道德準則,不應該被愛情“污染”。
在古希臘哲學家們對愛情的思考與解說中,愛天然包含欲望、嫉妒等“人性陰暗面”,現代社會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更外因性的虛榮、勢利等因素,于是誕生了“鳳凰男”“撈女”等詞匯。


信息時代,在種種“不美”的愛情故事的沖擊下,人們一面歌頌絕對純凈的愛情,因為它越來越顯得稀缺;一面對摻雜半點瑕疵的感情難以容忍,要求關系里的絕對公平與透明。
當人們對愛情不切實際的信仰和期望一點點破滅,緊隨而至的是對愛情的唾棄與嗤之以鼻。如今,輕視愛情甚至反對愛情成為某種時代主流。愛他人的分量遠遠讓位給“愛自己”,一個將愛情看得太重的人,被放置在了鄙視鏈底端,為了追求愛情付出的心力更是可恥的。
時代情緒在提倡“自愛”,并認為充分地愛自己是愛他人的前提。可愛情的本質,就是一種人格深處缺失的彌補,是一種“忘我”。人們沉迷其中是因為忘我,但經歷傷害和痛苦,也是因為短暫的忘我。
一個有些“反現代性”的事實是—在今天,道德在愛情里的地位似乎更高了。
抽絲剝繭之后
愛情的魅力之一,在于排他性與唯一性。在這個擁擠的世界里,我唯獨看到了你,你也獨獨看到了我。愛情發生的瞬間,個人價值得到最大程度地滿足,對大部分普通人而言,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滿足。而那些三心二意的、朝三暮四的曖昧和試探,在審美上就與愛情背道而馳了。
但真正的愛是依附于日常和世俗發生的,我們沒辦法忽略復雜的現實,反而去發明一些更復雜的理論和公式來提純愛情,這實際上是在拒絕真實的感情。
《半熟男女》的原著作者柳翠虎在接受采訪時形容:“都市里的愛情其實很像綠化帶里的花,它很鮮艷,但是它也有城市應該有的汽車尾氣和灰塵。”
利益和算計、防備和試探,不公平的付出,以及永遠辨不出來的“輸贏”,這些東西看起來很狼狽和污糟,但它們是在這個環境里生長并活下去的必要痕跡。
“互相劈腿”的何知南和瞿一芃,也會在與前任分手的時候真情實感地流淚,他們真切地感受到痛。只要一個人還有心,哪怕已經被大面積污染,他依然可能被刺痛,可能發生感情的波動。
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我們選擇去愛,就要接受受傷的可能性。因為它極大概率是理性控制之外的、防不勝防的,也可能是短暫且充滿危險性的。
愛情是《花樣年華》里周慕云與蘇麗珍在深夜她拾階而上之前的剎那對望,是《兩小無猜》里還不懂愛的兩人互相說“敢”的一瞬間,是《安娜·卡列尼娜》里有夫之婦和年輕軍官在火車上偶然發生的剎那對望和震顫。
有時,愛情的發生,短到還不夠進入道德審判的維度。可有時,它與世俗道德的相斥性,又恰恰證明了它的純凈性。
對大部分親密關系而言,百分百的、純粹的公平是個偽命題,總有人付出多一點,在意多一些。同理,不假思索地接受對方的全部也是偽命題。在一次次體驗、質疑的過程中,我們漸漸靠近真實的自己,也漸漸攢聚起生命的多維度和厚度。
特約編輯吳擎 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