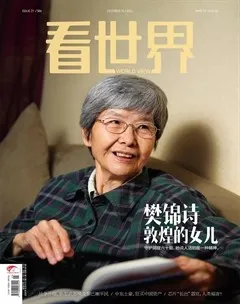中東土豪,狂買中國資產

近日,一家來自中東的投資機構Multi Gold Group Limited入主中國奧園的消息,引發了外界對中國房地產行業提振市場信心的關注。
將眼光從房地產行業放開去看,嗅覺敏銳且投資經驗豐富的中東資本,正在持續涌入中國。
此前據路透社6月4日消息,卡塔爾主權財富基金卡塔爾投資局已同意經由春華資本方面,購買中國第二大公募基金公司華夏基金10%的股份。
企查查數據顯示,目前華夏基金第一大股東為持股比例達到62.2%的中信證券,第二大股東為持股27.8%的外資機構邁凱希金融公司,第三大股東則為春華資本實控的天津海鵬科技咨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為10%。
也就是說,卡塔爾投資局與春華資本的交易落成后,前者將成為中國公募“大廠”華夏基金的第三大股東。
春華資本這10%的股權,已經“甩賣”許久。從2022年開始,春華資本想要轉賣套現的消息就不斷。如今,它終于等來了一位中東買家。
如果根據2024年3月中信證券所出的“放棄優先購買權”公告,卡塔爾投資局或將以不低于4.9億美元的價格,購買到這10%的股權。
不過,這不是中東主權財富基金第一次注意到中國資產。相反,一直重倉歐美的中東投資者們,近些年在中國的動作不斷。
比如,2023年6月,阿布扎比投資局通過旗下機構CYVN Holdings,向蔚來注入11億美元的投資,下半年蔚來再獲投,第二筆高達22億美元的投資資金最終落實。
Global SWF數據顯示,2023年,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六個主權財富基金,已經在中國進行了總計23億美元的直接投資與收購—而在2022年,這個數字還只有1億美元。
如果再算上主權財富基金透過旗下機構與公司的對華投資,那么2023年海灣地區國家對中國的投資數額將遠遠超過23億美元。
除了投資之外,中東投資者們同時“熱衷”于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組建當地團隊。
2023年,阿聯酋第三大主權財富基金穆巴達拉投資公司在北京設立辦公室;2022年,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資基金在香港設立了中國辦公室;科威特投資局早于2011年與2018年,就分別在北京和上海設立了辦事處,2019年更是出資2億投資濟青高鐵。
無法否認的是,2023年之后,中國越來越感知到來自中東的火熱。但并不是每個人都理解這背后的含義。我們仍需要知道,他們是什么來頭,以及何出此舉。
中東財團,何許人也?
談及為何我們需要關注來自中東的主權財富基金,原因無非是兩個。
一是中東主權財富基金確為全球最強大的投資者之一;二是相比于普通的投資機構,中東主權財富基金具備“特殊性”,其投資不僅僅追逐經濟目標,也反映著海灣地區國家政府可能的經濟與政治意向。
圍繞著地區內豐富的油氣資源,海灣地區國家已經積累起可觀的財富,在金融世界中占據了不可撼動的一席之地。根據Global SWF,2023年海灣地區主權財富基金的資產管理規模,已經達到了4.1萬億美元的歷史峰值。
他們的投資目光遍布全球,通過全球資產配置,發展經濟關系,降低經濟風險。與之相對應,海灣地區的主權財富基金在全球的上市公司中持有大量的股份,已經實際上具備了影響國際金融體系的力量。

2023年之后,中國越來越感知到來自中東的火熱。
這股力量,最早在2007年次貸危機時展現。期間其注入市場的數百億美元資金,就是證明之一。
時至今日,在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出具的全球十大主權財富基金名單上,來自海灣地區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已經占據了四席。
他們分別是管理著9930億美元資產的阿布扎比投資局,具備9250億美元資產的公共投資基金(沙特),擁有約9234.5億美元資產的科威特投資局,與有近5260.5億美元資產的卡塔爾投資局。
海灣地區主權財富基金資產實力之雄厚,不必再多說。
盡管細分來看,區域內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投資策略,總體呈現出多元化的投資偏好,但其仍有一個關鍵共同點不可忽視—其投資策略背靠國家政府或統治者家族,基本與具體國家的議程和長期經濟發展期望吻合。

能多大程度符合經濟多樣化、反哺本地等要求,也出現在沙特的投資考慮中。
中東主權財富基金對中國企業的投資,其實可以追溯到1992年。當年,中國市場首次向外國投資者開放,而阿布扎比投資局已經在列。此后,在2008年到2012年間,阿布扎比投資局、科威特投資局和卡塔爾投資局相繼獲得“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認證,就此,近20年間中東資金不斷流入中國。
從總體來看,目前已有的投資中,中東主權財富基金將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發達國家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和歐洲,其投資組合在地理上的分布差異較大。
但變化也在于,盡管流入歐美市場的資金仍然占據更大的比重,中東主權財富基金近期正有意識地增加亞洲投資組合,尤其與中國的接觸正越來越多。
中東主權財富基金投資中國相關的產業,其實并非一件新鮮事。“新”處在于,在多年的“平緩”發展之后,中東對于中國的目光突然變得炙熱起來。
冷卻與升溫
那么,為何是此時,中東投資者展現了對中國投資“更大的興趣”?
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是,從中國市場的情況來看,歐美國家對中國的投資增速近年放緩。
比如,拜登政府于2023年簽署了一則行政命令,限制美國風投機構與私募股權公司,向從事半導體、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領域的中國初創企業投資。出于地緣政治和經濟等因素考慮,也有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實行“中國+1”的發展策略。
這意味著,中國市場之中有更多的“投資空間”可以容納中東地區投資者,也希望吸納到更多來自中東的投資“補缺”。

因此,中國展現了更多面向中東的“善意”—一部分在經濟合作中展現,一部分則在政治上的“靠近”上展現。某種程度上說,中國與中東地區國家,彼此之間興趣都有所上漲,才最終促成了“來自中東的投資增多”的結果。
2023年以來,越來越多中國企業、投資機構帶隊前往海灣地區國家募資,尋求中東資本支持,一時間,已然掀起了“中東募資熱”。落實下來,也有一些中國企業已經與中東主權財富基金達成合作。
例如聯想在2024年5月與沙特的主權財富基金公共投資基金旗下子公司達成合作。在合作框架下,公共投資基金通過旗下子公司向聯想投資;相應地,聯想將在沙特設立地區總部,布置相關的生產設施。
有趣的地方在于,沙特正著力于其“2030愿景”。在該愿景中,2030年沙特將通過公共投資基金成為一個投資強國,并且,是一個經濟多樣化、就業機會繁多、經商環境良好的投資強國。
也就是說,從沙特的角度來說,其對企業的投資不停留在“企業能帶來多少利潤”的層面。能多大程度符合經濟多樣化、反哺本地等要求,也出現在沙特的投資考慮中。
不止專注于自身發展,企業在當地建立相應的產業鏈,按著本地“政治議程”和經濟發展軌道前進,是“友善合作”信號的一種體現。
擴大來談,經濟領域的“相互依賴”式合作不只體現在“投資熱”上。老生常談的是,中國是大多數中東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新變化在于,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已經在出海中東的事務上摩拳擦掌,比如美團計劃將中東作為其第一個海外擴張點。
但這并不是全部。尤其,當中東主權財富基金本身便帶有政治因素時。政治動機在中東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行為中占據多大的比重,不好測量,但影響一定是存在的。一個小證明是,在中國與海灣地區國家金融互動增多之后,2023年末,有外媒報道稱,拜登政府正對中東主權財富基金的對美投資交易,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核。
不難發現,近年來中國與中東地區國家正在不斷靠近。在中東地區,中國已經有了顯著的存在感。
2023年3月,一則重磅消息傳來。中國、沙特與伊朗三國在北京發表共同聲明,指出沙特與伊朗兩國達成一份“和解”協議,同意恢復雙方自2016年以來斷絕的外交關系,重開雙方使館。值得關注的是,在沙特與伊朗的突破性和解中,承擔調解人角色的,是中國。
而與“投資熱”在時間節點上吻合的,則是2022年年末中國與沙特達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沙特阿拉伯王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協議》,并在能源、技術和制造業等領域簽署了相應的商業協議。值得一提的是,此后,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也在沙特利雅得拉開帷幕。
兩方的關系,正在迅速升溫。

在A股市場,科威特投資局著重偏好生物醫藥行業。
投資法則
不過,當中東投資者將投資目光轉向亞洲時,他們仍遵循著一番策略。
從沙特與聯想的“合作式”投資中,已經可以看出一些中東主權財富基金們的一部分投資偏好—與本地的發展需求聯系緊密,最好能夠促進“共同目標”。
從公共投資基金的投資取向中,可以反復窺探到沙特“2030愿景”的身影—期待能源轉型,改變沙特的經濟結構和國際形象。于是其投資全球最大的科技投資基金,也投資高爾夫等體育運動。這也與“2030愿景”所闡述的,沙特對公共投資基金“寄予厚望”相一致。
在近些年來,中東地區的主權財富基金投資,已經不止于傳統的國債、銀行、房地產等領域。全球范圍內,其對新興技術、體育、游戲、可再生能源和醫療等領域的關注增加,樂于投注更多目光在獨角獸公司身上,其投資組合已經更加多樣。
在整體的投資組合中,阿布扎比投資局依然以“股票”作為最主要的投資方式,并且頻繁出現在A股市場之中,偏好有色金屬、生物醫藥、汽車等領域。無獨有偶,在A股市場,科威特投資局著重偏好生物醫藥行業,同時關注能源與汽車等相關行業。
某種程度上,這樣的行業偏好不算是“中國特例”,反而可以看作是它們的“投資慣性”。在過去的投資案例中,這樣的偏好反復出現。
比如2022年,阿布扎比控股公司(ADQ;阿布扎比三大主權財富基金之一)收購了土耳其藥品生產商Birgi Mefar Group,寄希望于借此在阿聯酋建立一個“完全集成的醫療保健和生命科學平臺”。
無論如何,加碼在中國的投資,意味著中東財團對中國資產的看好。畢竟,對于追求長期經濟目標的投資基金而言,選擇某個具體的投資對象,其利潤與未來的前景,必然在考慮范疇之內。
責任編輯張旦珺 吳陽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