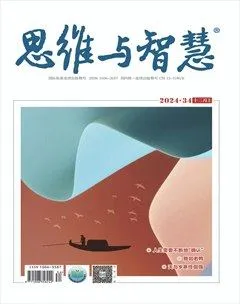為冷天留一副毛線手套
入了冬,天開始轉涼。每天午后的陽臺還算暖和,窗外的蠟梅也正爆著骨朵兒。母親便搬張小椅子,邊曬著太陽,邊織著毛線手套。這已是多年來的初冬,我們家陽臺上慣常的場景了。
母親年紀大了,我和妻已勸她很多次,不用再辛苦織毛線手套,長時間低著頭,抬著臂,對頸椎和手腕都不太好,再說家里已經沒有人戴了。
母親是執拗的,她不聽我們勸。有一次,快入冬的時候,妻悄悄地把棒針和毛線給藏了起來,謊稱前幾天收拾廢品的時候給處理了。
母親沒有作聲,趕緊起身,往樓下走去。妻緊跟著,沒想到平時腿腳不太利索的母親竟然飛快地跑到垃圾桶邊,踮著腳要去翻找。妻緊張地趕緊把她拉了回來,安慰說,垃圾桶里太臟了,已經幾天了,早就清走了。
母親有點兒失望,但沒有惱,卻像一個尋找丟失了心愛玩具的孩子似的,在家里著急地四處翻找。
我和妻看著心疼,但又想著,干脆再咬咬牙,挺兩天,也許她過幾天就忘了這茬兒了。我們到底是高估了自己的判斷,母親開始變得悶悶不樂,也不搬椅子到陽臺上曬太陽了,仿佛故意要躲著窗外那即將開放的蠟梅似的。
于是,我搬來妹妹這個救兵,可不但不奏效,反而激怒了母親,還被她狠狠地給頂了回去。我和妻心里都明白,母親是照顧著兒媳婦的面子的,可對女兒,她就真的是“原形畢露”了。
妻想,這樣下去,肯定不是辦法,于是不得不妥協。她笑著對母親說:“媽,那天我收拾了挺多東西的,也許那些針線什么的可能還塞在家里哪個角落吧。要不,您哪天得空的時候,再找找唄?要不要我們一起幫著找啊?”
“不啦,你們工作太忙了,我自個兒找。”母親雙眉一抬,提起了精神,嗓門兒亮了。
哪里還要等“哪天得空”啊,話音剛落,母親就開始仔細“搜尋”了。最后,在儲藏室的落地掛衣架上找到了。她一邊眉開眼笑地捧著針和線,一邊喃喃自語:“那天,我找了好幾遍,都沒找到呢。哎呀,到底是年紀大了,眼神不好啦。”我知道,這肯定是妻故意放到了顯眼的位置。
陽臺上,又恢復了往日的情景。
冬日的陽光透過玻璃,輕輕地灑落在母親額頭的皺紋上,像河面泛起的漣漪。那雙磨出老繭、浸染歲月風霜的雙手,正一針一針,慢慢悠悠地織著手套。
時光的指針仿佛慢了下來,綿長而舒緩,母親似乎要把這陽光和歲月都給織進手套里。這靜好的畫面卻無法阻擋我內心深處逐漸流淌而出的苦澀而溫暖的記憶。
那年,我剛上小學,初冬就開始出奇地發冷。有一次,我放學回來,手凍得像個涂了紅曲的小饅頭,紅紅的,鼓鼓的,麻木得快沒了知覺。
匆匆地吃了點兒炒干面,我便開始寫作業,可小手都快動彈不得了,握筆也不太聽使喚,即便強忍著,也還是沒寫上幾個字兒。
天黑了很久,父親和母親才從河道里上河工回來,他們滿身是泥,滿臉污水,看起來十分疲倦。可母親還沒來得及收拾,就徑直來到我的身旁,當她看到我才寫了幾個字,便開始責問,沾滿泥沙的手順勢抬了起來。
我趕緊伸出一雙小手,抬起頭,可憐兮兮的雙眼望著母親。她一怔,顧不得自己的衣服和手有多臟,一把拉著我的雙手,使勁地塞到自己的棉襖里,很快,又直接貼到她溫暖的肚皮上了,她彎曲著雙臂,使勁地從外面護著肚子,護著我的雙手。我看到了,在搖曳的煤油燈光里,她的雙眼變得模糊了起來。
幾天后,當我開始寫作業時,母親坐到了我的旁邊,手里拿著棒針,還有毛線,她在一針一針地,慢慢悠悠地織著手套,和如今初冬陽臺上的動作一模一樣,只是現在是因年老手緩,而那年,卻是因為剛學沒兩天,生疏得很。
母親為了給我織手套,從生產隊的會計那里借了兩根棒針,偷偷地把自己一條心愛的橙黃色圍巾給拆了,卷了一團毛線,而這手藝,則是她在上河工歇息空當兒,厚著臉皮,硬拉著同村的一位遠房姨媽教她的。這些,都是在我大些時候,遠房姨媽告訴我的,母親卻始終未曾提過一個字。
后來的每個初冬,母親便如約而至,坐在我旁邊,陪著我讀書,極其嫻熟地織著毛線手套,棒針越來越像變魔術似的,在毛線里快速地上下穿梭移動,一兩天就能織好一副。于是,每年冬天,我都能戴上厚厚的新手套,既溫暖又開心。
專業的針織技術,諸如鎖針、短針、長針、圓形針等,母親是壓根兒不懂的,她只知道,把一根長長的毛線編織成一副厚厚的手套,給她的兒子戴上,免得冬天小手再被凍壞了。后來,全家人整個冬天也都在享受著母親帶來的溫暖。
我一直在想,母親織進手套里的,其實是她的希望和慈愛。她美妙的動作,如行云流水般,一氣呵成,簡直像一首流淌在我心底的圣歌,給了我生活的溫暖和學習的動力。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場里的手套漸漸多了起來,材質、樣式、花色也越來越豐富。漸漸地,我們都開始嫌母親織的手套土氣,每年都會買新手套戴,母親織的便再無人問津。
母親并不惱,她默默地堅持著這個習慣,每年初冬,還是會為我們織毛線手套,只是今年織了,明年拆,再織,再拆,就如同家里陽臺外的蠟梅,開了又謝,謝了又開……只是棒針越磨越亮,毛線越來越細,一年一年地,她把歲歲年年的光陰織進了手套里。每當我們勸她不要織了,她總是輕輕地一句“為冷天留一副毛線手套吧”。
今年冬天,有一次,女兒周末回家,看到母親又在織手套,于是,在周日晚上,故意逗她,說:“奶奶,您抓緊織啊,我明天可就要上學去了,我想戴您織的手套!”
“真的?”母親雙眉一抬,提起了精神,嗓門兒亮了。
晚上,我起夜,發現客廳連接陽臺處的小落地燈還亮著。是母親,她低著頭,在橙黃的燈光下,如同那年她坐在我身旁,在煤油燈下一樣,一針一針,慢慢悠悠地織著。母親這是在為孫女趕織手套啊,我決定不去打擾她。
第二天,女兒戴著母親織好的毛線手套,歡悅地去上學了。母親也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我望著女兒遠去的身影,慢慢地體會到了,母親為冷天留的不單是一副毛線手套,而是在堅守一份溫暖,一份對親人的呵護。而我們卻選擇了近乎“背叛”的遺棄,遺棄了那段苦澀的時光,遺棄了那些曾經溫暖過我們心靈的手套,遺棄了我們生命中最樸拙最純真的底色。
我趕緊拿起手機,為母親在網上訂了一套棒針、一卷橙黃色毛線,和母親當年為了給我織手套而拆掉的心愛的圍巾一個顏色。
(編輯 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