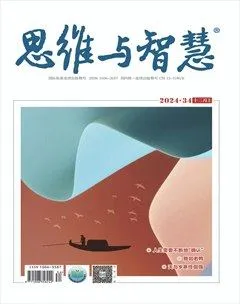藏在縫隙里的愛
常言道,少年夫妻老來伴,我的父親母親大概就是這樣。在那個物質匱乏、民風淳樸的年代,年輕時的他們沒有鮮花紅酒,也沒有甜言蜜語,卻一路風雨走來愈發地和諧、默契。尤其是今年發生的一件事,讓我逐漸明白了父親對母親無微不至的關心,也讓愛的空間有了新的詮釋。
最近幾年母親都在省城幫弟弟帶孩子,而父親則守在老家照看店里的生意,兩人也只有過年才能相聚。從來不喜歡煲電話粥的父親卻像變了個人似的,每天都要給母親打好幾通視頻電話,像叮囑晚輩似的提醒她照顧好自己。不像年輕人打電話那般隨性,父親看似見“縫”插針的電話,實際上是經過了自己用心的計算。他早已對母親在那邊的作息規律了如指掌,以至于母親得空時剛在心里一念叨,這邊父親的電話就來了。盡管父親每天都要叮嚀好幾遍,可意外還是發生了。
今年早春,省城剛下過一層薄雪,天一放晴母親便抱著小侄子去婦幼保健院體檢。走到一處臺階時,母親一個不小心滑了一跤。為了不摔著小侄子,母親牢牢地將他護在了身前,自己的頭和肩膀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據母親自己講,當時她腦袋里“嗡”的一聲響,半邊身子疼得動彈不得,后來還是好心的路人將她攙扶了起來。
弟弟沒敢大意,當天就領著母親在大醫院里拍片子、做核磁共振,結果顯示母親并沒有骨折。盡管大家都松了一口氣,可父親卻一臉愁容。
“就算沒有骨折,你這怕是一點活兒也不能干了,不行我把店門關了去幫你吧。”父親顯得格外擔心。
“別啊,這邊屋子小,你來了也沒處睡。再說我還有另外一邊胳膊能動,一只手不也照樣能干活嘛。”母親一貫要強,能堅持干活兒就絕對不會歇著。
就在大家以為母親會一天天地恢復過來時,母親卻說她疼得整晚上睡不著覺。已經兩周時間都過去了,肯定是哪里還有問題。父親不放心,聯系了自己在醫院的專家朋友,就這樣我們領著母親又拍了一次片子。
片子結果出來后,“骨裂”兩個字顯眼地印在報告單上,我們既困惑又震驚。困惑的是為什么那么好的大醫院第一次沒有檢查出來,震驚的是骨裂那么疼母親竟然忍著疼用一條胳膊堅持了兩周。在骨科主任的辦公室里,大夫向我們詳細地講解著片子:“看,就在這里,肩胛骨背后的縫隙里,這塊小骨頭有條不易被察覺的裂縫!”
“原來是這樣,那現在我們該怎么辦?”父親焦急地問著。
“前兩個月最好不要動,訂副支架將右肩固定起來,然后定期來復檢。”雖然主治大夫說得很輕松,我們一家人卻心疼不已。
沒辦法,弟弟只能叫來了自己的岳母幫忙照看孩子,而母親則被父親接回了家。母親回家靜養的那段時間里,一家人都忙碌了起來:弟弟從省城醫院里訂好了支架寄了回去;姐姐們老遠地寄回了補品,并時時在電話里叮囑母親加強營養;我和妻子則經常開車回家看望母親。但我知道,最辛苦的還是父親。整整兩個月,他都沒有讓母親動一下胳膊。在我們上班忙碌的時候,父親既要負責一日三餐和打掃衛生,還要照顧店里的生意,就連平時很少插手的洗衣服,那段時間也都是由父親包攬。很多時候我們回到老家時,洗衣機里正洗著衣服,父親剛吃完飯還沒來得及洗碗,就要跑到前屋去照顧生意。他的每一寸生活縫隙,似乎已經被填滿。
見父親那么辛苦,周末回家時我便提出要把母親接到縣城里照顧幾天。父親說什么都不答應,說怕我們不會照顧。還是妻子心細,一下子就猜到了關鍵,“爸是怕咱們上班后咱媽閑不住又幫咱們干家務,不利于骨傷恢復,待在老家他可一直都盯著呢。”
經妻子這樣解釋,我也不再執著,只是從心底里對父親更加欽佩。母親確實是那種閑不下來的人,如果真的讓她來家里,她肯定會忍不住幫我們打掃衛生。就這樣,父親一直把母親照顧得很好,即使是去醫院復查,他也要跟著,生怕我們粗心漏掉了什么。
一直以來,我所理解的愛是有儀式感,有行動力,但在具體的生活中卻變得模糊起來。然而,從父親身上我卻看到了愛的另外一種形式,那便是:無微不至的照顧。即使是在細小縫隙里,也能填滿真誠的關懷。
(編輯 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