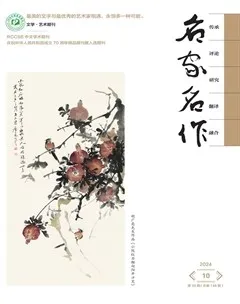西方藝術創作視聽融合層次分析




受古希臘“七藝”理念影響,七藝中音樂與不在范疇內的繪畫較為獨立地各自發展。隨著藝術創作理念不斷進步,藝術家們注意到在不同藝術門類中獲取創作靈感,使作品更具表現性。在跨藝術種類實踐中,音畫視聽融合在西方藝術史有著一定的重要性,不僅深刻影響了印象派、表現主義藝術創作,而且對現在也仍有深遠影響。本文通過分析西方藝術史中音畫結合的主要案例,劃分幾種不同視聽融合創作層次并進行分析,論證音畫結合變化契合西方藝術從再現到表現的發展脈絡。
形象再現層次
形象再現層次創作,多集中于浪漫主義時期前,音樂中通過強弱、音高、音色、配器、演奏法等模仿事物發出的聲響或暗示形象的樂音或音響,是音樂探索減少音響表達內容不確定性而模仿繪畫再現事物優勢的嘗試。如“繪詞”(Word painting)與“繪聲”(Tone painting),是較早就出現的一種音樂創作方式,可追溯至格里高利圣詠,通過創造契合文字歌詞意義的樂音,直觀地表達作品思想情感以及意義。
亨德爾的歌劇《里納爾多》開頭中,為體現角色的哭泣與悲傷,使用詠嘆調體現,歌詞意為“讓我為自己不幸的命運哭泣”,不僅使用小調,還利用節奏的間斷分割樂句為短片段,生動模仿悲傷哭泣時呼吸的斷續(見圖1)。
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曲《田園》中有使用樂器的樂音來指代事物。在第二樂章中,在開頭使用弦樂器演奏出模擬流水的動機;接近尾聲的第130小節,是一處貝多芬使用三種木管樂器來模仿鳥叫的華彩樂段。貝多芬在樂譜中對鳥的種類作了說明:長笛代表夜鶯、雙簧管指代鵪鶉、杜鵑是兩支單簧管。在第四樂章,開頭為了襯托將來激烈的雷雨,演奏了暴風雨來臨前的寂靜,然后中提琴急促連續的音階跳音,低聲部大提琴震音表現低沉的轟鳴,體現了風雨欲來的情景;第21小節作為轉折,樂器在極強的表情符號(ff)指導下齊鳴,給予人極大的壓迫感與震撼,然后利用大鼓和定音鼓的配器來模仿雷雨的音響效果,搭配以長笛和小提琴演奏緊湊的半音音階去模仿颶風襲來的景象。
但一些理論過度使用樂器模仿自然界的音響,導致使用的僵化,如獅子吼叫、公雞打鳴、窸窸窣窣的蛇①。這使音樂淪為一種文字性說明,導致音樂作品僵化。這是此時音畫藝術語言結合實踐不成熟導致的問題。音畫結合的初期仍受古典再現思維的影響,然而音樂的語言能力和形象再現顯然是有限的,這種思維下的音樂創作所拓展的藝術表現邊界是有限的,甚至局限了音樂原本的表達廣度,失去了音樂音響內容表述的不確定性。
內容敘述層次
浪漫主義時期,如瓦格納所提倡的 “Gesamtkunstwerk(整體藝術)”,強調音樂藝術創作需要與詩歌、戲劇、繪畫等音樂之外的其他藝術為靈感來源并與之結合,使得歌劇等綜合性藝術形式發揚光大。此時的音樂作品的視聽融合在內容敘述層次中有著集中體現。
有音樂作品借用已有的文學或繪畫作品的共有意象、故事情節進行再創作。李斯特與柏遼茲發展的 “標題音樂”是為了可以表現呈現超音樂的敘事。它鼓勵在音樂中使用文字、圖像和戲劇性的聯想,展示其音樂性和文學性,保證作品可讀性與畫面感。如柏遼茲的《幻想交響曲》,講述了一系列病態的單相思幻想。作品全名為《幻想交響曲:一個藝術家的生活片段……五個部分》(Fantastical Symphony: Episode in the Life of an Artist… in Five Sections),作品有“夢與熱情”“舞會”“田野風光”“赴刑進行曲”“妖魔夜宴”五個樂章,柏遼茲為每個樂章提供了序言和說明,以便觀眾理解作品內容,使整首交響曲猶如一部默劇。
李斯特的作品《婚禮》,靈感來源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畫家拉斐爾早期的名作《圣母的婚禮》①。這是李斯特創作的第一部直接以圖畫為素材的音樂作品;李斯特的另外一部作品是第11號交響詩《匈奴之戰》,取材自同名壁畫《匈奴之戰》(見圖2)。1855年夏,李斯特被贈予壁畫《匈奴之戰》,并在1857年將其音樂化②,他與另一位鋼琴家一起在畫作前演奏了此曲,證明這幅壁畫正是他作品的直接靈感來源,繪畫配合音樂的形式使得樂曲展現更為直觀。
不同于形象再現層次,內容敘述層次不局限于單純刻畫事物,主導動機與固定樂思對于描述事物更為抽象概括,具有一種符號性的對應關系,使故事描述邏輯更加連貫,更契合音樂本身的非語義性,有利于音樂內容整體敘述以及情感為重點展現在柏遼茲《幻想交響曲》演奏指導的文字說明中,就有強調如何通過音樂描述故事添加舞臺情緒感染力,但這種情感的表達依然還是以客觀事物為載體。
這一時期的音畫結合的表現更具張力,但音樂很難通過自身去敘述內容與創造新的意象,沒有完全讓音樂藝術擺脫受限于其他藝術內容的境地。事實上,大部分音樂家仍對繪畫藝術興趣寥寥。瓦格納和柏遼茲等人承認自己對欣賞美術作品漠不關心,很少參觀美術展覽。柏遼茲斷言:“繪畫不能侵占音樂的領域;但音樂可以通過自己的方式作用于想象力,產生類似于圖形藝術所產生的感覺。”諷刺的是,他們的作品卻充滿了視覺意境,畫家對此特別有吸引力。雖然此時音畫結合還并非藝術創作主要方法,但為印象派時期、表現主義音樂繪畫結合的藝術創作提供了寶貴經驗。
意象融合層次
傳統藝術邁向表現主義過程中的藝術創作開始不再刻意注意客觀形象的描繪,即使依然以客觀事物為主題,將對物體的內心投射為表達重點,印象派音樂作品常常圍繞著一個意象松散表述渲染意境。通過大量反傳統、模糊化、豐富化的色彩,代替細致刻畫。印象派音樂使用與繪畫相通的藝術手法,使作品提供相似的體驗。
德彪西創作在標題上就可見一斑:作品名字及題材有意模仿美術作品,如《版畫集》《意象集》《牧神午后》組曲等。德彪西表示《牧神午后》是一組具有意象的繪畫,他的創作構思以繪畫感為出發點,暗示印象代替直接闡述。在《亞麻色頭發的女孩》(見圖3)中,通過一種易于理解的方式傳達天真爛漫少女的印象,其節奏設計以反復的短—短—長音型為主,在樂曲開頭的初始音符及第4小節進下一個樂段前的音符,強拍與之后的音符通過同音兩線形成延長音,加強節奏不確定性,制造浮動飄忽之感,如印象派繪畫一樣使用松散的筆觸去營造夢幻般的畫面效果;旋律部分來自五聲音階Eb、Gb、Ab、Bb、Db,以五聲衍生的和弦與旋律為中心,削弱了傳統和聲功能性。使用復雜的和弦豐富了和聲色彩,借鑒了印象派繪畫強調顏色的理念,使作品輪廓若隱若現③,促使欣賞者感性理解作品,而非從具象、理性的角度解讀作品。通過一些視聽藝術互相照應的手段,營造有聯覺性的內容,使音樂在意象上呈現類視覺的既視感。
印象派過渡到表現主義時期許多音樂家的創作受繪畫影響,這得益于以法國為主的音樂與繪畫的密切接觸,相較之前以藝術內容為音畫結合主要結合契機,意象融合層次的音畫結合更體現在藝術處理方式上的融合。
精神融合層次
精神融合層次的音畫作品在表現主義時期有顯著體現。表現主義將精神性的體現作為主要目的,注重強烈的沖突與精神描述,表現手段更為激進與大膽,創作方法為感性表達讓步。以康定斯基為代表,強調以抽象形式表現內在精神,將繪畫與音樂進行對照研究,認為藝術家們應表達情感體驗,而非物理現實,藝術既不應該被“描寫”,也不應該被“象征”,“形式(唯物主義)并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最終目標”①。
康定斯基致力于有關“通感”等關于視聽藝術跨學科研究,指出無論繪畫、音樂都能夠通過自己的藝術形式等效的喚起欣賞者對于藝術作品精神的感悟②。康定斯基認為雖然聲音(音樂)與色彩(繪畫)具有相對應的聯想、相似的基因,但是這并非唯一的基因,另一個是心理的基因,即有關“精神”問題③。康定斯基也對瓦格納、德彪西和勛伯格等人的作品有所研究,在一場音樂會后寫給勛伯格的信中,他認為在勛伯格的作品中可以窺探每個生命的內在,體現了康定斯基在有關視覺藝術與音樂結合理論方面的思想。
勛伯格的繪畫作品《藍色自畫像》(見圖4),充分體現了表現主義特點,描繪客觀外貌并非作品目的,而是內在精神的傳遞。他的音樂作品以更純粹的精神表達與內心寫照為題材,這不同于印象派音樂、浪漫主義等“以景抒情”的方式——雖也強調情緒原則表現感性內容,但仍以客觀世界為主導。勛伯格在印象派音樂弱調性基礎上發展無調性音樂,使作品不被調性所束縛,更具精神性、沖突性,更易產生情感共鳴。比如《華沙幸存者》中緊張急促的樂器音響是由大量不和諧和弦構成,使作品中的恐懼和痛苦體現得淋漓盡致。
以康定斯基與勛伯格代表的表現主義藝術創作,都盡力摒棄具體藝術形象,將視聽藝術作品指向共通的精神性,為音畫融合的藝術創作提供了成熟的思路,指出視聽藝術語言相通的精神性本質,為音畫結合跨藝術學科結合研究作出巨大貢獻。
參考文獻:
[1]李雪潔.浪漫主義時期音樂非音樂性:繪畫性[J].中國科技博覽,2010(12):241.
[2]夏賢智.西方音樂美學情感論視域下的李斯特音樂美學思想研究[D].南昌:江西師范大學,2011.
[3]喬玥.人文與浪漫,靜止與流動:從李斯特宗教小品《婚禮》中看音樂與繪畫的關系[J].藝術百家2011,27(S1):345-346.
[4]張春華.瓦格納“整體藝術”觀對象征主義美術的影響[J].齊魯藝苑,2006(2):19-22.
[5]段文玄.瓦格納“整體藝術”觀形成與發展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13.
[6]陳婧.讓瞬間成為永恒:印象派繪畫“光色”與印象派音樂“音色”之對比[J].當代音樂,2016(9):77-79.
[7]劉長林.印象派繪畫與印象派音樂的比較研究[D].成都:四川音樂學院,2016.
作者單位:江西服裝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