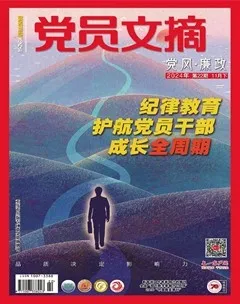30年近1.2萬名干部支援,助力西藏實現跨越式發展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作出“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決策后,西藏用30年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治國、治邊和穩藏的關系,決定了西藏的發展路徑是獨特的。援藏是國家治理的戰略部署,也成了西藏發展的重要支點。
2024年8月底,“30年來援藏工作開展情況”新聞發布會在拉薩召開,公開的數字顯示,自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對口支援”西藏計劃起,已有10批、近1.2萬名干部人才進藏工作。
高原養魚
2024年10月11日,距離西藏自治區林芝市中心約40公里的一處農場里,3名來自廣東珠海的援藏干部在塵土飛揚的工地上,一邊承受著因高原缺氧所造成的身體負擔,一邊籌建著新的漁業養殖設施。
農場全稱是林芝農墾嘎瑪農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康曉丹是廣東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隊成員,2022年進藏前,他在珠海九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任經營管理中心總經理一職。康曉丹現在的同事、林芝農墾嘎瑪農業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兼董事長林浩生,進藏前是廣東省珠海市僑聯黨組成員、副主席。
他們要經營的是一處連年虧損的農場。
初到林芝的林浩生,此前從未學習過任何農業知識。
另一位從珠海市現代農業發展中心派來援藏的漁業專家駱明飛成為技術骨干。正式開展工作后,三人決定,將農場的主導產業從水果種植業轉向高原漁業與水果種植業并重發展。
僅用了一年時間,他們將農場種植的反季櫻桃打造成了品牌,投資5萬元的“保溫養殖”專利技術就帶來超過30萬元的漁業回報,將高原養魚從不可能變為可能。
回望兩年援藏生涯,康曉丹見證了這方小天地一點點好起來。
2022年的某一天,康曉丹接到廣東省珠海市委組織部的電話時,正在辦公室午休。電話那頭,一位科長告訴他,新一輪的援藏工作正在找合適人選,有人推薦他,讓他考慮是否愿意去。
接到這通“緊急”來電前,康曉丹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一名援藏干部。與家人商量后,他很快作出了肯定的選擇。
與康曉丹不同,林浩生是主動報名要求援藏的:“我原來的領導援過藏,對西藏感情很深。”
援藏干部群體中,像這樣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傳承并非孤例。
援藏干部許曉珠告訴記者,現在林芝市內有十幾個援藏的公務員、志愿者或老師,都曾是他的學生。
三個階段
今年57歲的扎西洛布是林芝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他至今還對第一批援藏干部進入林芝時發生的事記憶猶新。
聽說援藏干部要來,干部、群眾自發組織了歡迎活動,排了兩公里長的隊伍,但援藏干部卻遲遲未到。
原來,當時市區到波密的必經之路318國道是沙土路,下雨時,常發生高山滾石、塌方、泥石流等現象,其中最危險的“排龍天險”14公里路段更是以險峻聞名,被稱作“死亡路段”。
2010年出版的《西藏援助與發展》一書中,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靳薇寫道:“內地黨政干部到西藏工作經歷了‘進藏建藏’‘輪換進藏’以及‘定期輪換援藏’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1951年至1978年間,進藏的主要是軍人,四川、青海、云南等地的藏族干部,還有從內地選調的技術干部等,普遍工作時間長,多為10年到15年,有的達28年,很多軍人的子女都在西藏出生、成長、工作。
到了第二階段,1979年至1993年間,中央開始對干部終身進藏工作的制度進行改革,從19個省、市和9個中央國家機關抽調黨政干部或專業技術干部進藏,將黨政干部的工作時間縮短為5年,專業技術干部縮短為3年。
1994年召開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干部援藏的政策為“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要求北京、上海、廣東等14個省、市對口支援西藏7個地區,中央多個部委對口支援西藏自治區直屬機關。干部援藏進入第三階段。
1995年2月底,分片對口政策提出后,中央決定從首批承擔援藏任務的各省市、部委中選派1000名左右領導和技術骨干進藏,其中縣處級以下干部年齡一般在40歲以下,縣處級以上干部年齡在45歲以下。
1995年,662名援藏干部正式進藏。許曉珠了解到,由于進藏時間晚,第一批工作隊實際在藏工作時間為兩年半左右。此后,每三年輪換一次成為常態。

轉向
10月中下旬的林芝有些北方秋末初冬的意味,但正午強烈的紫外線穿透淺白的云層時,又讓人恍然如至暖春。
林芝市中心區八一鎮,作為“一個在河灘上崛起的援藏新城”,遍布“珠海樓”“廣州大道”“福建路”“福建園”等地理坐標。
1986年,林芝地區行政公署剛剛恢復設立時,扎西洛布還沒有參加工作。在他的印象中,當時整個片區只有一條街。
四川大學社會發展與西部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楊明洪被稱為“二代援藏研究專家”,在他看來,早期援藏的核心就是工程建設項目。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對口支援期限為10年,其間為西藏安排了62個工程建設項目,由有關部委和有關省市分別承擔。
楊明洪告訴記者,這一階段各省市援助不僅需要援藏干部提出項目,準備原材料、施工隊完成工程、建設資金也需要對口支援的省市尤其是援藏干部去落實。就像蓋房一樣,房子建好,只把“鑰匙”交給受援方。
到了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要將原定的對口支援期限再延長10年,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將未建立對口支援關系的29個縣納入對口支援范圍,同時安排26個省市進行對口項目建設。
許曉珠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到林芝市墨脫縣的,到了縣里,許曉珠提出想給縣里修路。當地干部以及其他的援藏干部們不看好許曉珠這一充滿“英雄主義色彩”的想法。
2006年6月,在許曉珠的爭取下,原交通部派出了以地方公路司司長為組長的工作組到墨脫實地考察。
工作組到達那天,縣里很多老百姓都出來迎接,打出了“墨脫軍民盼通公路”的橫幅。許曉珠在日記中寫道:“看到這種情景,所有工作組的同志都流淚了。”
2007年,三年援藏期滿,許曉珠離開墨脫時,墨脫公路建設已被納入自治區“十一五”公路建設規劃。2013年,墨脫結束了不通公路的歷史。
細數援藏30年的項目投入,在扎西洛布看來,一切遠非“逢山開路,遇水架橋”那樣簡單,前三批援藏干部的工作主要是打基礎,重點看西藏缺什么、往哪個方向發展,之后則是進行接續式的推進。
從“輸血”到“造血”
除了方向略有偏轉,楊明洪還提到,與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規定了62個項目不同,2001年召開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中央并未規定援助方應該出多少錢,而是將各省市的年度援藏投資實物工作量交由援助方決定,事后研究發現,由于各省市相互競爭,實際的資金投入體量基本相當。
在楊明洪看來,也是出于希望援藏干部多回所在省份、單位獲取援助的考慮。2001年過后,尤其是第五批、第六批援藏干部中,出現多人在支援地擔任縣委書記、縣長、區長等正職的情況。
不過很快,從第七批援藏干部開始,援藏的干部只能任副職,將正職留給當地干部。
在扎西洛布看來,職務身份的轉變其實體現了援藏制度的調整:剛開始是“輸血型”援藏,后續援藏轉變為“造血型”,援藏干部到來后不僅要承擔具體的工作,還要把當地的很多能人,黨政機關的領導干部、企業的人才等培養起來,“不能在援藏干部換了以后,我們自己走不動了”。
2010年,扎西洛布獲得了去往廣東省廣州市增城區掛職交流的機會,為期一年。這也是中央為培養西藏當地干部,特地安排的雙向交流活動。
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官網信息顯示,1997年至2008年間,西藏先后選派248名干部赴中央國家機關和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掛職鍛煉,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占95.16%。
曾與許曉珠共事過的墨脫縣原副縣長央金就在2006年3月,被派往廣東省中山市西區辦事處掛職,擔任主任助理半年后,她感嘆自己在離西藏千里之外的廣東,“反而更加了解西藏,認識墨脫”。
考核與延續
小到一處農場,大到自治區、中央層面的項目,提升援藏效率已成為對口援藏中后期工作的重要導向。
2023年5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組織調研團,進藏開展“十四五”對口支援西藏階段性績效綜合考核評價抽查調研工作。廣東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隊副領隊、林芝市委副秘書長鄧鋼告訴記者,這次考核中,廣東省因投資實際綜合效益上表現良好,6項考核指標中,有5項拿到了第一,最終與北京市、江蘇省兩支援藏隊一起位居綜合排名前三。
考核不僅針對援藏隊,對援藏干部工作成效的考核同樣存在。
早在2012年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聯合下發了《對口支援西藏干部和人才管理辦法》,提出對援藏干部的平時考核側重政治表現、工作實績、在藏率、在崗率等。
回望過去30年干部援藏的歷程,林芝市經開區副主任李明高坦言,在傾斜了大量資金、資源之后,西藏的基礎設施確實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目前當地還存在造血功能不足的問題:如果有一天停止投入,當地能否將現有成果保持下去。
不過,對目前還在援藏的干部來說,延續與造血早已列入他們的工作計劃。
林浩生告訴記者,為了完成與下一批次援藏干部的工作對接,從2024年年中開始,農場的3位援藏干部便開始為“交渠道、交經驗、交人才”作準備。
“至于本地人才培養,我們搞了個‘傳幫帶’的制度,找了3位從珠海市的國企選派的柔性援藏人才,一個教財務,一個教項目建設,一個教銷售,慢慢地將藏族的這些大學生職工也培養起來。”林浩生說。
(摘自《南方周末》)